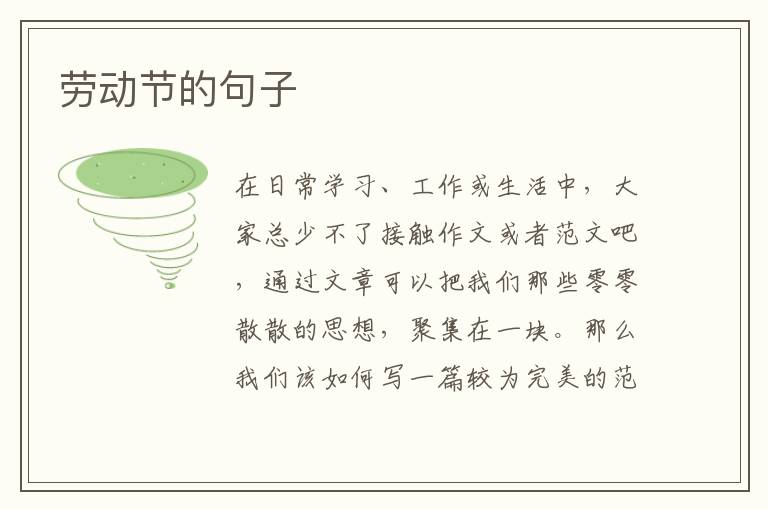賈平凹描寫陜西面食的句子100條

賈平凹《陜西小吃小識錄》原文賞讀
醪糟
醪糟重在作醅。江米泡入凈水缸內,水量以淹沒米為度,夏泡八時,冬泡十二時。米心泡軟,水空干,籠蒸半時,以涼水反復沖澆,溫度降至三度以下,控水,散置案上拌糯粉,裝入缸內,上面拍平,用木棍在中間由上到底戳一個直徑約半寸的洞。后,蓋草墊,圍草圈,三天三夜后醅即成。
賣主多老翁,有特制小灶,特制銅鍋。拉動風箱,卜卜作響,一頭灰屑,聲聲叫賣。來客在灶前的細而長的條凳上坐了,說聲:“一碗醪糟,一顆蛋”。賣主便長聲重復:“一碗醪糟,一顆蛋------!”銅鍋里添碗清水,放了糖精,三下兩下燒開,呼地在鍋沿敲碎一顆雞蛋打入鍋中,放適量的醪糟醅,再燒開,漂浮沫,加黃桂,迅速起鍋倒入碗中。
要問特點?酸甜味醇,可止渴,健胃,活血。
桂花稠酒
【第1句】:泡米:清水入缸,淹沒江米,木瓢攪拌使臟物上浮撇而棄之。四時為宜。
【第2句】:蒸米:上籠,燒大火,熟爛達八成,離火,澆水,先米中間后籠周圍,溫度降至三度以下即可。
【第3句】:拌曲:平散攤開在案,撒曲面,拌,需均勻。
【第4句】:裝缸:先置木棒一個,于缸中心,將米從四周裝入輕輕拍壓,后木心轉動抽出,口成喇叭狀。白布蓋之,再加軟圓草墊,保持三十度溫,三天后酒醅即熟。
【第5句】:過酒:將缸口橫置兩個木棍,銅絲蘿架其上,蘿中倒多少酒醅,用多少生水幾次淋下,手入酒醅中轉、攪、搓、壓,反復不已,酒盡醅干。 酒中放糖精,加桂花,加熱燒開。 一般酒澄清,此酒粘稠,一般酒辣辛,此酒綿甜。鄉民能喝,市民能喝,老人能喝,兒童能喝,男人能喝,女人能喝,健胃、 活血、止渴、潤肺。
相傳太白飲此酒,成詩百篇。故歷來文人到長安,專飲桂花稠酒。今有一學子欲做詩人,每次到酒店大飲覓靈感,但三碗下肚,則大醉,語無倫次,不識歸路。
涼皮子
是夏天食品,三九寒天卻有出售,吃者,男食者絕少,女人多,妙齡女人尤多,半老徐娘的女人更多。
制法:一斤面粉用二斤水,分三次倒入,先和成稠糊,再陸續加水和稀,加鹽,加堿,稀漿用手勺揚起能拉起筷子粗細的條為宜。籠上鋪白紗布,面漿倒其上,攤二分厚,薄厚均勻,大火暴蒸,氣圓,約六七分鐘即熟。將面皮從籠箅上扣在案上,每張面皮上抹一層菜油,疊堆一起晾涼后用擺刀切成細條。
賣主賣時并不用稱,三個指頭一捏,三下一碗,碗碗份量平等,不會少一條,多一條也不給。加焯過的綠豆芽,加鹽,加醋,加芝麻醬,后又三指一捏,三條四條地在辣椒油盆里一蘸放入碗上,白者青白,紅者艷紅,未起唇則涎水滿口。
且記:吃涼皮子的別忘記帶手帕,否則吃罷一嘴沿紅色,有傷體面。
粉 魚
名曰魚,其實并不似魚,酷如蝌蚪。外地人多不知做法,秦人有戲謔者夸口為手工一一捏制,遂使外人嘆為觀止。
秦人老少皆能作,依涼水加白礬將豆粉搓成硬團,后以涼水和成粉糊,使其有韌性。鍋水開沸,粉糊徐徐倒入,攪,粉糊熟透,壓火,以木勺著底再攪,鍋離火,取漏勺,盛之下漏涼水盆內;“魚”,則生動也。
漏勺先為葫蘆瓢作,火筷烙漏眼;后為瓦制;現多為鋁制品。
漏雨可涼吃,滑、軟,進口待咬時卻順喉而下,有活吞之美感。易飽,亦易饑。暑天有愣小子坐下吃兩碗,打嘈松褲帶,吸一支煙,站起來又能吃兩碗,遂暑熱盡去,液下津津生風。
冬吃則講究炒粉,平底鍋燒熱,淋少許清油,將蔥花稍炒后,倒粉魚炒,加糖色、調料,以瓷碗捂住,一二分鐘后,色黃香噴即成。賣主見婦人牽小孩路過,大聲吆喝,小孩便受誘不走,婦人多邊喂小孩,邊斥責小孩嘴饞,卻總 要喂小孩兩勺,便倒一勺入自己口中。
歧山面
歧山是一個縣,盛產麥,善吃面條。有九字令:韌柔光,酸辣汪,煎稀香。韌柔光是指面條之質,酸辣汪是指調料之質,煎稀香是指湯水之質。
歧山面看似容易,而達到真味卻非一般人所能,市面上多有掛假招牌的,俗辨其真偽,一觀臊子[左火右覽]法和面條搟法便知。
臊子,豬肉,必帶皮切塊,碎而不粥。起鍋加油燒熱,投之,下姜末、調料面煸炒。待水分干后,將醋順鍋過烹入,沖冒白煙。以后醬油殺之,加水,煮。肉皮能掐時,放鹽,文火至肉爛舀出。搟面,堿合水,水合面,揉搓成絮,成團,盤起回性。后再揉,后再搓,反復不已。而后搟薄如紙,細切如線,滾水下鍋蓮花般轉,撈到碗里一窩絲,澆臊子,只吃面而不喝湯。
在歧山,以能搟長面者為女人本事,否則視之家恥。娶媳婦的第二天上午,專門有一個搟面的隆重儀式:客人上席后,新媳婦親自上案搟面,以顯能耐。故女兒七歲起,娘便授其技藝,搭凳子在案前使搟杖。
羊肉泡
骨,羊骨,全羊骨,置清水鍋里大火燉煮,兩時后起浮沫,撇之遺凈。放舊調料袋提味,下肉塊,換新調料袋加味。以肉板壓實加蓋。后,武火燒溢,嘭嘭作響,再后,文火燉之,人可熄燈入睡。一覺醒來,滿屋醇香,起看肉爛湯濃,其色如奶。此羊肉制法。
十分之九面粉,十分之一酵面。摻和,攪勻,揉到。做饃胚二兩一個,若[左食右乇][左食右乇]狀,[左食右乇]邊起棱。下鏊烘烤,可悠悠溫酒,酒未熱,則開鏊,取之平放手心,在上騷騷,手心則感應發癢,此饃餅制法。
食客,出錢并非飯來張口,凈手掰饃,碎如蜂[左月右上夭下韭]。一是體驗手工藝之趣,二是會朋友談藝文敘家常拉生意,饃掰如何,大、小、粗、細,足可見食者性情;烹飪師按其饃形,分口湯、干泡、水圍城、單走諸法烹制,且以饃定湯,以湯調料,武火急煮,適時裝碗。烹飪十年,身在操作室,便知每一進餐人音容相貌,妙絕比柳莊麻衣相師有過之而無不及。
西安五味巷有一翁,高壽七十。二十年前起,每日來餐一次。
饃掰碎后等候烹飪,又買三饃掰碎,食過一碗,將掰碎的饃帶回。
明日,將碎饃烹飪,又買新饃掰。如此反復,不曾中斷。
臨終, 死于掰饃時,家人將碎饃放頭側入棺。
漿水面
“下里巴人”飯。不吃者絕不吃,喜吃者死都要吃。
城里人制漿:鍋中添清水,一手持長筷,一手撒面,邊攪邊撒,攪勻燒開。將醋曲和洗凈的芹菜放在缸里,燒開的面湯入缸內,日曬六七天,湯呈乳白色即可。鄉下人制漿簡單,泡半生不熟的蘿卜纓子及白菜在甕,將糝子稀飯的清湯倒幾勺進去,六七天即成。
面條下鍋,漿匯鍋即可,面撈碗澆漿亦可,以口味而定,但絕少不了葷油、蒜苗。冬吃能取暖,夏吃能消暑。萬不能再加醋,有醋則澀,切記。
此食流行鄉下,城市不多見,一向被視為賤食。殊不知漿水面味在于淡,淡方是食物本味、真味,飲食是衛護人的生命的,如果自視高雅,追求滋味精美,那將會本末倒置,反害了卿卿健康。曾風傳:漿水致癌,此惡意中傷。
辣子蒜羊血
將羊扳倒,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熱血接入盆中。用馬尾籮濾去雜質,倒進同量的食鹽水,細棍攪之,勻,凝結成塊后改切成較小的塊,投開水鍋煮,小火血固如嫩豆腐,撈出,呈褐紅色,舌舔之略咸。 至此羊血制成,可泡在清水盆里備用。
清晨,或是傍晚,食攤安在小巷街頭,擺設十分簡單,一個木架,架子上是各類碗盞,分別放在鹽、醬、醋、蒜水、油潑辣子、香油。木架旁是一火爐,爐上有鍋,水開而不翻滾,鍋里煮的是切成小方塊的羊血。羊血撈在碗里,并無許多湯,加各類調料便可下口了:羊血鮮嫩湯味辣、嗆、咸,花椒、小茴香味竄撲鼻。
咸陽有一人,可以說什么的都不缺,只是缺錢;也可以說什么的都沒有,只是有病。病不是大病,體弱時常感冒。中醫告之:每日喝人參湯半碗,喝過半月即根除感冒。此人拍拍錢包,一笑了之。賣辣子蒜羊血的說:買羊骨砸碎熬湯每早喝一碗;再每晚吃羊血一碗吧。如此早晚不斷,一月后病斷。
石子餅
七十年代,關中一農民有冤,地方不能伸,攜此餅一袋,步行赴京告狀。正值暑天,行路人干糧皆壞,見其餅不餿不腐,以為奇。至京,坐街吃之,市民不識何物,農民便售餅雇人寫狀,終于冤案大白。農民感激涕零,送一餅為其明冤者存念。問:何餅?說:石子餅。其餅存之一年,完好無異樣,遂京城嘩然。
此餅制作:上等白面,搓調料、油、鹽,餅胚為銅錢厚薄。洗凈的小鵝卵石在鍋里加熱,餅胚置石上,上再蓋一層石子,烘焙而成。其色如云,油酥咸香。
同州人尤擅長此道,家家都有專石子,長年使用,石子油黑錚亮。據傳,一家有二十多年的油石子,到六十年代,遭災,無面作餅,無油炒菜,每次熬蘿卜,將石子先煮水中便有油花,以此煮過兩年。
錢錢肉
此肉知道的人多,品嘗的人少,據說,即使在盛產的西府,一縣之主每年也只有支配一個正品的.權力。一般人便只能享用到此肉的下品了。
下品者,臘驢腿。將失去役力的驢,殺之,取其四腿,掛架景晾冷,淋盡血水,切塊,分層入甕,每層加土硝、食鹽,最后壓以巨石。越旬日取出,掛陽光下曝曬,等其變干,再以石塊反復壓榨,排盡水分,用松木水加五香調料煮熟。取出,用驢油及煮肉之原汁摻和,再加溫,肉塊在油湯中提提浸浸,然后將肉塊晾至呈霜狀之色。
人言:吃五谷想六味。臘驢腿下酒之后,便鼻沁微汗,口內生津,故猜錢錢肉的正品不知何等仙品六味!錢錢肉正品據說更味美,且補虛壯陽,但卻不是一般人所能吃到,因其價昂且要有地位才能買到。
錢錢肉正品何物炮制?猜。
臘羊肉
1900年,庚子事變,慈禧太后愴惶出逃,避難西安,一日坐御輦經城內橋梓口坡道,聞香停車,問:何處美味?答:鋪里煮羊肉。便饞涎欲滴,派人購買,嘗之大喜,后賞金字招牌:“輦止坡”。
輦止坡的羊肉便是臘羊肉。本是百姓食物,太后竟也輦止;而在這以前,百姓更是早已馬止、步止,故此食品更朝換代數百年流傳不失。
制作此肉一腌:大瓷缸倒入井水,羊肉,帶骨鮮羊肉,皮面相對折疊而放,撒精鹽、芒硝,夏腌一至兩天,春秋腌三至四天,冬腌四至五天,腌到肉里外色紅。二煮:倒老鹵湯多少,倒清水多少,輔花椒、八角、桂皮、小茴香為料,旺火燒開,羊肉下鍋,老嫩分別,皮面朝上,再燒開放鹽,爾后加蓋,武火文火煮四五個小時至肉爛。三撈:撇凈浮油,火壓來滅,燜半小時待湯溫下降,用長竹棍挑肉,放入瓷盤。四潷:肉皮面上平放盤中,用原汁湯沖澆數遍,再小心以凈布揩干。
因為是當年慈禧所留的遺風吧,此肉漸漸進入上流宴席,且趨熱愈來愈甚,已大有攀高枝之德性。近多年更有人以此作后門的見面禮,致使聲名大壞。
錄者聲明:有人曾非議臘羊肉,建議將其開除出小吃之列。但念其畢街巷有賣;況且,以送臘羊肉走后門,罪應在送肉人而不在臘羊肉本身,故不從。
攬 飯
南瓜老至焦黃,起一層白灰的,摘下洗凈切為小塊,于日頭下晾曬半晌。綠豆當年收獲、飽滿锃亮如涂漆的,簸凈淘搓三四次,用溫水浸泡一響,起火燒鍋,綠豆在下,南瓜在上,水與南瓜平齊。以蒸布蒙鍋蓋,小火半晌,揭蓋用鏟子將綠豆南瓜攪混搗為粥狀,即成。
此食做法簡易,重在選料。雖看來不倫不類,食之卻甜而鮮香。
攬飯流行于秦嶺山區,但平日不易吃到。吃則須貴客上門。冬食之可暖胃,夏食之能祛暑。有中醫鑒定:久吃此食,身不出瘡疔,足不得腳氣。
泡油糕
清花水一斤六兩,熟獵油五兩,上等面二斤,水燒開油攪勻形如乳濁狀湯火面成團。涼開水五兩,摻入面團揉搓不已,使溶膠狀為凝膠狀,包餡料入油鍋。炸出,色澤乳白,表皮膨松,形似一堆泡沫,恰如蟬翼捏成。
吃泡油糕,不可性急。性急者,咬一口便咽,易燙前心。糖餡溢流順胳膊到肘部,揚肘用舌舔之,手中油糕的糖餡則又滴下,燙痛后心。
大刀面
最有名的在銅川。
刀:長二尺二寸,背前端寬三寸,背后端寬四寸,老秤重十九斤。
切:右手提刀,左手按面,邊提邊落,案隨刀響,刀隨手移。
面:搓成絮,木杠壓,成硬塊,盤起回性,搟開一毫米厚薄后拎搟杖疊起成半圓形。
藝高者膽大,揮刀自如,面細如絲,水開下鍋,兩滾即熟,澆上干[火覽]肉臊子,一口未咽,急嚼第二口,一碗下肚,又等不及等二碗,三碗吃畢,滿頭熱汗,鼻耳暢通,還想再吃,肚腹難容,一步徘徊,怏怏離去。
銅川出煤,下礦井如船出海,鄉俗有下井前吃長面,以象征拉魂。故至今礦區多集中大刀面館。外地人傳:賣大刀面的多姓關,是關公后世,或姓包,是包公后裔。此言大謬。銅川東關一家賣主,夫姓華,婦姓陳,皆是關公包公當年所殺之人的姓氏。問及手藝,祖傳。再問:先祖出身?則馬場鍘草夫。
油 條
油條為極普通之食品,小說中描寫舊中國工人生活貧困,即言其食“大餅油條”。
油條的原料為:面粉十斤,堿面一兩,食鹽二兩,菜籽油三斤,白礬一兩半。將鹽、堿、礬溶化在六七斤溫水里,后徐徐倒入面內和成絮狀,再扎成面團,窩二十分鐘后再揉和一遍,至面色光亮,再窩。炸時,切面一塊于案板上,捋成長條。有走棰,兩頭細中間粗的物件,搟成寬二寸厚二分的長條片,那么三指頭一蘸,將油條來回一抹,快刀橫剁為若干小條。而小條有陰陽,兩個一疊用筷子一壓,逼使結合,再兩手提起摔打拉長約一尺時,捏緊兩頭入油鍋。
其做法真令人想起包辦婚姻,但經油一炸,兩根面條相纏相粘,合二為一,活該是先結婚后戀愛了。
吃油條必喝豆漿。西安北大街一賣主講:來他店里的食客多為夫婦,一人一碗漿,兩根油條,而常有一男一女買兩碗漿一根油條的,你吃半截,我吃半截,這必為少男少女,初戀情人
圪 坨
圪坨,陜北語,關中稱麻食、猴耳朵。以蕎面為料,掐指蛋大面團在凈草帽上搓之為精吃,切厚塊以手揉搓為懶吃。圪坨煮出,干盛半碗,澆羊肉湯,乃羊腥圪坨。
吃圪坨離不開羊肉湯,民歌就有“蕎面圪坨羊腥湯,死死活活緊跟上”之句。
圪坨是一種富飯,羊肉湯里有什么好東西皆可放,如黃花、木耳、豆腐、栗子。
此物有一秉性:愈剩愈熱愈香。但食之過甚則傷胃,切記。
甑 糕
甑糕,用甑做出的糕也。甑為棕色,糕有棗亦為棕色,甑碗小而粗瓷,釉舟為棕色,食之,色澤入目,和諧安心。
做甑糕在四關:一泡米,米是糯米,水是清水,浸一晌,米心泡開,淘洗數遍,去浮沫,瀝水分。二裝甑,先棗子,后米,一層鋪一層,一層比一層多,最后以棗收頂。三火功,大火煮半晌,慢火煮半晌。四加水,一為甑內的棗米加溫水,使棗米交融,二為從放氣口給大口鍋加涼水,使鍋內產生熱氣沖入甑內。吃甑糕易上癮。有一作家,黎明七點跑步,八點赴甑糕攤吃三碗,返回關門寫作至下午四點方停歇,數年一貫,寫書十年,體壯發黑眼不近視。
柿子糊塌
吃在臨潼。
臨潼有火晶柿,火如火,亮如晶,肉質細密,且無硬核。吃一想二,飽一人思全家。但季節有限,又不易帶,遂柿子糊塌應運而生。
將軟柿去皮摘蒂,放面盆中攪拌成糊,加入面粉,即為柿子面糊。
用鐵片做手提,外凹中凸邊高二公分。
手鏟將面糊攤入手提,一起入油鍋,炸;面糊熟至五成,脫手提漂浮,翻過,炸;如此數次兩面火色均勻即可食之。
但買者多有不忍吃的,顏色太金黃可愛,吃在口,又不忍細咬,半囫圇下肚,結果有燒了心的。
臨潼人炸的糊塌味最佳,油鍋前常圍滿人,便有一光棍只看不買,張大口鼻吸味,竟肥頭大耳。
賈平凹《真品》原文賞讀
世上再沒有比西安更古意的城市了。那里遺跡多,文物多,老街坊多。連寺廟也多呀,熙熙攘攘的街市上,你常會看到那些穿了黃袍的或木棍兒束了頭發的和尚道士,就感覺他們是遠昔的人,歷史一下子與你拉近。可是,在很窄很窄的小巷里你往一家飯館里走,粗糙的木桌邊就坐著個老頭兒寂然地喝酒,吃一碗羊肉泡饃,你可能輕視他,卻保不準兒這正是
某個大學的教授,或者是飽知天文地理的易學大師。西安這地方,實在是難于理喻,如同進了佛殿,你可以張望,但不容囂張。我和我的老板為著淘尋古字畫來到西安的那天,從河西走廊沙漠上刮起的沙塵正彌罩了古城,雖然太陽還懸掛在空中,已失去了顏色,在城樓的沉沉鐘聲里漸漸殘淡如紙。我們去的是碑林博物館。碑林博物館在海內外聞名,竟原來是一片灰磚灰瓦的老建筑,樸素著,也蕭然著。而圍繞著博物館四周的一棵一棵合抱粗的古樹古松間,則搭就了一排排店鋪,色彩斑斕。這些店鋪都清一色的經營著字畫。據說這里在以前賣買得非常好,曾經有那么多日本的新加坡的游客如蜂如蟻,每一天里銷量超過了二百幅,但現在卻冷清了,因為大量的贗品敗壞了聲譽。我們在店鋪巷里走過的時候,巷外的馬路上正停著一輛旅游車,舉著三角小旗子的旅行社導游員每每往外跑,他可能再難以讓游客在這里購物,沒有得到店鋪的提成,也懶得停下腳來與女店主打情罵俏了。那些鮮艷的女人叫不住導游員,便都笑臉向我們招呼:哈羅,哈羅!
我的老板鼻子大,又是自來卷頭發,鬼曉得怎么就認他是外國人?我的老板說:“請說中國話。”
“你不是外國的?”她們說,“自己人好說呀,進來看呀,看上什么都給你便宜啦!”
我們當然不敢再理,身后飄來的就是一句:傻×!
“西安人怎么這樣?”我的老板氣憤了。
“打著親罵著愛么,”我嘿嘿笑起來,“你聽,你聽……”
我讓我的老板聽的是歌聲:走頭的騾子喲三盞燈,白脖子狗朝南哇哇的聲,趕牲靈的人兒過來了。你是我的哥哥你招一招手,你不是我的哥哥喲你走你的路!這是陜西有名的民歌,在西安,尤其在沙塵籠罩的天氣里,聽起來是別一番的滋味。
“你聽得懂歌詞嗎?”我說,“這是給你唱情歌了。”
我的老板駐腳細聽的時候,歌聲戛然卻止了,回頭四顧,店鋪里的條凳上三個女人湊了一堆說趣話,一個人笑得從條凳上跌下來,而拴在門檻上的一只狗,埋頭啃一根骨頭,吞進去,吐出來,再吞進去再吐出來。歌聲是從哪兒傳來的呢?不遠處的槐樹下,那個老頭已經蹴了許久,現在用手在剔牙縫。可能是風沙鉆進了口里,一只手在牙縫里剔,一只手卻在懷里掏東西,一時掏不出來,站起身了,穿著的是一件袍子,長過了膝蓋。
“口安,”我的老板給我說,“那是個道士。”
“哪兒是道士?”我說,“那藍衫是菜場的工作服。”
藍衫人終于掏出來了,是個破舊的小錄放機。錄放機可能卡了盒帶,他搖著,又啪啪拍打了幾下。
“原來是錄放的,”我有點喪氣,“虧了這么好的情歌!”
“情歌?”藍衫人并不看我們,只是繼續擺弄他的錄放機。“這是窯姐兒拉客哩。”
我們向他走近,并掏出了一支紙煙遞他,他的錄放機突然又出聲了,幾乎是撕帛碎瓶般地一陣激越的鼓點,夾雜著聲嘶力竭的吶喊。“這是‘安塞腰鼓舞曲’么,”我揮了一下拳頭,“多激越的旋律!”
“是嗎,你們喜歡窮人的藝術?”
“窮人的藝術?”
“聽口音是打北邊的首都來的?”
“是從北京來的。”
“噢。”
藍衫人將我遞過的紙煙接住了,沒有吸,卻夾在樹的枝椏上,目光仰視了樹梢。樹梢上正棲了一只鳥,鳥叫了一聲:呀。
“老先生是……”
“鄙吝一銷,白云亦可贈客;渣滓盡化,明月自來照人。”
我和我的老板面面相覷,我們知道我們又遇上了一位高深莫測的人,誰知道他是個什么角色呢?但藍衫人似乎并沒有要與我們交談的意思,他重新蹴下去,靠住了樹,眼睛已經微微閉上了。錄放機里開始飄出另一種樂曲,似乎是《春江花月夜》,但又不似,藍衫人搖頭晃腦了起來。我們不敢造次,遲疑了一會,便往店鋪門口的攤子上翻動那些各種各樣的碑拓。
店鋪里的女人立即迎上來,叫我們是老總。
“我們不是老總。這都是在哪兒拓的?”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守著個碑林,你想想老總!”
“不是說那些碑子都罩了玻璃不準拓了嗎?”
“正是不準再拓了以前拓的才珍貴啊!”
“這一幅歐陽詢《皇甫誕碑》多少錢?”
“今日天氣不好,圖個吉祥便宜給你了,一萬二。”
“給個實價吧,我們要買就買得多哩。”
店鋪外一聲冷笑。這冷笑我和我的老板聽見了,店鋪的女主人也聽見了,她臉上有了明顯的慍怒,順手將柜臺上的一杯殘茶潑出去。我的老板悄悄扯了一下我的衣襟,我扭過頭看見了冷笑正是槐樹下藍衫人的鼻子里哼出來的。藍衫人似乎壓根兒就沒有看著我們在挑選碑拓,也沒有看著我們扭頭在正看他,殘茶的水點濺到了他的藍衫上,他動也不動,又連續地哼著鼻子。我知道,他并不是患有鼻炎,連續的哼鼻子是為了掩飾那一聲冷笑。
“這該不是假的吧?”
“你說對了,別的店鋪是翻刻木板拓下的,只有我們店賣的是真拓。”
女店主越是這般說,我們越不敢買她的貨了。離開攤子,一輛賣鏡糕的三輪車就咿呀咿呀推過來,小販臉上沒表情,只盯著我們,吆喝:鏡———兒———糕!西安的小吃品類繁多,但鏡糕第一回見,瞧了瞧,覺得不衛生,卻對掛在三輪車扶手上的小木牌上的字感興趣了。這一次見面就這么遺憾地結束了,但我們留下了手機號碼,約定三天后郗藍衫安排好地點了隨時通知。我們請郗藍衫去賓館喝茶,他推辭了,矮子要跟他一塊走,他偏讓留下,矮子有點不愿意,他示了個眼神,自個就先走了,一邊走一邊扭頭四顧著,然后便消失在夜幕中。我笑著說:“郗先生怕我們跟蹤他呀。”矮子怔了一下,慌忙說:“這,這……不是的,他急著回去是他弟弟今日得了孫孫,他得過去看看。你猜,是男娃還是女娃?”我說:“男娃?”矮子說:“不對!”我說:“女娃。”矮子說:“呀,你真行,只猜了兩下就猜準了!”
沙塵暴終于是停止了,第三天的早晨下了一場小雨,雨都是黃的,街上的行人全穿了雨衣或撐著傘,而所有的車輛被黃泥雨涂成了迷彩。雨一停,每家洗車房門前排著等待清洗的車輛,司機們三三兩兩站在那里罵天,抱怨著西安之所以做過十三朝國都而后來衰敗至今,都是這風沙所害,要不,秦腔就該是普通話了。又恨著往往把車清洗了,隔二日三日又得下雨,雨是黃湯,又得來洗。西安做什么生意都難,唯獨羊肉泡饃和洗車房把錢賺海啦。我們耐心地等待著郗藍衫的通知,但哭笑不得的是,約定的地點竟是城東南角一條巷頭的公共廁所門口。我和我的老板在那里等了許久,未見到郗藍衫出現,連矮子也沒個蹤影。我安排了我的老板先到附近的夜市上吃飯,西安的`小吃在國內有名,小吃又都集中在夜市上,我們吃過一碗雞蛋醪糟,覺得肚子難受,就進了廁所蹲坑。廁所里光線幽暗,臭氣哄哄,我聽見緊挨的隔檔里有人在大聲努勁,似乎不是在出恭,而有物堵于肛門,憋得命懸一線。如此哼哼哈哈了半天,安靜下來,卻見一只手伸出隔檔,企圖去撿坑臺前一張什么人已經用過的臟紙,而有趣的是恰恰一股陰風從廁所門口刮進來,竟將那張臟紙卷起,飄然落入另一個坑去,隔檔里沉沉地發了一聲恨。這實在是一場巧得不能巧的風的惡作劇,偏偏讓我瞧著,差點笑出來,便將一張手紙遞過隔檔,說:“用這個吧。”那邊的人說聲“謝謝”,站起來了,我看見他竟是郗藍衫!郗藍衫也同時看見了是我,很窘地,立即縮回身子咳嗽,然后提了褲子出了隔檔,將那張手紙又回給了我,說:“是你呀!是你給我的紙嗎?我不用紙的,我用錢揩了!”他走出廁所,一邊走一邊說:“你瞧這墻上,這便是屋漏痕,黃賓虹的線條就這般畫。”我沒有去端詳廁所墻上的臟跡,只疑惑:他真的是用錢揩過了嗎?或許礙于面子壓根就沒有揩!在廁所門口,他又恢復了他的怪異,大聲放著錄放機中的歌曲,在音樂聲中,告訴我巷子盡頭的三十五號是他的朋友家,他已經把真跡從銀行保險柜取來放在那兒,讓我和我的老板過會兒來,說完扭頭便走,那錄放機中開始唱“你要拉我的手,我就要親你的口,拉手手,親口口,咱們黑屹嶗里走。”聲越來越小。
我和我的老板拐彎抹角地在巷子里尋到了三十五號,門是破舊的木門,上面用墨寫了:院中有狗,小心咬你。我忙撿了一塊石頭在手,可一進院就爬梯子,并不見狗,剛剛扔了石頭,還說:是空城計么!一只狗呼地向樓梯沖來,嚇得我的老板險些跌倒。我急喊:“郗先生!郗先生!”狗卻停在樓梯上的平臺上,原來一條鐵繩拴著它,再撲不過來,就汪汪銳叫。是矮子先跑出來,唬住了狗,招呼我們進屋,我們還是不敢動步,一定要矮子將狗用雙腿夾了,才迅速地跑進平臺上的一間屋去。屋小得可憐,除了一張桌子上亂七八糟堆滿了雜物外,幾乎就是那張床了。我的老板不知道該往哪兒坐,我把床上的沒有疊起的臟被子往床根擁了擁,要讓我的老板坐在床頭,沒想褥子下壓著一張百元的鈔票,矮子趕忙拿了,塞給了郗藍衫。
“我那里寬敞,”郗藍衫說,“可這里安全啊!我這兄弟光棍一條,以替人討債為業的,別瞧他個頭小,好勇斗狠,比這狗要兇的!”
“能看出來。”我說,“你需要一個保鏢!”
郗藍衫干笑了一下,就對矮子說:“一回生二回熟,都是朋友了,你給我和兩個朋友留影做個紀念吧。”
我明白郗藍衫的意思,就說:“好么,好么,”讓矮子拿了相機給我們拍照,我的老板偏又將汗手在墻上按了一下,又在一塊破了半邊的鏡子上按了一下,說:“我再給你留個手印!”
郗藍衫有些不好意思了,說:“你這同志有趣,我就愛和有趣的人交朋友。看貨,看貨!”
郗藍衫就拍打了幾下床鋪,將一個報紙卷兒展開,里邊是一個塑料卷兒,又展開,是一個布卷兒。布卷兒雖舊,卻是湘繡,一下一下再展開了,露出畫軸,郗藍衫才從懷里取出一副白線手套,戴上了,說:“你把紙煙掐了。”我把紙煙丟在地上,用腳踩滅。他說:“把放大鏡拿來。”矮子說:“放在哪兒?”他說:“枕頭底下。”矮子翻開枕頭,果然下邊一個硬盒,盒中取出一面鏡子,但枕頭上的塵土揚起來,一股嗆味直鉆鼻子,我就咳嗽,走到平臺上要吐痰。我的老板也咳嗽,跟出來擤鼻涕,悄聲說:“這里就是姓郗的家。”還要再說,矮子就出來了,我們遂返回屋,矮子也跟進來。郗藍衫說:“你們可以附著身看,但不得用手摸,汗手。”慢慢將畫軸展開。
這確實讓我們大開眼界,整幅作品是橫的,幾乎和床一樣長短。在展開的過程中你們似乎能感覺到祥云繞繞,有一股神氣撲面而來,再仔細看去,婉麗處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勁健處奔馬走虺,驟雨旋風。我周身顫抖,且有熱流迅速從丹田涌起,通向腦頂和四肢,回頭看我的老板,他只是呲著眼,呆若木雞,我說:“好啊!寶氣逼人!”我的老板怔了一下,俯身再看,手卻在我腿上掐了一下。我曉得我的老板城府深,不再叫好,拿放大鏡又細照了一遍。
“怎么樣?”郗藍衫說,“要看貨,這就是一眼貨,比碑林博物館的字碑氣韻強了數倍吧?”
“這……怎么這般干凈的?”我說,看著郗藍衫的臉。郗藍衫臉上的麻子是黑麻子,好像沒有洗過。
“算你看出門道了。”郗藍衫說,“你瞧我像個鄉下來城里打工的吧,可我世世代代都是城里人!真的往往看上去像假的,假的倒像真的。西裝革履的顯得氣派,可一身行頭能值幾個錢呢,一萬元穿得什么都有了!”
郗藍衫緩緩地將《圣母帖》卷起來,一層一層包裹,矮子幫著往盒子里裝,一失手,掉在地上,他哎喲叫,忙撿起來,輕輕地拍著,說:摔疼你了,摔病你了。然后說他得和矮子連夜將《圣母帖》送回銀行保險柜去,如果愿意購買,改日再選個時間面議。
《圣母帖》肯定是真品,這已毋庸置疑,我的老板極盡和藹,一定要請郗藍衫和矮子去夜市上吃飯,郗藍衫卻表現得很不情愿,我的老板就說在吃飯時可以先議一議價錢,如果雙方覺得合適,我們就要籌款了,至于安全么,四個人一塊走,會萬無一失的。郗藍衫沉吟了一下,就從桌上取了一把菜刀讓矮子揣在懷里,自個又將一個小瓶裝在口袋。我說:“不用帶酒,夜市上都能買到。”郗藍衫說:“這是硫酸,誰要敢搶《圣母帖》,我就噴他的眼睛!”他說得狠,大家都沒有言傳,他又將裹著真品的紙卷兒裝進一個帆布口袋,口袋里又放著了六七根竹笛,然后斜掛在肩上,四人方下得樓來。
“郗先生是個賣笛子的人了,”為了緩和氣氛,我笑著說,“你這口袋,扔在街上也沒人撿的。”
“狐貍有好皮毛才遭獵殺哩。”郗藍衫也笑了,卻對矮子說:“你急什么呀,讓客人先下樓么。”
他讓矮子斷后,防備的還是我們,我們就知趣地先下樓,我的老板說:“郗先生這么大年紀了住得這么高,越往后就越不方便啊!”
“是嗎?”郗藍衫說,“能走動的時候住高住低都能走,等走不動了,住在一樓你還是走不動。你說什么?這房子可不是我的。”他轉過頭向矮子:“你在這兒住幾年了?”
矮子怔了怔,趕忙說:“五年吧。”
郗藍衫說:“你想不想換個地方?”
矮子說:“誰不想?”
郗藍衫說:“那就包在我身上啦!”
到了夜市,揀墻角的一張桌子,我故意讓郗藍衫坐在里邊,并讓矮子挨著他,我和我的老板坐在對面。夜市上十分熱鬧,那些賣
饣合饹的,煎餅的,粉蒸肉的,涼皮的,踅面的,燈火通明,熱氣騰騰,人聲吵嘈。我們先是感嘆著西安的小吃這么豐富又疑惑西安竟沒有自己的大菜系,郗藍衫就開口了,說:“你知道西安是幾代首都?”我說:“十三。”郗藍衫說:“你想想,十三朝的皇帝在這兒,各省市為了爭寵,都要把他們的飯食貢獻來,久而久之就形成菜系了,西安是一張大餐桌,它只擺貢獻來的美味佳肴,知道了吧?”我說:“知道了。”郗藍衫更得意了,說:“那我再告訴你,西安將來還是要做首都的,歷史上有王氣的地方只有三處,南京、北京和西安,在南京建都是短命王朝,在北京則容易腐化,只有在西安建都的都會強盛啊!”我說:“這可能。”郗藍衫說:“你笑什么?”我說:“我想,西安建都了,我們公司就可以搬過來了,一想到這兒,我就笑了。”郗藍衫看著我,半天不言語,突然說:“我對你這個人有個評價,一個字,只一個字……”我說:“是罵我了吧?”郗藍衫還舉著一個指頭:“一個字:不錯!”我的老板就大笑起來,一邊讓端飯的往上擺八寶稀飯,一邊說再談正經事吧,讓郗藍衫報個《圣母帖》的價格。郗藍衫就一臉嚴肅了,只咬定一個底價,不再松口,幾乎將八寶稀飯吃完,又吃了幾十串烤羊肉串,討價還價總算有了個結果。郗藍衫就環顧四周,低聲說:“你們是識貨人,我也就委屈了。就你給的這個價,有人也出過,還外加一套紅木家具,我是沒松口的。項羽在烏江岸上,和劉邦的兩個將軍碰上了,原本是能搏殺一場的,但他說:我成全二位將軍立功了,把這顆頭獻給你吧,就拔劍自刎……”郗藍衫竟說起漢楚之爭的故事來,我還未醒過神來,聽他再說下去,他卻垂了頭,一顆眼淚叭嗒地濺在桌面上。他的突然落淚,遂使我感動起來,卻不知說什么話好,他終于一抹眼睛,說:“活該《圣母帖》與我的緣分盡了……不說了,喝茶,再來一壺龍井吧!”
我趕忙讓飯攤上的人上茶,一邊起來用指頭將郗藍衫面前桌面上的淚水擦去,一邊說:“這么大的數目,我們得讓公司電匯,三天后怎么樣?”
“不急,十天八天也不急的,你們再考慮考慮,既便不愿意了,那也沒什么。”郗藍衫說,讓矮子尋張紙,“你把電話留給他們,他們考慮妥了來個電話就是。”
矮子一直伸著腦袋看對面街上的一座高樓,有無數的亮的方塊,郗藍衫的話他沒有聽見,郗藍衫又說了一句。
“你賣啥眼哩?”
“我數樓層的。”
“你想住幾層,將來給你弄上。”
“我可不要三室兩廳的,我一個人,我才懶得打掃衛生哩!”
“老婆難道不是你找的,沒出息!像這個模樣的怎么樣?”
一個穿旗袍的高挑個頭的女人從桌前走過,矮子低聲說:“我有個瘸子爛眼的就行啦。”
“要娶就娶個時髦的!”
郗藍衫一臉的麻子都漲紅了,我看著他的臉,想到了猴的屁股,也笑起來。
“這有啥笑的,是瞧著我的麻子吧。”
“郗先生小時候出過麻疹?”
“不是,西安的風沙大呀。”
這一回,四個人全都笑了,惹得周圍飯桌上的人就朝我們看,而路邊柳樹下的兩男一女指指點點了一番,竟落座在我們旁邊的桌上。郗藍衫突然地不笑了,緊了緊身上的口袋,悄聲說:“這些人是沖我來的!”
我抬頭看看來人,說:“哪里會,就算他們不懷好意,咱這么多人的……”
郗藍衫鎮靜下來了,卻說:“誰來我都不怕的,公安局里有我的熟人。”掏出一張名片讓我看。“我一打電話他立馬就來的。”我沒有看那名片。
但是,郗藍衫卻并沒有再坐下去,匆匆離開了夜市,而且他讓矮子廝跟著,拒不讓我們送他。
在自后的三天里,我和我的老板帶著郗藍衫給我們的那些報紙,專門去找了西安字畫界鑒定的權威,權威也已知道《圣母帖》真跡問世的事,并應允在購買時可當場鑒定,以免發生掉包。就這樣,我們籌齊了款額便給矮子撥電話,但矮子的電話卻怎么也撥不通,便再一次去了那條有著公共廁所的小巷去找。
我的老板是個有心的人,他要給郗藍衫帶一份禮品,以示我們的誠意,因為他懷疑郗藍衫是不是反悔了。在買禮品時我們費了思忖,先是要給他買些臘汁羊肉,后又準備買一件西服,結果還是買了個收錄機覺得得體。我們穿過了緯十街,才到了城墻外丁字路口,聽見有很大的吵罵聲,接著就一陣哐哩嘩啦銳響,扭頭看時,路斜對面的一家飯館里,三四個穿著保安服的人在毆打一個人,被毆打者還在強辯,便被提了胳膊腿一下子扔了出來,罵道:“沒有錢你吃毬飯?你吃了飯不給錢?!”
“我有錢的!你以為我沒錢嗎?”被毆打者往起爬,沒爬起來,頭就努力地往上撅,像是個出頭龜,口里的血沫使牙齒也看不見。“我有錢的,我的錢能砸死你!”
保安又跑出來,用腳踩下了他的頭,說:“你有錢?你掏么,一碗面三塊錢你掏出來呀?掏呀!”
“我有……”
“你有你娘的×!”
頭被保安再一次踩下去,踩下去頭又往起撅。保安就在他懷里掏,他捂著懷,藍衫就嘶啦撕開,掏出來的是一個破舊的錄放機,保安將錄放機摔在了地上。
我突然看這是郗藍衫啊,忙呼嘯著跑過去,將保安推開。扶郗藍衫時,他的手里握著那個公安局熟人的名片,要我打電話:“我明白他們為什么打我了,他們要謀財害命……”
我說:“你是欠人家一碗面錢嗎?”
他說:“他們是沖著《圣母帖》的!”
我說:“他們認識你?”
他說:“不認識,可包準兒是他們認識我了,我知道謀算我的人多,賊可以防,防不住的是賊惦記呀!”
我的老板也從馬路那邊過來,我們把他扶起來,他的口鼻血沫模糊,而且額角也有個口子,用手捂了,血水從指縫往出流。我問他家住在哪兒,可以送他回去,或者直接去醫院。郗藍衫已經站起來了,梗著脖子罵已退去的保安:“你瞧著吧,我會收購你們店的,收購了還讓你們當保安,你們給我當狗!”罵著罵著,卻突然甩開了我,盯著我不言傳。
我說:“你怎么啦,感覺頭暈嗎?”
“你們為什么這么關心我?”
我說:“你是被打暈了嗎,認不得我們了嗎?”
他說:“我怎地認不得?把你們燒成灰我也能認得的!可……這么大個西安城,為什么巧不巧就遇上你們在這兒?”
郗藍衫極快地往后一跳,指著我說:“你們和這些保安在演雙簧!你們是來救我嗎,不,不是的,是要尋著我家,或者要把我綁架到別的地方!”
我和我的老板哭笑不得。我還要去扶他,他雙手沾著血揮舞著,我的老板讓我不要扶了,別讓他的血沾在身上,別人還以為是我們毆打了他。我的老板說:“你不就是有《圣母帖》嗎,我們正是籌齊了款要尋你交易的,偏巧在這兒遇上,如果有不良企圖,那次看到真跡時就下手了,是我們打不過你和你的那朋友呢,還是怕你小瓶里裝的自來水?”
“你知道那是水?你知道了當時為啥不挑明,你這么鬼的,你越發有大企圖的,你只是瞅機會,是不是?”
氣得我的老板再不理他。
我瞧見郗藍衫往前走了幾步就摔倒在地上,便又去扶他去醫院,他趴在地上,怎么也不肯起來了。“我朋友不在場,我是不跟你們走的。”
我和我的老板只好離開。當天晚上,第二天和第三天,我們一直給矮子撥電話,仍是撥不通,第四天終于撥通了,讓他趕快找到郗藍衫,還未告訴說郗藍衫被人毆打了,矮子卻開口便說:“生意做不成了,他死了!”
他死了?郗藍衫死了!問郗藍衫怎么就死了,矮子說是被一家飯店的保安打傷后,就趴在飯店外的馬路邊,保安以為僅僅是打了一頓不會出事的,可兩個小時后,他還趴在馬路邊,保安覺得不對勁,出來看時,他因失血過多已昏了過去,急忙往醫院送,還未到醫院就斷氣了。
“那,《圣母帖》呢?”
“誰知道藏在哪兒。”
“真可憐,他把《圣母帖》丟了。”
“是《圣母帖》把他丟了,先生。”
2003年1月10草畢
2003年1月30改完
賈平凹《人病》原文賞讀
我突然患了肝病,立即象當年的四類分子一樣遭到歧視。
我的朋友已經很少來穿門,偶爾有不知我患病消息的來,一來又嚷著要吃要喝,行立坐臥狼籍無序,我說,我是患肝病了,他們那么一呆,接著說:“沒事的,能傳染給我么?”但飯卻不吃了,茶也不喝,抽自己口袋的劣煙,立即拍著腦門叫到:“哎吆,瞧我這記性,我還要出去辦一件事的!”我隔窗看見他們下了樓,去公共水龍頭下沖洗,一遍又一遍。似乎那雙手已成了狼手,恨不能剁斷了去。末了還湊進鼻子聞聞,肝炎病毒是能聞出來的么?蠢東西!
有一位愛請客的熟人,隔天半月就要請一次有地位的人,每一次還要拉我去做陪,說是“寒舍生輝”,這丈夫就又要了我去,夫人當然熱情,但我看出她眉宇間的憂愁,我也知道她的為難了,說,多給我一個碟一雙筷子吧,我用一雙筷子把大盆的菜夾到我的小碟里,再用另一雙筷子從小碟夾到我口里。我笑著對被請的那位領導說:“我現在和你一樣了,你平時是一副眼鏡,我也是一副眼鏡,批文件又是另一副眼鏡。”吃罷了,我叮嚀婦人要將我的碗筷蒸煮消毒,婦人說:“哪里,哪里。”我才出門。卻聽見一陣瓷的破碎聲,接著是攆貓的聲,我明白我用過的碗筷全摔破在垃圾筐,那貓在貪吃我的剩飯,為了那貓的安全,貓挨了一腳。
這樣的刺激是我實在受不了,我開始不大出門,不參加任何集會,不去影院,不乘坐公共車。從此,我倒活得極為清靜,左鄰右舍再不因我的敲門聲而難以午休,遇著那可見不見的人數米外抱拳一下就敷衍了事了,領導再不讓我為未請假的事一次又一次寫檢討了,那些長舌婦和長舌男也不用嘴湊在我的耳朵上是是非非了。我遇到任何難纏的人和難纏的事,一句“我患了肝炎”,便是最好的遁辭。
妻子說:”你總是宣講你的病,讓滿世界都知道了歧視你么?”我的理由是,世界上的事,若不讓別人尷尬,也不讓自己尷尬,最好的辦法是自我作賤。比如我長的丑,就從不在女性面前裝腔作勢,且將五分的丑說成十分的丑,那么丑中倒有它的另一可愛處,相聲藝術里不就是大量運用這種辦法嗎?見人我說我有肝病,他們防備著我的接觸而不傷和氣,我被他們防備著接觸亦不感到難下臺,皆大歡喜,自賤難道不是一種維護自己尊嚴的妙方嗎?
再者,別人問起:你這些年是怎么混的,怎么沒有更多的作品出版,怎么沒有當個**長,怎么沒能出國一趟,怎么陽臺上沒植花鳥籠里沒養鳥,怎么只生個女孩,怎么不會跳舞,沒有情人,沒一封讀者來信是姑娘寫的?“我是患了肝炎呀!”一句話就回答了。
但是,人畢看是群居動物,當我一個人獨處的時候,不僅無限的孤獨和寂寞。惟有父親和母親、妻子和女兒親近我,他們沒有開除我的家籍。他們越是待我親近,我越是害怕病毒傳染給他們,我與他們分餐,我有我的臉盆、毛巾、碗筷、茶幾,且各有固定的存放處。我只做我的坐椅,我用腳開門關門,我瞄準著馬桶的下泄口小便。他們不忍心我這樣,我說:這不是個感情問題。我惱怒著要求妻子女兒只能向我做飛吻的動作,每夜燒兩盤蚊香,使叮了我血的蚊子不能再去叮我的父母,我卻被蚊香熏的頭疼,我這樣做的時候,我的心在悄悄滴淚,當他們用滾開的熱水燙我的衣物,用高壓鍋蒸或熏我的餐具,我似乎覺的那燙泡的,蒸熏的是我的一顆靈魂。我成了一個廢人,一個可怕的魔鬼了。
我盼望我的病能很快好起來,可惜幾年間吃過幾簍中藥、西藥,全然無濟于事。我笑自己一生的命運就是寫作掙錢。我平日是不吃葷的,總是喜是素菜,如今數年里吃藥草,倒懷疑有一日要變成牛和羊。說不定前世就是牛羊所變的吧。
我終于住進了傳染病院。
病院里,我們像囚犯一樣要穿病服,要限制行動于一個極小的院子里,雖然那院墻是鐵制的柵欄,可以看見外邊的人。但看了外邊行人穿著花花綠綠行走,就頓生列入另冊的凄慘。我們渴望自由,每天打過吊針之后,就在院子里看紅紅的太陽,看涌動的云,弄著嘴唇逗引柵欄外樹上的小鳥。小鳥卻飛去了,落下那一根或兩根的羽毛,我們皆如年節的小孩搶拾炮仗一樣去強個不亦樂乎。這行為乎被柵欄外的一個孩子瞧著,那小小的眼睛里充滿了在動物院看籠中動物的神氣,他竟大但地走進了幾步。他的母親,一個肥胖的女人就喊:“走遠點,那是傳染病!”這話使我催然淚下,我只有背過身去,默默地注視著院中的一片玫瑰花,和花壇上的一群黑色的螞蟻。啊,美麗而善良的玫瑰不怕傳染,依舊花紅如血,勇敢的那螞蟻不怕傳染,依舊在為我們表演負重的遠距離運動。這一夜晚我們皆要等到很晚方回去睡,那依舊潔亮的月亮,它隨我們到了柵欄里,它不嫌棄。
我們最不喜歡看到的是柵欄角上的那一個蜘蛛網,它好大,狀若一個筐籃,為我平生之少見。我們傍晚用竿子挑破它,第二天,它又完好無缺,象一個通了電的鐵網,又像是監視我們行動的雷達。我們無可奈何,開始產生了一個惡毒的念頭,后悔我們為什么要聲張自己是肝炎患者?為什么要來住傳染病院?人們在歧視我們,我們何不到人群廣眾中去,要吃大餐飯,要擠公共車。要進影院,甚至對著那些歧視者偏去摸他們的手臉,對他們大哈欠,吐唾沫。那么,我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他們就和我們是一樣的人了!
病院中的人都是面黃青黃,目光空洞,步履虛弱。看著他們的形象我也知道自己的模樣。我們是忌諱用鏡子的,但我們對黃色并不反感,黃在中國是皇帝的象征,于世界也是流行色,于是我們都顯得親熱,在過道上,院子里,誰和誰見了都要點頭,微笑也隨之綻開,似乎我們有緣分,數十年前就認識似的,互相詢問名稱和單位。
醫生和護士是從不喚我們名姓的,直呼床號。世界上叫號的只有監獄和醫院。我先是“+235”后一個病號出院了,我正式成了“235”。“235!235!”這是在買飯了,飯勺不挨著我的碗,熱湯幾次就淋在我的手上,“235!235!”這是護士在送體溫表了,她們查看了溫度便去我們看見的地方洗手,我先是極不習慣這種代號,但后來想通了,“賈平凹”不也是一個代號嗎?雖然235不是爹娘為我起的名字,可現在滿社會不是都在叫“張書記”“李主任”“劉主席”嗎?
我在打吊針的時候,目光一直是看著天花板的,天花板很潔凈,而我還是看出了上面的細小的紋路,并且從這紋路上看出了眾多的魚蟲山水人物。有人說,天花板是病人的一部看不完的書,這話真對。然后我在琢磨“+235”,想有個“+”號,這是不吉利的,因為乙肝之所以是乙肝,就是各項指標是陽性,陽性表示出來就是“+”號。待到正式為“235”了,我思索235為數相加是10,這還好不是13,但10也是不好,應該是 9 恰好,圍棋的最高段位不就是9 嗎?中國人是愛好【第3句】:【第6句】:9 的,幸喜有個3 字。
在醫院的西樓角,也即在廁所的旁邊,是有一棵古槐的,古槐的樹叉上白天常見到臥一個貓頭鷹。每到夜里,它就叫了,它一叫,我們都驚慌起來,肯定在第二天,定要抬出去一個的。這不是迷信,一定時貓頭鷹聞著了欲亡人的氣息在鳴叫。大家都走出來,默默地注視著一個裹著床單的軀體出太平間。他永遠無煩惱痛苦。他的毛巾。牙具被拿出來放在窗臺,他的母親,或者他的妻子在地上滾著哭。這時候,有許多蒼蠅在嗡嗡叫,那一個是他的靈魂所變呢?我們無聲的祈禱他靈魂安妥,卻不愿有蒼蠅落在我們身上。從此,我們皆害怕貓頭鷹,但我們沒有一個人敢詛咒它,更沒有人動手打它,甚至連這個念頭都沒有,當一日數次去廁所經過古槐下,都不自覺地往樹杈上看看,那是驚慌的一看,也是盼望的一看,我們在心中默默的向它祈禱,企望它能饒恕了自己,我至此方明白了人人恨閻王卻還給他修廟塑像稱他是閻王的原因,而貓頭鷹也該是稱作爺的,也該是有廟和塑像的。人怕什么,又奈何不了,人就想著法兒去討好,去供奉,這就是上神的產生,貓頭鷹也就是一個神的。
在這個監獄似的.大地里,我們病人是互不歧視的,他同監獄的區別正在這里,犯人是要互相監督互相打小報告而爭取減刑,這是因為他以前曾經“犯”過人,以犯人入獄,只以犯人減刑入獄。我們患了病,并不是企圖犯人,入院的一半是為了自己,一半也是為了不犯了別人,所以我們互相關心,體貼。每有一個出院,我們歡欣慶賀他的康復,也為了自己能治好而高興。每有一個入院,我們多半卻為他傳染了病而悲傷。我們歡迎他的儀式雖不是握手和擁抱,卻提醒他怎樣買飯票,怎樣服藥,怎樣不必悲觀,病友和學友的感情一樣珍貴,有待我們統統治愈出院后,我們在社會上仍可以形成一個關系網,這個關系網是受歧視之下,在生與死的分界線上建立的天長地久的友誼,他比那些互為利用的情網、烏七八糟的網純潔高尚的多。
我們失卻了社會所謂的人的意義,人們卻獲得了嶄新的人的真情,我們有了寶貴的同情心和吝憫心,理解了寬容和體諒,熱愛了所有的動物和植物,體會了太陽的溫和空氣的清新。說老實話,這里的檔案袋只有我們的病史而沒有政史,所以這里沒有猜忌,沒有幸災樂禍,沒有勾心斗角,沒有落井下石,沒有勢力和背棄。我們共同的敵人只是乙肝病毒。男女沒有私欲,老少沒有代溝。不酗酒不賭博,按時作息,遵守紀律,單人單床,不嫖x,貴賤都同樣吃藥,從沒人象官倒那樣嚼藥成性。醫護是我們的菩薩,我們給他們發出的笑是真正從心底來的,沒有虛偽。貓頭鷹是我們的上帝,我們畏懼而崇拜,沒有絲毫的敷衍。我們為花壇中的那一片玫瑰澆水除草,數的清那共有多少花瓣,也記載了多少片落花被我們安葬。那洞穴的螞蟻和檐下的壁虎,我們雖然是壞了肝的人,但我們的心臟異常的好。
據說,在我們中國,患乙肝的是十個人中有一個或兩個的,我們這些人差不多都是在偶然的體檢時發現病的,所以,當我站在鐵柵欄內向外張望那些歧視我們的人群時,總是想:別神氣十足以為你們干凈吧,或許,你們是沒有查出乙肝的病人,我們是查出了乙肝的健康人!中國人這么多,如果逐個檢查一下,這里就是一個多大的世界了,那么,都能來這里呆呆,人際的感情恐怕比鐵柵欄之外要好的多呢。
我們是病人,人卻都病了,我的貓頭鷹上帝!
賈平凹《文竹》原文賞讀
離開我的文竹,到這鬧鬧嚷嚷的城市里采購,差不多是一個月的光景了。一個月里,時間的腳步兒這般踟躕,竟裹得我走不脫這個城市,夜里都夢著回去,見到了我的文竹。
去年的春上,我去天靜山上訪友,主人是好花的,植得一院紅的白的紫的,然而,我卻一下子看定了那里邊的這盆文竹了。她那時還小,一個枝兒,一乍高的來樣,卻微微仄了身去,未醉欲醉的樣子,乍醒未醒的樣子,我愛憐地撲近去,卻舍不得手動,出氣兒倒吹得她裊裊拂拂,是纖影兒的巧妙了,是夢幻兒的甜美了。我不禁叫道:
“這不是一首詩嗎?”
主人夸我說的極是,便將她送與我了。從此我得了這仙物,置在我的書案,成為我書房的第五寶了。她果然地好,每天夜里,寫作疲倦,我都要對著那文竹兒坐上片刻,月光是溶溶的,從窗欞里悄沒聲兒地進來,文竹愈覺得清雅,長長的葉瓣兒呈著陽陰,楚楚地,似乎色調又在變幻……。這時候,我心神俱靜,一切雜思邪念蕩然無存,心里盡是綠的純凈,綠的充實。一時間,只覺得在這深深的黑夜里,一切都消失了,只有我了;我也要在這深深的夜里化羽而去了呢。
她陪著我,度過了一個春天,經過了一個冬天,她開始發了新芽,抽了新葉,一天天長大起來,已經不是單枝,而是三枝四枝,盈盈地,是一大盆的'了。我真不曉得,她是什么精靈兒變的,是來凈化人心的嗎?是來拯救我靈魂的嗎?當我快樂的時侯,她將這快樂滿盆搖曳,當我煩悶的時候,她將這煩悶淡化得是一片虛影,我就守在她的面前,弄起筆墨,做起我的文章了。人都說我的文章有情有韻,那全是她的,是她流進這字里行間的。啊,她就是這般地美好,在這個世界里,文竹是我的知己,我是再也離不得她了。
然而,我卻告別了她,到這鬧市里來采購,將她托付養育在隔壁的人家了。
這人家會精心養育嗎?他們是些粗心的人,會把她一早端在陽光下曬著,夜來了,會又端著放在室里嗎?一天可以辦到,兩天可以辦到,十天八天,一個月,他們會是不耐煩了,把她丟在窗下,隨那風兒吹著,塵兒迷著,那葉怕要黃去了,脫去了,一片一片,卷進那豬圈牛棚任六畜糟踏去了。那么,每天澆一次水,恐怕也是做不到的,或許記得了倒一碗半杯殘茶,或許就灌一勺涮鍋水呢。那文竹怎么受得了呢,她是干不得的,也是濕不得的,夕陽西下的時候,舀一碗水來,那不是凈水,也不是溶著化肥的水,是在瓶子里摳了很久的馬蹄皮子的水,端起來,點點滴滴地滲下去的呢……
唉,我真糊涂,怎么就托付了他們,使我的文竹受這么大的委屈啊!
采購還沒有完成,身兒還不能回去,愁得無奈了,我去跑遍這城的所有花市,去看這里的文竹。文竹倒也不少,但全都沒有我的文竹的天然,神韻也淡多了,淺多了。但是,得意洋洋之際,立即便是無窮無盡地思念我的文竹的愁緒。夜里歪在床上,似睡卻醒,夢兒便跚跚地又來了,但來到的不是那文竹,是一個姑娘,我驚異著這女子的娟好,她卻仄身伏在門上,抖抖削肩,唧唧嗒嗒地哭泣了。
“你為什么哭了?”我問。
“我傷心,我生下來,人人都愛我,卻都不理解我,忌妒我,我怎么不哭呢?”她說,眼淚就流了下來。
哦,這般兒的女子處境,我是知道的:她們都是心性兒天似的清高,命卻似紙一般的賤薄,都易折,皎皎者易污啊。
“他們為什么這樣?他們為什么要這樣?”
我卻淡淡地笑了:
“誰叫你長得這么美呢?”
她卻睜大了眼睛,定定地看著我,有了幾分憤怒;我很是窘了。她突然說:
“美是我的錯嗎?我到這個世上來,就是來作用,貢獻美的。或許我是纖弱的,但我嬌貴,但我任性,我不容忍任何污染!”
我大大地吃驚了:
“你是誰,叫什么名字?”
“文竹!”
文竹?我大叫一聲,睜開眼來,才知道是一場夢了。啊,是一場夢呢?往日的夢醒,使我失落,這夢,卻使我這般地內疚,這般的傷感!我沉吟著,感到我托付不妥的罪過,感到我應該去保護我的責任,我一定是要回去的了,我得去看我的文竹了。
作于1981年1月20日靜虛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