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表為什么不敢北上和曹操一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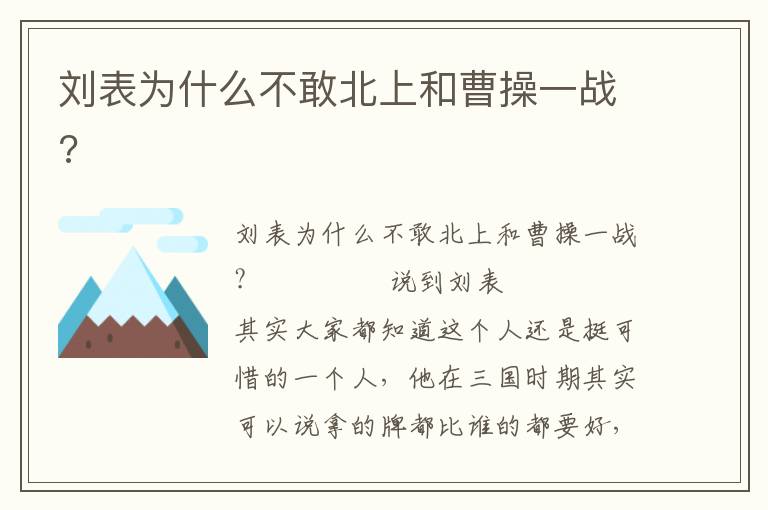
劉表為什么不敢北上和曹操一戰?
說到劉表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人還是挺可惜的一個人,他在三國時期其實可以說拿的牌都比誰的都要好,手下兵多將廣的,但是這個劉表就是有點太安于現狀了,話說他那么厲害為什么卻不敢北上和曹操一站呢?下面我們不妨就著這個事情一起來探討揭秘看看吧!
江漢沃土,四戰之地,帶甲十萬,坐觀天下而不動,即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劉表并非不敢北上和曹操作戰,曾經北上在南陽與曹操發生過沖突,雙方互有勝敗,雖然劉表是以守代功,但是曹操當時也確實奈何不了劉表。至于說北上吞并曹操,劉表確實沒有這個想法。
有人說性格決定成敗,劉表多疑少斷不足以成大事。前半句我很認可,后半句不敢茍同。劉表之敗,在于性格與時代不相符。
頗具雄才
劉表年少時知名于世,名列“八俊”。公元190年“單騎入荊州”,到207年病逝,期間恩威并著,招誘有方,使得萬里肅清、群民悅服。又開經立學,愛民養士,從容自保。遠交袁紹,近結張繡,內納劉備,據地數千里,帶甲十余萬,稱雄荊江,先殺孫堅,后又常抗曹操。
雄踞荊州近十余年,占據四戰之地而未被攻占,劉表之才智可見一斑。試問一個多疑之主又怎么會又如此格局氣魄,將匪亂連連、邊患四起的江漢之地治理的海晏河清呢?說多疑,袁術那才叫多疑,說無斷,袁紹才是無斷,兩者都不過十年就湮滅了。
那么劉表的失敗在于哪里呢?
性格決定命運
從劉表的成名之路和治理荊州的政策,可以看出其頗有合縱之才,甚喜文脈養民,在軍政上以守為攻,不求遠征。這是什么樣的性格特點呢?
往好了說是安宅正路、不喜征伐;往壞了說是偏安一隅、故步自封。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300多年后有一位虎踞河北的豪雄,同樣“不思進取”,后來迫于形勢不情不愿的去支援其他勢力,最終兵敗身亡,這個人叫竇建德;又過了800多年,有一位占據江浙、安徽北和山東部分地區的雄才,同樣“安于一隅”,坐觀成敗,最終被吞并,這個人叫張士誠。
這三個人都有幾點明顯的特質,相對比較仁義,治下百姓安定、財力雄厚、兵精將猛,不喜遠征,他們在有足夠的實力自保之后,都選擇穩固自己的領地,不參與天下紛爭。然而亂世就如鼎中沸水,怎么可能安得一隅清凈呢?
劉表擁有這種安逸的性格,可能是自身原因,也可能是后期的無奈。劉表年老時溺愛庶子,更無斗志,荊州雖然表面上一片祥和,實則暗流涌動,如果可以向天再借五百年,劉表自然有信心鎮住宵小,之后坐觀群雄爭霸,適時出手也未嘗不可。然而自身油盡燈枯,子孫不及自己遠矣,這時算再打江山,經歷不允許,子孫也守不住,還不如安之若素、聽天由命呢。
其實不光是劉表,亂世之中豪雄如云,到最后只有一根獨木橋,又有幾人能走過呢?亂世需要那種“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豪情,需要“一覽眾山小”的情懷,需要“唯我獨尊”的霸氣,而不需要“坐看庭前花開花落,笑看天邊云卷云舒”的閑情。
因此,劉表不北上討伐曹操,主要是因為性格使然,缺乏四下征戰之心,其次后繼無人,無以為繼。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這是古典文化扎根在士大夫腦海中形成的處事哲學,然而這是治世的安身之法,是君子無為不爭的情懷,完全不適合亂世。
亂世有亂世的法則,“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劉表的錯誤在于,站在什么位置,就應該做相應的事情,否則就會被擁護者拋棄,被敵人消滅。
尹禾有詩云:
少而有為稱八俊,單騎入荊笑風云。
功在民安邊匪定,君愿風雨我賞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