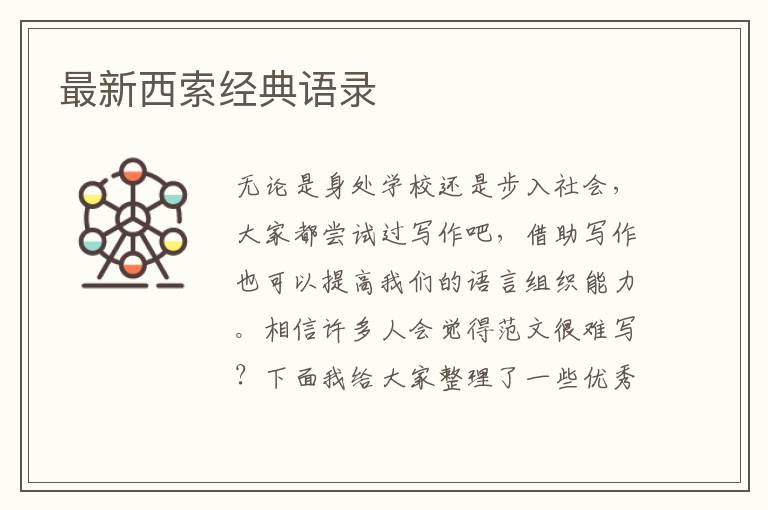與檔案有關的格言集錦50句

與檔案有關散文
很長時間沒更新博客了,有人打電話問我,你玩兒失蹤呢?!
說實話,我這個連撒謊都有些蹩腳的人怎么會玩失蹤呢?!之所以不能更新博客,那得怨我媽,因為我一心不會二用,。
小時候,我媽常常教導我一心不可二用——我是個死心眼,就把這話牢牢記在腦子里了,也照著這話的意思去做了。可沒想到這樣做的結果是在同一時間段內,我只能做一件事。比如,我媽說,你去打一斤醬油,再買一包花椒面回來。我去了。可回來時準得忘一樣,不是忘了打醬油,就是忘了買花椒面。當我媽發現這個問題比較嚴重時,習慣已經養成,想糾正已經來不及了。直到現在,我也是在同一時段內只能干一件事。
我說這事的目的,是想給兩個多月不更新博客找個原由,因為在這個時段里,我正在辦著另外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的起因得從老岳父說起;這是今四月中旬的一個中午,老岳父從雙榆樹公園玩耍過后回來吃午飯,他說在公園里聽人說國家有規定,丟失檔案現在能補。
我聽了之后心里一陣惡心,怒火就從胸口燒到了腦門兒。
我是一九九三年在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區文化館自動離職闖蕩北京的,從一九九六年受聘于《人民文學》雜志社開始,我就不斷地回家鄉尋找我的檔案,這期間,能管得著我的文化館館長換了四任,文化局局長換了五任,人事局局長換了三用任;關于我的檔案,從查查看,到幫助尋找,從宣告檔案丟失,再到請求補辦,在這十二年間,我利用工作之余往返了十一次,所有我認識的當權者,見了就說要請我喝酒,一提補辦檔案的`事就全退了,更有一位當權者對我說,你現在名氣也有,錢也不缺,扯這事干啥,多麻煩呀!
當時也是因為工作太忙,不能長時間的堅持下去,只得一次次敗退回京。
聽岳父這么一說,在憤怒之余,我咨詢了國家人事部、國家檔案局、國家勞動部、國家社會勞動保障部,他們都說丟失檔案各地都能補辦,還可以參加社會保險。接著,我又咨詢了岳成大律師,岳成給了我一個電話,讓我找徐陽律師,說她是這方面的專家,不行讓她跟你去一趟。我把電話打過去,徐陽告訴我說,檔案是單位給弄丟的,又不是你弄丟的,你自己回去找他們辦就行,如果他們說不能辦,你就到法院起訴,這是必須給辦的,除了補辦檔案之外,如果你還有其它要求,那就得到勞動仲裁委員會——不對,你是文化館的,屬于機關事業,應該到當地的人事仲裁委員會。這事百分之百能給你解決。
聽過了,我大喜過旺,喝了點小酒,準備出發。在出發之前,又跟綜合頻道、法治頻道相關的幾個哥們兒打了個招呼,讓他們準備一下,如果家鄉領導不作為,我就叫他們去做一期節目,給他們爆爆光,跟他們魚死網破。
出發前,老婆說,到那別廢話,直接就起訴。我說,還得先禮后兵好,現在文化局跟體委合并了,叫文體局,我哥們兒張書君在那當局長,總不能不打個招呼吧!
于是,我帶上馬原送我的《懸疑地帶》、阿成送我的《歐陽江水綠》、孫春平送我的《江心無島》、聶鑫森送我的《誘惑》、柳建偉送我的《突出重圍》、邱華棟送我的《搖滾北京》和方青卓送我的《情墜洛杉磯》等幾本書,帶上筆記本電腦上路了。我想,回到家鄉,跟現任局長打一招呼,然后上法院一起訴,文體局就得乖乖地去給我補辦檔案,在等待期間,我把這些書都讀完,然后再寫點東西,等事情全辦完了,帶上補好的檔案、帶上養老保險的手續回北京,從此咱也是個有身份的人了。
沒想到,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順利,在補辦檔案過程中,富拉爾基這座家鄉小城里發生太多的故事,從現在開始,我會一心一意的把這些故事一段一段地寫出來,讓各位品味品味小城里的滋味。
檔案丟了散文
辦事難, 事難辦, 到處求人陪笑臉;世態變, 人情淡, 遇事求人的花錢
——題記
天天想、夜夜盼,終于盼到這一天,從2008年3月份單位宣布改制破產到現在,將近4年的時間,期間,大小會開的無數,職工上訪的次數也不計其數。說真的,要不是討口飯吃,象政府機關這樣的高門樓,我們這些貧民百姓,是不敢大搖大擺、厚顏無恥的進出自由。
記得2000年臘月二十四那天上午,經協商,我們三個《酒廠、大修廠、印刷廠》破產單位幾十個人聚集在縣長的辦公室,七嘴八舌的議論著,都希望有關部門抓緊時間,把我們這二百多名職工的失業手續盡快辦妥。其實,大家的要求不高,只要把我們的養老金交到當年年底,按國家政策,下崗職工該得的錢發給我們就行,大家都想早一天和單位脫離關系。
常言說:“有錢能使鬼推磨”,沒錢的日子最難過,沒錢的縣長更做難,這幾年,一任推一任,誰也不想來管這難纏懶手的事情。記得當時縣長說:“沒事,請大家放心,無論如何,非達到你滿意不成,到時候,每人給你們發幾萬元的錢,讓你們個個都笑著回家過舒心的日子”。
也許是領導心情不好吧!他指著一位職工的臉惡恨恨的說:“我就知道,每次上訪就少不了你!”那人也惱火,扯著嗓子說:“你把問題解決了,你看我還會來找你不。”所有的人都面面相覷,嚇得不敢吭聲。
現在,總算有結果了,按國家政策,所有破產單位職工的安置手續,必須在年底前清算結束,事情到火燒眉毛的節骨眼上,本月15號那天,單位通知說:“每人準備八張一寸照片,八張身份證復印件,帶上戶口本去填表,交養老保險金和失業金。”
當我手持各種證件去填表時,我傻眼了,一百多號人都有檔案,就我的檔案丟了,我做夢也沒想到,辛辛苦苦上了一輩子的班,現在是個黑人,沒檔案,領不了失業金暫且不說,更讓人愁心的是,過兩年退不成休咋辦,我慌了手腳,四處打電話追原因。
我87年10月到果酒廠上班,當時,待業青年太多,想有個正式工作真是比登天還難,人事局組織崗前培訓學習,結業后發證,再統一考試擇優錄取,那一年是人事局招收第一批全民合同制工人,果酒廠,植物油廠、化肥廠等幾個廠礦,安置職工200多名,我就是其中一員。
起初,酒廠系商業局下手單位,所有的檔案由局檔案室保管。此后,幾經改革,酒廠統一劃撥給經委領導,最后又原班人馬轉給黃金局。
當年,從商業局往經委轉檔案時,就聽領導說:“你和夏寶娟兩人的檔案死活找不到”,我問咋辦?他們說:“沒事,統一轉過來”,我也沒把此事放在心上,總想沒事,再說一同進廠的26名職工,有權有勢的人,都調到好單位,我沒關系,就在原單位熬到今天,應該沒事。
鬼知道,檔案這么重要,檔案是退休審核時絕對重要證據,沒有檔案,你就有一百張嘴給你說話,理由再充足,還是辦不成退休手續。
從15號(星期三)下午,我開始跑到檔案局、人事局、商業局等單位。先到檔案局,人家告訴我,管檔案的人有事在家休息,星期五才上班,我認識她,打電話求人家幫忙,星期五八點鐘,又去找她,她說:“有難度,不過盡量給你查查,還說,別看這張紙,在有些人手里是廢紙一張,有的人就是花上十萬八萬也難找到”。我想,同時招收一大批工人,應該有文件,信心十足的等待結果,等到的結果是:“實在是找不到,是不是時間說錯了”。
我又跑到人事局辦公室,在人事局,我算真正的見識到,大官的威風,說話氣粗、高高在上、盛氣凌人的模樣,一個有四十多歲、中等個子、白臉、大眼的'干部,說話死難聽,吹胡子瞪眼說:“你的檔案丟了與人事局無關,誰弄丟你去找誰,就這,我已解釋清楚,你也別再問,我一句話也不多和你說。”我說:“我不是來找事,想問問這種情況該咋辦?”嗨!真是活見鬼了,撞見這樣的愣頭青,事情沒問出個原因,還塞了一肚子的氣,我厚著臉,轉身走的時候,甩出一句話:“要不是檔案丟了,我才不會踏你們人事局的高門樓”。
這幾天,我不停地跑來跑去,檔案局、商業局、黃金局、社保所、教育局等單位,見到好多人,不管是能不能辦事,服務行業的人說話都好聽,沒有象人事局那位大干部那樣說話氣粗。
禮拜天兩天,我跑到單位查文件,可是單位的文件也是亂七八糟的一大堆,也查不出有價值的東西,20號那天晚上,我整整一夜沒睡好,滿腦子想的全是,萬一查不到原始文件咋辦,越想頭越痛,沒法子,只好吃個安定片,迷迷糊糊的熬到天亮。
還好,謝天謝地,也許是老天可憐我吧!又托關系、找親戚、提禮品、說好話。星期一下午,總算找到當年招工的花名冊和原始紅頭文件,清楚地看到我名字的瞬間,我高興地幾乎跳起來,一個勁的說:“謝謝、謝謝、吃啥、喝啥、我請客!”都是熟人,他們都替我高興。
雖說我費盡心血找證據、補檔案,期間,也遭到他人的冷言冷語令我惱恨一輩子的人和事,但我不后悔,值得,檔案啊檔案,我的命根子,我后半輩子的生活支柱,不知道,找不到你,我會氣的咋樣?
唉! 說一千道一萬,補好檔案是我最最開心、高興的一件事。天南海北的朋友們,替我高興吧!
土地檔案散文
我們家的豬牛貓狗什么的都有名字。那條毛色黑亮的狗,我們叫它黑狗,那只羽毛黃紅間雜的公雞,我們叫它花雞。我們家的田地也都有名字。我們家種了三畝土地,算起來,大大小小的田地共有十二片。這么多田地,當然得一一給它們取上名字,不然容易亂套。比如,要上地里干活去,卻不說是哪塊地,一家五六個人,有的扛著鋤上山,有的架著犁下河,那成什么樣子?而一說“沙地”或“彎彎田”,都就明白了方位,都朝那里走,事情就簡單多了。
【第1句】:沙地
沙地是我們屋后樟樹邊那塊地的名字。這地沙性重,雨水一浸泡,土壤就要板結。土壤一板結,禾苗就長不好。一年之中,下雨的日子總是很多,因此,為料理好這塊地,讓它長出好莊稼,我們費了不少的勁。我們在這地里栽種的主要是紅薯、小麥或油菜。
這地離我們家最近,一有空閑,譬如飯前或飯后的那點閑余時間,我們總要到這地里看看,或者侍弄點什么。春天,小麥或油菜長起來了,看禾苗是不是齊整,哪塊地方的苗子稀了黃了,得給那兒補施一點肥水,如果禾苗上生了蟲,得噴些藥。夏日,看地里是否有旱象,是否長了雜草,有,當然趕緊設法解決。因為離得近,我們對沙地的照看要比其它田地周到,這地里發生的一切我們也能隨時知道。
現在是五月中旬,沙地成了一塊空地,正閑著。十天前,這地里還是一地油菜。那時,沙地正努力地把快要成熟的油菜養得籽粒更飽滿些。土地養育莊稼,就像母雞孵蛋一樣不聲不響,菜籽角不知不覺間一天天肥碩粗壯起來,壓得菜稈互相扶持著也還是撐不住彎腰欲倒的樣子。那天,我們見菜籽熟得要在陽光里炸開了,就割了回來堆在院壩里。
油菜收割之后,沙地就閑了起來。
但這時,沙地四周其它田地正在忙著長莊稼。左邊是陳海家的一地麥子,麥子一天一天黃起來,趕路似地往收割季節走。右邊是陳大安家的萵筍地,萵筍日漸長高,葉子一日趕一日地闊大起來。上邊那塊地是陳小強家種的油菜,還沒成熟,得等上三五天才能收割。下邊那塊地又是陳海家的麥子……
閑下來的沙地,像一個無所事事的人,感覺是空蕩蕩的。早上,村路邊的野草上都掛著露水,沙地四周幾塊地里的麥苗上、萵筍葉上也濕漉漉的,我們家的沙地里什么也沒有,空空地袒露著一地泥,露水直接落在泥土上,泥土就濕潤了一層。
兩天前,我們從沙地邊路過,見地里零星地生出了一些嫰嫰的野菜。父親說:“土地是閑不住的,沒有禾苗生長的時候,它就要生長野菜、雜草。一年四季,它總是沒有歇息的時候,不像我們人。”
父親說得對,我們人勞累一陣就想歇下來喘口氣,什么也不干,讓時間白白流走那么一段。土地卻是從來不歇息的,它一直都在忙著生長什么,年復一年都這樣。
野菜長起來了,這是沙地在提醒我們不要讓它閑得太久,在催促我們要及時播下另一個季節的種子。
“加緊收麥子吧,收了麥子,快來這里栽紅薯。”我們從沙地邊走過時,父親這樣說。
過兩天,也許就是明天或者后天吧,我們要來翻耕這塊沙地,然后栽紅薯。
【第2句】:麥田
麥田原來叫方田。包產到戶那年,它給分到我們家后,我們就改了名叫麥田。這田也怪,專能長麥子,村里那么多田地,一年要種多少麥子啊,可就數這塊田里的麥子長得好,收成好。別的莊稼,比如油菜、大豆什么的就不成,這些東西在這田里總是長不好,肥施少了,苗子又矮又瘦,肥施得稍稍多了點,苗子就猛勁兒往上竄,又高又壯,但到秋天收獲的時候,收成卻比同樣面積的其它土地少得多,還是欠收。既然麥子長得好,我們就叫它麥田了。
麥田位于村子東邊的一條大路邊。那條路從鄰近的村子伸過來,然后蜿蜒著又伸到另一個村去。每年二月到五月,從麥苗長起來到收麥這一段時間,一撥又一撥的過路人經過這里時,總要驚驚詫詫地說一句:“哈呀,多好的一地麥子!”
麥田是在分給我們家以后才長好麥子的。父親說,大集體生產那會兒,一個隊里二十多號人都來這田里種麥子,可地里老長野草,麥子差不多每年都長得像一地狗尾巴草,麥稈又細又矮,風一吹,輕飄飄的麥穗亂晃蕩。麥田在那個年代出不了麥子,就像一個人耽誤了好多年的青春,什么事也沒干。
后來土地下戶了,父親對我們說:土地生來是長東西的,你在地里種瓜,它就長瓜,種麥它就長麥,種得好,它就長得好,什么都不種,它就什么也不長。一句話,土地是沒有過錯的,有錯的話,那是人的錯。我們明白父親的.意思——麥田分給我們了,我們得好好侍弄。
自從我們家種了這塊田,它就再沒長過野草什么的,一年一年春長麥子,秋收紅薯。當然,村里所有的土地這以后都沒長過野草了,長的都是好好的莊稼。
記得麥田分給我家的第三年,是四月初吧,有天傍晚,父親從地里回來,路過麥田時,他想看看麥子的長勢,繞著田埂走了一圈。麥子長勢當然好得很,父親很滿意。但父親發現一件奇怪的事,麥田中央有一片麥苗搖晃得厲害,像有一陣風專門對著那兒吹。可是那天傍晚根本沒有風,村里風平浪靜的。父親決定看看究竟,側著身子順著地溝進入麥田,一看,原來是一對小男女藏在麥田里親熱。他們不僅把我們的麥子弄得搖晃不已,還壓倒了好大一片。那對小男女一個是鄰村的,一個是我們村的。我們村的那個一見父親來了,嚇得拔腿就跑,像兔子那樣三竄兩竄就不見了,扔下鄰村那女子不管。父親有些生氣,在后邊追著喊:賠我的麥子,狗東西。“那是多好的麥子啊,他們給壓倒了好大一片。”父親回來跟我們說的時候,還是忿忿的樣子。
多年以后,當我讀到《詩經?丘中有麥》的時候,才知道麥田自古就是男女相戀的去處。“丘中有麥,彼留之國。彼留之國,將其來食。”(我在麥田里長久地等著你,遠方的心上人。遠方的心上人呀,我給你帶來了你最愛吃的食物。)不知這位多情的古代女子是否等到了她的心上人,不知這對相戀的男女是否也壓倒了田里的麥子。
【第3句】:新地
新地是我們在桑園壩那片荒野里新開的一塊地。
村子南邊的桑園壩實際上沒有一棵桑樹,好多年來,那一大片土地上只有野草在生長。連片的野草春天長起來,秋天枯萎下去,自生自滅。那似乎是一片沒有用處的閑地,年復一年地荒蕪著。
有一年,父親忽然對這片荒野動了心思,帶我們來這里墾出一片地,然后種上麥子。我們一帶頭,村里許多人家都來這里開荒種地了。現在的桑園壩不再是荒野,一大片田地里種滿了莊稼。
新地剛種莊稼那兩年,我們沒指望有什么收成。剛開墾過來的處女地,泥土是生的,地性野,能長好什么呢?種了幾十年地,我們知道土地跟其它有生命的東西一樣,也有它的生長、發育和成熟的過程,要讓一塊生地長出莊稼,得首先把這片土地養熟,就像把一個瘦弱的女子養得白白胖胖才能育出健康的孩子一樣。我們不斷在田地里忙活,表面看來是在侍弄莊稼,實際上是在養育土地——把生土養熟,把瘠地養肥。新墾的土地長不出莊稼,不是土地不好,而是我們還沒有把它養好養肥。
我們花了整整三年時間才把這片瘠地養肥。我們不斷在地里翻耕,搗碎粘結的土壤,撿出瓦礫,除去草根,施肥,澆水……土地跟我們養的牛羊一樣,馴順而有靈性,時間一長,它明白了我們的心思,漸漸脫去野性,不長野草了,一心一意給我們長起莊稼來。頭兩年,它還像個剛理事的新手,慌手忙腳的,莊稼長得不咋樣,但第三年,它什么都熟慣了,把我們種下的麥子當成自己的麥子那樣養育了,春天,滿地的麥苗齊齊整整、嫩嫩綠綠地茂盛,是全村最好的一地麥。到夏天,新地給我們產下九百多斤顆粒飽滿的麥子,而當初播下的麥種不過百十來斤。
我們終于把這一片野地養肥養熟了。新地成了我們家的一部分。
【第4句】:屋邊地
我們房屋右邊有一塊地,不大,約一分面積,通常只種些家常小菜,比如四季豆、茄子、絲瓜、辣椒、蒜苗。這些蔬菜都是隨時用得上的,種在家門口自有好處,比如,米已經下鍋還沒有摘菜,菜下鍋了還沒有蒜苗,那好,馬上去地里摘幾把回來,——葉子上還有露水在滴呢,鮮炒現吃,方便得很。
但是,距房屋太近了也不好:雞鴨老在地里糟蹋。種子剛下地,它們就溜進去東刨西抓,弄得地里到處是坑;菜苗長起來,葉子還很小,就給它們一嘴一嘴地蠶食,只剩小小的莖在地上禿著。這是很令人頭疼的事。
雞鴨這東西是不講道理的,我們只有哄趕。大聲吆喝,或者拿土塊打。即使它們不在地里,只在地邊轉悠,我們也不放心,非要趕到遠遠的地方不可。我記得,每到種子下地,我們就開始吼雞吼鴨了,天天吼,吼得它們看見人的影子就炸著翅膀跑。
但哄趕也不是良方,因為我們還有別的事要做,不能總在地邊守著。所以后來就采用另外的辦法:用柵欄把整塊地圍住。柵欄是用樹枝和竹片密密地編織而成,有人多高,雞鴨進不去,別的什么東西也不容易進去。這樣,這地就安全了,不再擔心雞鴨或牛羊的打擾,一心一意給我們長菜。到春末夏初,地里綠汪汪一大片,肥胖的葉子把地遮得嚴嚴實實,而絲瓜的藤蔓,一條一條牽到柵欄上,晃眼一看,仿佛是干枯的樹枝又復活了,長了那么多鮮活的嫩葉。再過些日子,張著嘴的絲瓜花就喇叭一樣繞著菜地嗚哇嗚哇吹起來。
菜地里那樣熱鬧,雞鴨們是很羨慕的,在柵欄外面伸著長長的脖子張望,它們走過來走過去,心里七上八下不能安靜。那樣子叫人好笑,又有些可憐。
到秋天,這些家常小菜敗勢之后,我們就在這地里栽種灰菜。灰菜的學名叫磨芋,這是一種懶莊稼,雞鴨也不感興趣,我們就讓它自己長,忙別的活去。這時的柵欄還在地邊圍著,不過沒什么實際用處了,日曬雨淋,慢慢就朽壞了。
第二年春天,我們又在這地里種小菜,同時把壞了的柵欄拆除,重做了新的柵欄。
年年都這樣。一塊地,每年修一圈結實的柵欄把它圍著,我們從不覺得麻煩。
【第5句】:旱地
這是我們屋后山包上的一塊地,呈葫蘆狀。因為地勢較高,又沒有水源,常年干旱,所以叫它旱地。
這地我們秋天種小麥,夏天種稻子。收成當然不好,旱得兇的那一年,禾苗枯得像一地茅草,連種子都收不回來。所以每遇天旱時,我們就為這地擔心。
為了解決干旱的問題,有一年,父親想出一個辦法,就是在地邊挖一個坑,用來蓄水。水坑的位置要比地高,雨天把山水引進去,蓄滿,到地里旱起來的時候,就把水放進地里灌溉。水用完了就再蓄。
但是日曬風吹的,水蒸發得很快,一坑水蓄在那兒,并沒有灌多少到地里,不久就只剩半坑了。這跟把糧食蓄在倉里,把念頭蓄在心里一樣,結果總是這樣的:蓄著蓄著就有好些不見了。
后來我們把坑擴大,裝下的水比原來多了一倍。這樣一般的旱情就能抗過去了。再過兩年,我們又把它擴大,像個不大不小的池塘了,裝下的水更多,這地的灌溉就再不是問題了。
這時候我們擔心的是牛去池塘里滾澡。天熱的時候,不論是黃牛還是水牛,見到水坑就要去滾幾滾,如果是大的堰塘倒沒有什么,我們的水池小,牛到里面一滾,水就四處漫溢,幾條牛一齊滾,那就會水漫山坡,池塘里就剩不下多少了。為這事,我們還跟一些人說了紅臉話,比如三叔,他的牛一次又一次跑到池塘里滾澡,每次都浪出很多水,水白白地流走了,叫人心疼。有一回母親就把三叔喊到池塘邊,指著四處漫流的水忿忿地說:“你看你的牛,把我們這一塘水整得像個啥,這些水是救命的,救谷子的命,也救人的命……天旱了我們拿啥灌苗?你去河里給我擔行不行?”三叔紅著臉無話可說,當即把他的牛狠狠打了一頓。
打一頓又怎樣呢,牛是那個德性,照樣要滾澡的,這家的牛不去那家的牛去。沒辦法,還得靠我們自己好好盯著。
【第6句】:水毀田
桑園子有一個水田,緊傍著山坡,我們叫它傍山田。這田夏天栽稻子,秋天就耕過來種小麥。兩季的收成都不錯。
有一點不好,就是種稻子的時候,只要下大雨,山上的洪水一下來,這田盛不住,田坎的某一段就轟地一聲崩潰了,那個聲音和陣勢,很嚇人。
田坎一垮,水都嘩嘩地流個精光,稻子現時要受旱,秋天要減產,所以每次山洪過后,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趕緊把田坎修好。修田坎不是輕松活,需得先用石頭在崩潰的外圍碼一道矮墻,再拿泥土把缺口筑起來。如果崩潰的只是一小段,也費不了多少事,小半天就能弄好,如果口子又大又長,那就費工夫了,兩個人干一整天也不一定能修好。
偶爾一次倒也沒啥,問題是,隔兩年就要給沖垮一回。上次是這里垮,下次是那里塌。
我們想過不少辦法。比如把山上的堰渠理好,將山水引開,使其不往田里流。但洪水大了,堰渠也會給沖壞,山水還是下來了。比如把田坎加厚筑高,但要是雨下得太大,大到山體都滑坡了,這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該垮還是要垮。
沒辦法,只好隔兩年修一次田坎。
【第7句】:漏水田
這田在風包嶺。這田有個毛病,隔那么幾年,突然就關不住水。特別是五六月份的時候,稻谷長得正好,田里也蓄了滿蕩蕩的水,可是才過一月半月,水就悄無聲息地少了一大截。說蒸發吧,哪有蒸發得這樣快的?說流走了吧,又不見一絲痕跡。找不出原因。
找不出原因,父親就猜測:這田的某個地方有暗洞,水從暗洞里流走了。暗洞可能是黃蟮鉆的,也可能是地鼠鉆的。但那洞到底在哪里?找不到。
找不到,就拿鋤頭把田邊、田埂密密實實地筑過一遍,希望這樣能夠碰巧把漏洞砸實。但總是白費工夫,水還是不知不覺少下去。
正是稻秧拔節的時候,眼看著田里的水一天天少下去,又無技可施,心里干著急。
如果這個時候下雨了,就把快要干涸的稻田蓄滿水,滿得都要溢出來的樣子,這樣維持到稻谷成熟,還無大礙。如果天旱,老不下雨,那就只好看著稻田干下去,看著禾苗枯萎,最后看著糧食大大減產。真叫人心痛。
到下一年耕田栽秧的時候,父親就在這塊田里花很多工夫,一犁耕過來,一犁耕過去,仔細得很,生怕哪里少耕了一犁。所費時間和精力比其它田地要多得多,就說拉犁的牛吧,耕完這田就累得趴在地上起不來,得把草背到地里,堆在它嘴邊,它臥在那兒有氣無力地細嚼慢咽。
父親的意思是,耕得細致一點,好好把泥拌一拌,拌熟了,慢慢的,熟泥也許就能把那暗洞給堵上。
也許真是這樣,他這么一弄,當年就沒再漏水。第二年沒事,第三年也沒事。你以為可以放心了,但偏偏是這個時候,第四年,突然又漏了。于是又費很多工夫去耕田。
這田,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關《流光》的散文
再后來,他離開以前的工作單位。慢慢地,越來越少喝酒,越來越少應酬。他依舊喜歡動畫片,猶愛《蠟筆小新》;他依舊喜歡講冷笑話,諸如“婦女節”其實是“父女節”。
是誰說的,“女兒是父親前世的情人。”我曾暗暗揶揄這句話,我的眼光才不會這么差。現在我想,這也許是真的。
安意如說:“關于光陰的流轉,是蔣捷說的最美: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我曾深以為然,我和父親,都成熟了。
但我發現,我又錯了。
四十多歲的男人過著二十幾歲年輕人的生活,修補著曾破碎過的好物。聽起來不錯。但是我忘了,父親不是超人。畢竟四十多歲的人啊,畢竟從前很少受過苦啊,畢竟他是從小被寵著的老小啊。
那天晚上下晚自習,媽媽來接我。
“爸爸呢?”
媽媽眼中有一絲無奈和不忍:“他在家睡覺。”
八點四十而已。
“他怎么不來接我!”
“他今天太累了……”
一時之間,我竟喪失了言語功能。
他,太累了。
我卻,一點沒有發覺。
我想笑。他偽裝得太好:他依舊給我編冷笑話;依舊跟我打嘴仗說我腿粗;依舊讓我打他明顯變小的肚子。可是我忽視了,七十歲的爺爺依舊滿頭烏發,爸爸鬢角卻多了隱約的銀絲;他曾號稱有“航空眼”,如今看報卻不得不戴上老花鏡。
歲月真是把殺豬刀。我曾以為我和父親都變成熟了,現在才發現,他不是成熟,是變老。
回到家里,到主臥,看見他趴在床上,背朝天花板,雙臂間抱著枕頭——真是幼稚的睡相。卻情不自禁走到床前,替他蓋好被踢掉的'被子,然后毫不猶豫地離開,跑回自己的房間,用被子把自己蒙起來,先是啜泣,最后泣不成聲。
世間好物不堅牢啊。我剛要和你勾肩搭背,你卻已經變老。
“流光容易把人拋。”這分明是最殘忍的詩句。
如果我可以賄賂一下流光,我倒希望流光把你拋到流光之外,歲月才你身上靜止:四十歲的年齡,二十歲的張揚,六十歲的享受。
你說,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