鼐《游靈巖記姚》原文,注釋,譯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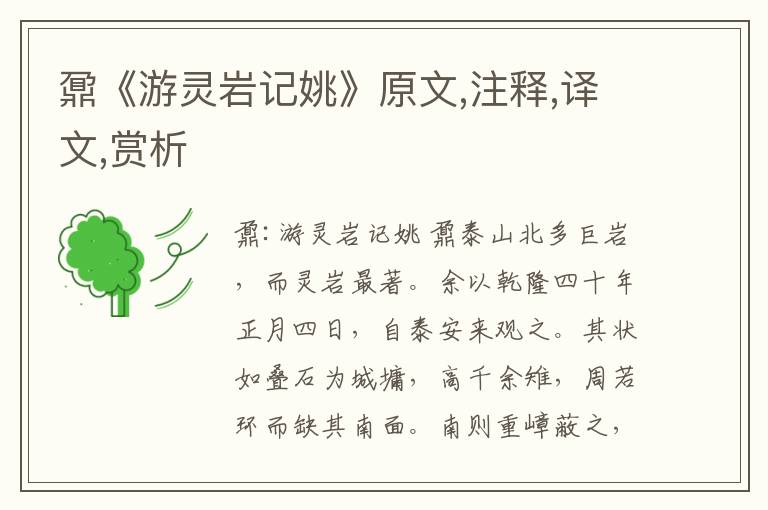
鼐:游靈巖記姚
鼐
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著。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自泰安來觀之。其狀如疊石為城墉,高千余雉,周若環而缺其南面。南則重嶂蔽之,重溪絡之。自巖至溪,地有尺寸平者,皆種柏,翳高塞深,靈巖寺在柏中。積雪林下,初日澄澈,寒光動寺壁。寺后鑿巖為龕,以居佛像。度其高當巖之十九,峭不可上,橫出斜援,乃登。登則周望萬山,殊鶩而詭趣,帷張而軍行。巖尻有泉,皇帝來巡,名之曰“甘露之泉”。僧出器,酌以飲余。回視寺左右立石,多宋以來人刻字,有墁入壁內者,又有取石為砌者,砌上有字,曰“政和”云。
余初與朱子穎約來靈巖,值子穎有公事,乃俾泰安人聶劍光偕余。聶君指巖之北谷,溯以東,越一嶺,則入于琨瑞之山。蓋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濟;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皆泰山之北谷也。世言佛圖澄之弟子竺僧朗居于琨瑞山,而時為人說其法于靈巖。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而靈巖有朗公石焉。當苻堅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樓閣甚壯,其后頹廢至盡。而靈巖自宋以來,觀宇益興。
靈巖在長清縣東七十里,西近大路,來游者日眾。然至琨瑞山,其巖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書以告子穎。子穎他日之來也,循泰山西麓,觀乎靈巖,北至歷城,復溯朗公谷東南,以抵東長城嶺下,緣泰山東麓,以返乎泰安,則山之四面盡矣。張峽夜宿。姚鼐記。
登臨泰山后的第一年(1775),姚鼐又興致勃勃地游覽泰山北向的靈巖。靈巖山在山東省長清縣東南九十里,因四向方正,又稱方山。東晉高僧竺僧朗在此說法,傳說有白鶴翔舞,亂石點頭的靈異,因又有靈巖之稱。后魏孝明帝正光年間法空禪師始建、后來成為全國著名的四大寺廟之一的靈巖寺在此。
靈巖不比泰山,泰山雄渾壯麗,景色隨著山勢的增高而各有不同。靈巖則以懸巖峭壁為主體,以形態和布局為主要景架,所以作者采取前后左右、由外而內的全方位掃描。“其狀如疊石為城墉,高千余雉”,以城墻為喻和以數量詞“千余雉”標高,寫出巖石的重疊和高峻。“周若環而缺其南面,南則重嶂蔽之,重溪絡之”,這兩句點出靈巖象個特殊的四邊形:三面是石,一面是山,而山又是重嶂蔽日,溪水環之,這里的“蔽”字與“絡”字,活畫出山勢之高和溪水的盤繞。讀到這里,我們仿佛置身于與世隔絕的境界,這就是靈巖的外觀。接著作者轉入巖內的描寫:“自巖至溪,地有尺寸平者,皆種柏,翳高塞深,靈巖寺在柏中”。看到靈巖的外觀,我們以為它只是重重疊疊、環聳如城的峭巖,現在隨著作者視線轉移,原來巖內還別有洞天:平地處一片蒼松翠柏,古寺就隱于其中。多么神秘的古寺,靈巖寺本來是靈巖的中心景觀,吸引游人主要是它的存在,但它的出現卻是在層層的外圍描寫之后露面的,這就平空給讀者增添幾分神秘感。古寺如何呢?作者沒有細寫,只說“積雪林下,初日澄澈,寒光動寺壁”,話雖簡短,卻既寫出了雪,又表現了古剎的超塵脫俗。從日光與雪光交相輝映中,我們感到周圍是一片銀白世界,沒有這玻璃似的白色世界,是沒有寒光閃動的,而在這白色世界中,見不到人影,聽不到人語,只有古剎靜靜地屹立其中,其情其景不是超凡脫俗么。作者不言雪,而雪景自見,不言境,而境界自出。
寫到這里,靈巖本身已勾勒完畢,接著作者寫它的外圍。“登則周望萬山,殊鶩而詭趣,帷張而軍行”,這是他想方設法攀登懸巖所見,說山象馬狂奔,象帷幕拉開,象軍隊的隊列。這一筆寫出了靈巖自身的位置,它在群山環繞之中,這靈巖之“靈”又增添了靈氣,至此,姚鼐完成了對靈巖的總體描摹。
這篇游記的重點就是這前半段,后半段主要敘述靈巖、琨瑞山的山水流向,朗公谷的興廢沿革,以及向朱子穎介紹游山路線等等,這雖然是游記中有時必須插入的,但在這里,顯然篇幅太多,而且文字也顯得平淡,這是姚鼐游記中常見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