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非十二子篇譯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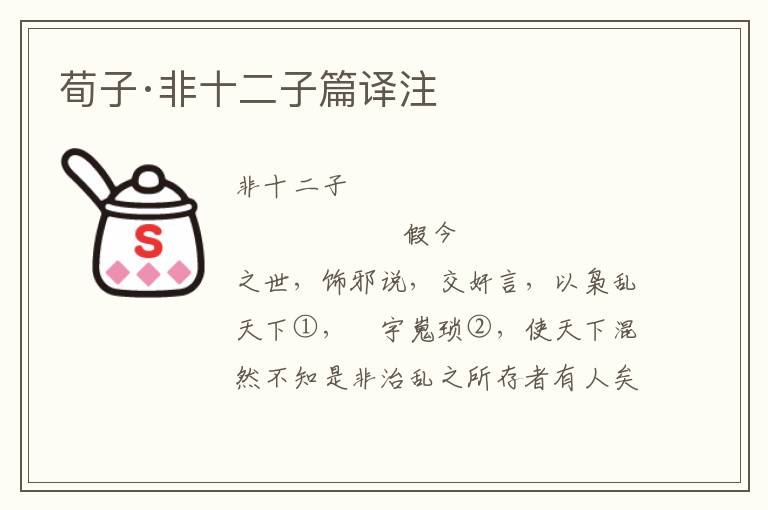
非十二子
假今之世,飾邪說,交奸言,以梟亂天下①,矞宇嵬瑣②,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
[注釋] ①梟:通“撓”,擾。 ②矞(jué決):同“譎”,詭詐。 宇:(xū須),虛夸。嵬:通“傀”(guī歸),怪誕。瑣:卑微。
縱情性,安恣睢①,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它囂、魏牟也②。
[注釋] ①恣睢(suī雖):放縱。②它囂:人名,生平不詳。魏牟:戰國時魏國公子,《漢書·藝文志》將其歸入道家。
忍情性,綦谿利跂①,茍以分異人為高,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陳仲、史鰌也。
[注釋] ①綦谿(qíxī其溪):極深。利跂(qǐ企):離世獨立。利,通“離”。跂,通“企”,立。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①,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②;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钘也③。
[注釋] ①上:同“尚”。大:重視。僈:輕慢。②縣:通“懸”,懸殊。③宋钘(jiān):戰國時宋人,主張禁欲。
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①,上則取聽于上,下則取從于俗,終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②,則倜然無所歸宿③,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④。
[注釋] ①下修: 當作“不循”。② 紃(xún尋):通“循”,順著。反循,反復。③倜(tì惕)然:遠離的樣子。④田駢(pián胼):戰國時齊國人,早期法家代表人物。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①,甚察而不惠②,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
[注釋] ①琦:通“奇”,奇異。②惠:當為“急”字。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①,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②,謂之五行③,甚僻違而無類④,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⑤: 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⑥,孟軻和之⑦,世俗之溝猶瞀儒⑧,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⑨,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于后世⑩,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注釋] ①劇:繁多。②案:通“按”,按照。③五行:即五常,仁、義、禮、智、信。④僻違:邪僻。類:法。⑤案:語助詞。祗(zhī知):敬。⑥子思:孔子的孫子,名伋,字子思。⑦孟軻:即孟子,戰國中期鄒國人,是孔子之后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著有《孟子》。⑧溝(kò寇)、猶、瞀(mào冒):都是愚昧的意思。⑨嚾嚾(huān歡)然:喧囂的樣子。⑩子游:當為“子弓”之誤。
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①,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間②,簟席之上③,斂然圣王之文章具焉④,佛然平世之俗起焉⑤,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⑥,莫不愿以為臣⑦,是圣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注釋] ①大古:即太古。②奧窔(yào藥):堂室之內。奧,屋子的西南角。窔,屋子的東南角。③簟(diàn)席:竹席。④斂然:聚集的樣子。⑤佛(bó勃)然:興起的樣子。佛,通“勃”。⑥成:通“盛”。況:益。⑦“愿”后脫一“得”字。
一天下,財萬物①,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圣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圣王之跡著矣。
[注釋] ①財:成就,成全。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類,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湎然①,雖辯,小人也。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奸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奸心,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奸說。此三奸者,圣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為詐而巧②,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③,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④,飾非而好,玩奸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無法,勇而無憚,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⑤,好奸而與眾,利足而迷,負石而墜,是天下之所棄也。
[注釋] ①流湎:沉湎。②為:通“偽”,虛偽。③惠: 當為“急”字。④辟:通“僻”。⑤大(tài太):同“汰”,驕奢。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圣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后為德。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①,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之人矣②,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③此之謂也。
[注釋] ①恢然:廣大的樣子。苞:通“包”,包括,包容。②訞:通“妖”,怪異。③“《詩》云”句:見《詩·大雅·蕩》。匪,通“非”。時,通“是”。
古之所謂士仕者①,厚敦者也,合群者也,樂富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污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強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為俗,離縱而跂訾者也②。
[注釋] ①士仕:當為“仕士”。下同。②縱:通“蹤”,車跡。訾:通“跐”(cǐ此),走路。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污;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于譽,不恐于誹,率道而行①,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②此之謂也。
[注釋] ①率:循,依照。②“《詩》云”句:見《詩經·大雅·抑》。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①,其衣逢②,其容良,儼然,壯然,祺然,蕼然③,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愨,儉然,侈然④,輔然,端然,訾然⑤洞然,綴綴然,瞀瞀然⑥,是子弟之容也。
[注釋] ①進:通“峻”,高。 ②逢:寬大。 ③蕼(sì 肆)然:寬舒的樣子。④恀(chǐ齒)然:溫順的樣子。⑤訾(zī孜)然:勤勉的樣子。⑥瞀瞀(mào冒)然:不敢正視的樣子。
吾語汝學者之嵬容:其冠絻①,其纓禁緩②,其容簡連;填填然,狄狄然③,莫莫然,瞡瞡然④,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儢儢然⑤,離離然,偷儒而罔⑥,無廉恥而忍謑詢⑦,是學者之嵬也。
[注釋] ①絻:當為“俛”,俯。 ②纓:帽帶。禁:腰帶。 ③狄狄然:跳躍的樣子。狄,通“趯”。④瞡瞡(guī規)然:見識短淺的樣子。瞡,同“規”。⑤儢儢(lǚ呂)然:懈怠的樣子。 ⑥罔:不怕別人議論。 ⑦謑訽(xì gòu 戲詬):同“奊詬”,辱罵。
弟佗其冠①,神禫其辭②,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③。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④,是子夏氏之賤儒也⑤。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⑥,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⑦。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⑧,勞而不僈⑨,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
[注釋] ①弟(tuí 頹)佗:頹唐,形容帽子歪斜。②神禫(chōng dàn 沖淡):通“沖淡”,淡薄,平淡。③子張:姓顓孫,名師,春秋時陳國人,孔子的弟子。④嗛(xián賢)然:口中銜著東西的樣子。⑤子夏:姓卜,名商,春秋時衛國人,孔子的弟子。⑥耆:通“嗜”,愛好。⑦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春秋時吳國人,孔子的弟子。⑧佚:安逸。⑨僈:通“慢”,懈怠,怠惰。
【鑒賞】 終其一生,荀子都在尋找一位能夠一統天下的明君,其著書立說無不由此出發。他在《非十二子》中寫道:想要“兼服天下”,就得遵循長幼尊卑之序,秉持寬容辭讓之禮,甚至還得做到泛愛眾生。這種表面上的與世無爭,底下卻潛伏著欲得人心而王天下的宏圖大志。在荀子立下的“行為規范”中,有一條所謂“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但放到現實里,荀子本人卻未必能做到“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至少在《非十二子》中,我們就看不到他所推崇的包容一切的雅量。
荀子開篇即罵:“假今之世,飾邪說,交奸言,以梟亂天下,矞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言下之意,這些人似乎都是惡貫滿盈,貽害天下,罪無可赦,當立懲不貸。緊接著,荀子一氣批倒它囂、魏牟、陳仲、史鰌、墨翟、宋钘、慎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軻十二子,將他們的學說歸為六種類型,一一指出弊病:“不足以合文通治”、“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荀子衡量諸子學說的唯一標準就是能否為現實政治所用,否則一律歸之為“欺惑愚眾”的“邪說”。篇末,荀子更是怒斥子張氏、子夏氏、子游氏三派儒家后學為“賤儒”,言辭之酷烈,簡直流露出深惡痛絕的意思。郭沫若以為“荀子罵人每每不揭出別人的宗旨,而只是在枝節上作人身攻擊”(《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我們通過《非十二子》這篇檄文也的確感受到了濃重的火藥味。荀子在《榮辱》中曾經說起:“傷人之言,深于矛戟。”現在卻是他自己舉起矛戟,想要進行一場思想上的清敵運動。“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圣王之跡著矣。”荀子身處“諸侯異政,百家異說”(《解蔽》)的亂世,親眼目睹長期分裂格局所造成的山河破敗、禮崩樂壞,使他產生了對于“四海之內若一家”的深切渴望。統一思想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成就統一天下的霸業,故而荀子“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視十二子為阻撓大一統進程的天下大患,斷言“圣王起,所以先誅也”(《非相》)。秦滅六國后,李斯主張“焚書坑儒”,這等極端行為也正顯示出了荀子的思想投影。到了漢代,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儒學正統之先聲,似乎同樣緣自荀子的理論。
相比之下,《莊子·天下》雖然也是先秦學術史著作,卻有著與《非十二子》迥然不同的學術氣度與思想傾向。《天下》把超越百家學說、遍包宇宙萬物的“古之道術”作為學術的最高境界,惜嘆“后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認定“道術將為天下裂”;但同時也對各派學說的歷史起源和自身價值進行了褒貶得當的客觀評論,并肯定了百家之學“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錢鐘書先生曾以《非十二子》與《天下》為例,論述荀、莊兩派的學術思想差異:“荀門戶見深,伐異而不存同,舍仲尼、子弓外,無不斥為‘欺惑愚眾’,雖子思、孟軻亦勿免于‘非’、‘罪’之訶焉。莊固推關尹、老聃者,而豁達大度,能見異量之美,故未嘗非‘鄒魯之士’,稱墨子曰‘才士’,許彭蒙、田駢、慎到曰.‘概乎皆嘗有聞’;推一本以貫萬殊,明異流之出同源,高矚遍包,司馬談殆聞其風而說者歟?”(《管錐編·史記會注考證》)恰如其分地點評了《非十二子》中的偏頗意識與《天下》中的寬容精神。青史為鑒,對于學術思想乃至政治、軍事、商業、科技、藝術等各個領域的百家爭鳴,究竟應當獨尊一統還是兼收并蓄?毋庸置疑,一切粗暴的手段只能給文明帶來毀滅性的災難,而給我們自身留下追悔莫及的感傷。與其執意專斷地恪守己見,面對異己力量謾罵不休,不若虛懷兼顧,去其糟粕而取其精華,因為這將是維護國家持久興盛與政局長期平衡的唯一杠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