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呂氏春秋·貴直》原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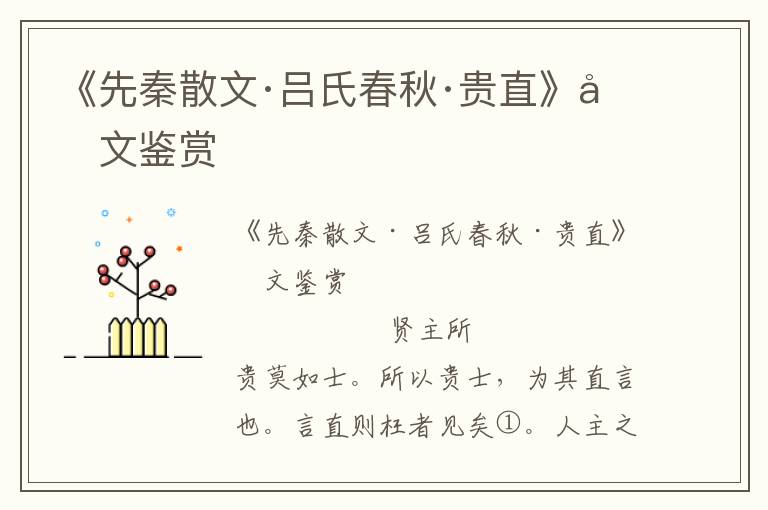
《先秦散文·呂氏春秋·貴直》原文鑒賞
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為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①。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
能意見齊宣王②。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污君。身今得見王③,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④,將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謹乎論于主之側,亦必不阿主。不阿⑤,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
狐援說齊湣王曰⑥:“殷之鼎陳于周之廷⑦,其社蓋于周之屏⑧,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⑨。亡國之音不得至于廟,亡國之社不得見于天,亡國之器陳于廷,所以為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⑩,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11),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纻(12);后出也,滿囹固。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13)。”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14)。”王曰:“行法。”吏陳斧質于東閭(15),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16)。吏曰:“哭國之法斮,先生之老歟?昏與?”狐援曰:“曷為昏哉?”于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17),鮒入而鯢居(18),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19)。殷有比干(20),吳有子胥(20),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22),又新之東閭,每斮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23)!”狐援非樂斮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24),將以救敗也,固嫌于危(25)。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26)。
趙簡子攻衛(27),附郭(28)。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于犀蔽屏櫓之下(29)。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嘆曰(30):“嗚呼!士之速弊一若此乎(31)!”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曰(32):“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艴然作色曰(33):“寡人之無使,而身自將是眾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34),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35),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36),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37),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38),底之以勇(39),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40),五敗荊人,圍衛取曹,拔石社(41),定天子之位(42),成尊名于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于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43),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斗之上(44),桴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為其上死。
【注釋】 ①枉:邪曲。見(xian現):顯露。 ②能意:戰國時齊人。齊宣王:名辟強,戰國時齊國國君,公元前319—前301年在位。 ③身今得見王:當作“今身得見王”。 ④與:猶“用”,采用,聽取。 ⑤不阿:當作“不阿主”。 ⑥狐援:齊臣。他書或作“狐咺”、“狐爰”。齊 王:名地.宣王之子,公元前300年—前284年在位。 ⑦鼎:古代一種禮器,被視為立國的重器、政權的象征。 ⑧社:祭祀土神處。屏:這里指遮蓋神社的棚屋之類。 ⑨干戚之音:武舞的音樂。古代舞蹈分文、武兩種,文舞執羽旄,武舞執干戚。干:盾牌。戚:大斧。游:娛樂。 ⑩大呂:齊鐘名。 (11)太公:戰國時田姓齊國的開國之君,姓田,名和,原為齊康公相,后逐康公,取代姜姓自立為諸侯。 (12)締(chi吃):細葛布。 纻(zhu住):苧麻織的粗布。 (13)洋洋然:猶“茫茫然”,心神不定、無所歸依的樣子。 (14)斮(zhuo濁):斬。 (15)斧質:古刑具。質:古代斬人用的墊板。東閭:指齊國都的東門。 (16)蹶:這里指走路跌跌撞撞。過:訪,見。 (17)人:指淖齒。 (18)鮒(fu付)入:象鯽魚一樣進來。鮒體小,喻恭謹謙卑。鯢(ni泥)居:象鯨鯢一樣住著。鯢體大,吞食小魚,喻兇殘。 (19)為草:變為草莽。史載,齊湣王四十年(公元前284年),燕、秦、韓、趙、魏等國伐齊,齊湣王奔衛。楚派淖齒率兵救齊,遂為湣王相。繼而淖齒殺湣王。 (20)比干:商紂王的叔父,因諫紂,被剖心而死。 (21)子胥:伍子胥,名員(yun),春秋時吳大夫,因諫吳王夫差伐齊而被殺。 (22)若:此。 (23)每:猶“當”,將。參(san 三):動詞,使比并為三。 (24)平論:持平之論,準確恰當的言論。(25)嫌:近。 (26)觸子、達子:皆齊湣王臣。觸子去,達子死,事詳見《權勛》。 (27)趙簡子:名鞅,春秋末晉國正卿。 (28)附:迫近。郭:外城。 (29)犀蔽屏櫓:當作“屏蔽犀櫓”。櫓:大盾牌。(30)桴(fu 浮):鼓槌。 (31)弊:惡,壞。 (32)行人:官名,負責外交事務。胄:頭盔。“免胄橫戈”是手執武器、甲胄在身的臣下謁見君主時的禮節。 (33)艴(fu 扶)然:盛怒的樣子。作色:臉上變色。 (34)說:解釋。 (35)獻公:晉獻公,名詭諸,春秋時晉國國君。 (36)惠公:晉惠公,名夷吾,獻公之子。 (37)遜:逃遁。去:離,距離。絳:指新絳,晉國國都,在今山西曲沃縣西南。 (38)文公:晉文公,名重耳,獻公之子。 (39)厎:通“砥”,磨礪。 (40)城濮之戰:公元前632年晉楚兩國在城濮進行的一次戰爭,結果晉獲全勝。城濮:春秋衛地,在今河南范縣西南舊濮縣南。 (41)石社:古地名。 (42)定天子之位:晉文公元年(公元前636年),周襄王之弟叔帶率狄人伐周,襄王出奔鄭。第二年,晉文公興兵誅叔帶,復納襄王。“定天子之位”即指這件事。 (43)與:與其。(44)上:猶“時”。
【今譯】 賢明的君主所尊重的莫過于士人。之所以尊重士人,是因為他們說話正直。說話正直,邪曲的東西相形之下就顯露出來了。君主的弊病,在于想要聞知邪曲卻又厭惡直言。這就好比堵住水源卻希望得到水,水又從何而至?這就等于輕賤自己想要得到的而尊崇自己所厭惡的,那么自己想要得到的又從何而來?
能意見齊宣王。宣王說:“我聽說你喜好直言,有這樣的事嗎?”能意回答說:“我哪里能做到直言?我聽說喜好直言的士人,家不安在政治混亂的國家,自己不見德行污濁的君主。如今我來見您,家又住在齊國,我哪里能做到直言?”宣王憤怒地說:“真是個粗野的家伙!”打算治他的罪。能意說:“我年輕時喜好直言爭辯,成年以后一直這樣做,您為什么不能聽取鄙野之士的言論,來彰明他們的愛好呢?”宣王于是赦免了他。象能意這樣的人,如果讓他在君主身邊謹慎地議事,一定不會逢迎君主。不逢迎君主,君主得到的教益難道會少嗎?這是賢明的君主所追求的、不肖的君主所厭惡的。
狐援勸齊滑王說:“殷商的九鼎被陳列在周的朝廷上,它的神社被周蓋上廬棚,它的舞樂被人們用來娛樂。亡國的音樂不準進入宗廟,亡國的神社不準見到天日,亡國的重器被陳列在朝廷上,這些都是用來警戒后人的。您一定要好自為之啊!千萬不要讓齊國的大呂陳列在別國的朝廷上,不要讓太公建起的神社被人蓋上廬棚,不要讓齊國的音樂充斥在別人的娛樂之中。”齊王不聽他的勸諫。狐援離開朝廷以后,為國家即將到來的災難一連哭了三天,哭著說:“先離開的,尚可穿葛衣;后離開的,遭難滿監獄。我馬上就會看到百姓倉惶東逃,不知道在哪里安居。”齊王問有司:“國家太平無事卻給它哭喪的,按法令該治什么罪?”有司回答說:“當斬。”齊王說:“照法令行事。”有司把刑具擺在國都東門,不愿真的殺死狐援,只想把他嚇跑。狐援聽到這個消息,反倒自己跌跌撞撞地跑去見有司。有司說:“給國家哭喪依法當斬,先生不知道嗎?您這是老糊涂了呢?還是頭腦發昏呢?”狐援說:“怎么是發昏呢?”于是進一步說道:“有人從南方來,進來時象鯽魚那樣恭順謙卑,住下以后卻象鯨鯢那樣兇狠殘暴,使別人的朝廷變為草莽,國都變為廢墟。歷史上因直諫而被殺的,殷商有個比干,吳國有個伍子胥,現在齊國又將有個狐援。大王既不聽我的這些話,又要在東門把我殺掉,這是要把我同比干、伍子胥比并為三吧!”狐援并不是樂于被殺。國家太混亂了,君主太昏憒了,他哀憐國家和人民,所以才說這樣的話。這些話并不是持平之論,因為想以此挽救國家的危亡,所以必定近于危言聳聽。湣王不采納忠言,卻戮辱直士,這正是觸子棄之而去的原因,也是達子戰敗而死于齊難的原因。
趙簡子進攻衛國,迫近了外城。他親自統率軍隊,可是到了交戰的時候,卻站得遠遠的,躲在屏障和盾牌后面。簡子擊鼓進攻,士卒卻不動。簡子扔下鼓槌感嘆道:“哎!士卒怎么這么快就腐敗到這個地步!”行人燭過摘下頭盔,橫握著戈走到他面前說:“只不過是您有些地方沒能做到罷了,士卒有什么不好!”簡子氣得勃然變色,說:“我不委派他人而親自統率這些士卒,你卻當面說我無能。你說得出道理便罷,說不出道理就治你死罪!”燭過回答說:“從前我們的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就兼并了十九個國家,用的是這樣的士卒。惠公即位二年,縱情聲色,殘暴傲慢,喜好美女,那時秦人襲擊我國,晉軍潰逃到離絳城只有七十里的地方,用的也是這樣的士卒。文公即位二年,以勇武砥礪士卒,所以三年之后士卒都變得堅毅果敢;城濮之戰,五次打敗楚軍,圍困衛國,奪取曹國,攻占石社,重新確定周襄王天子的地位,顯赫的名聲揚于天下,用的還是這樣的士卒。所以說只不過是您有些地方沒能做到罷了,士卒有什么不好?”簡子于是撤去屏障和盾牌,站到弓箭石磐射程以內,只擊鼓一通士卒就全都登上了城墻。簡子說:“與其獲得兵車千輛,不如聽到行人燭過一席話。”行人燭過可算得上能勸諫他的君主了。正當擊鼓酣戰之時,賞賜不增多,刑罰不加重,只說了一席話,就使士卒樂于為他們的君主效死。
【集評】 民國·張之純《諸子菁華錄》:“干將出匣,錯鍔逼人(按:評能意對宣王語)。”。切直而典重,較能意以諧語出之者更上一層(按:評狐援說齊湣王語)。”“屈子行吟澤畔有此哀痛(按:評狐援哭國)。”“《國風》《小雅》之遺,不圖于戰國見之,此以見人心之不死也。”
【總案】 這是《貴直論》第一篇,論述君主要尊重直言敢諫之士,虛心聽取他們的逆耳之言。文章贊揚了狐援、燭過等“直士”的耿介忠貞,同時以齊湣王和趙簡子為例,正反對照,證明君主能否虛心納諫直接關系到功業的成敗、國家的存亡。文章引事論證,語言生動,通過對話刻劃了鮮明的人物形象,能意、狐援、燭過這三個性格不同的“直士”的音容舉止躍然紙上,給人留下較深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