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散文·酈道元·江水·三峽》原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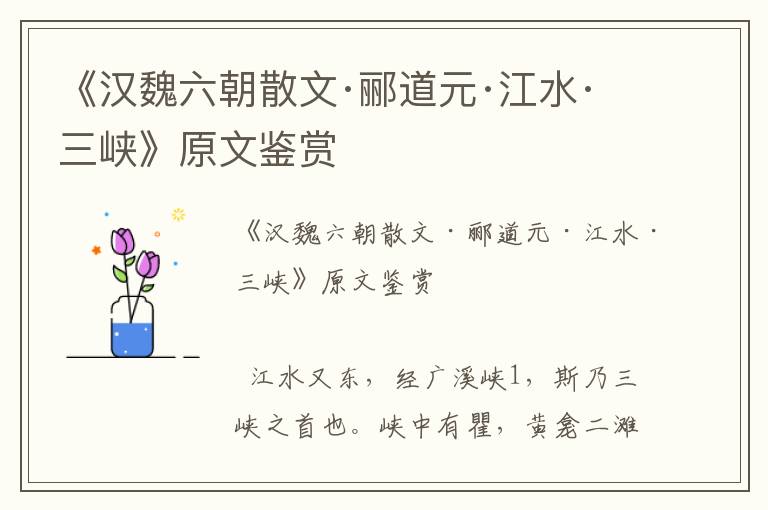
《漢魏六朝散文·酈道元·江水·三峽》原文鑒賞
江水又東,經廣溪峽1,斯乃三峽之首也。峽中有瞿,黃龕二灘,其峽蓋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也2。
江水又東,經巫峽,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3。江水歷峽,東經新崩灘,其間道尾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為名也4。
自三峽七百里中5,兩岸連山,略無闕處6。重巖疊嶂7,隱天蔽日, 自非亭午夜分8,不見曦月9。
至于夏水襄陵10,沿泝阻絕11。或王命急宣12,有時朝發白帝13,暮到江陵14,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15,不以疾也16。
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17,回清倒影18,絕瓛多生怪柏19,懸泉瀑布,飛漱其間20,清榮峻茂, 良多趣味21。
每到晴初霜旦22,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凄異23,空谷傳響,哀轉久絕24,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江水又東,逕狼尾灘而歷人灘。袁山松25曰:“二灘相去二里。人灘水至峻峭26,南岸有青石,夏沒冬出。其石嶔崟27,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須發皆具,因名曰:‘人灘”也。”
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28。既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以江湍紆回20,雖途逕信宿30,猶望見此物。故行都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水路紆深,回望如一矣。
江水又東,逕西陵峽。《宜都記》曰31:“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陜口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象類32。林木高茂,略盡冬春33。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泛泛不絕34。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山松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35,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36,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其疊崿秀峰37,奇構異彩,固難以辭敘38。林木蕭森39,離離藯藯40,乃在霞氣之表。仰囑俯映,彌習彌佳41,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警知己于千古矣42。
【注釋】 1廣溪峽:即今瞿塘峽,在今四川奉節東。2郭景純:即郭璞,字景純,東晉人,長于辭賦,注《山海經》。后:君主。夏后:夏禹。3杜宇:古代傳說中蜀國的一個帝王。4巫峽蓋因山為名:巫峽以巫山而名。巫峽以巫山而名。巫峽巫山均在今四川巫山縣東。5自:有“在”的意思。七百里:為古制,現今計算約二百里。6兩岸連山,略無闕處:兩岸都是連接的山,一點沒有中斷的地方。7嶂:像屏障似的高山。8停午:中午。夜分:半夜。9曦:日光。曦月:日月。10襄:上。陵;大的土山。這句說,夏天水漲,大水凌駕于高山之上。語本《尚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11沿:順流而下。泝:逆流而上。12或:有時。王命:王朝的告示。宣:宣布,傳達。13白帝:城名。在今四川省奉節縣。14江陵:今湖北省江陵縣。15奔:奔星,流星。《爾雅·釋天》注:“流星大而疾曰奔”。又,奔:指奔馳的快馬。御風:駕風。16以:據趙一清《水經注列談》“以”當作“似”。17素湍:白色的急流。18回清:回旋的清波。回清倒影:清光物影倒映其中。19絕:高峻的山峰。20漱:噴射的意思。21良:甚。水清,樹榮,山高,草茂。22霜旦:下霜的早晨。23屬引凄異:連續不斷,音調凄涼怪異。24哀轉久絕:悲哀宛轉,很久才消失。25袁山松:東晉時人,博學能文。官吳郡太守,曾著《后漢書》百篇。《四庫水經注集釋訂訛》作袁崧。26峻峭:急速。27嶔崟:高峻。28成就:指人和牛的開頭形狀,色彩。29江湍:長江的急流。30信宿:猶兩晚。再宿曰“信”。31《宜都記》:晉袁山松有《宜都山川記》,此《宜都記》或系指此。32其石兩句:這兩句意思說,林木高大茂盛,一年四季都是如此。33略盡:歷盡。34泠泠:這里形容猿聲充塞山谷,綿延不盡絕。35書記:書本記載。臨懼,言登臨此境者心懷恐懼。36躋:登。37崿:山崖。38難以辭敘:很難用言語來敘說。39蕭森:樹木高長竦立之狀。40離離藯藯:繁榮茂盛之狀。41彌:愈。習:親近熟悉。42亦當句:言千古以來山水之神乃逢此探幽索勝之人,亦當驚以為知己。
【今譯】 江水又向東流,經過廣溪峽,這地方是三峽的開頭。峽中有瞿塘,黃龕兩個灘涂。這個峽就是過去大禹開鑿以便溝通長江,也就是郭景純所說的“巴東的峽,為夏禹所疏鑿”的那個。
江水又向東流,經過巫峽,這便是杜字開鑿以便溝通江水的那一條峽。江水穿過峽谷,向東經過新崩灘,這一段首尾長一百六十里,之所以稱之為巫峽,是因山得名的。
在整個三峽的七百里中,兩岸山山相聯,沒有一點空缺的地方。層層的巖石,重疊如屏的山峰,遮天蓋日。如果不是正午或者半夜時分,是不能看見太陽和月亮的。
到了夏天,江水猛漲,淹沒了山陵,這時沿江溯流而上是不可能的。偶爾皇帝發布緊急命令,順流而下,有時居然可以早上從白帝城出發,晚上便抵達江陵。這中間有一千二百里路,就算你能駕著流星乘風飛翔,也不會有這么快的。到春冬兩個季節,素白的激流,碧綠的潭水,回旋著清波,映著各種景物的影子。高聳入云的山峰上長著很多奇形的古柏樹。掛在高山上的泉水瀑布在中間飛舞傾灑,那種水清、山高、樹榮、草茂的景色,實在是樂趣無窮。
每到天氣剛剛睛朗的降霜的早晨,林木中已生許多寒意,澗中泉水給人以肅殺之感。常常可以聽到在高峰之上有猿猴哀鳴,一聲接著一聲,扯著長音,格外地凄冷;更還有空無人跡的幽靜的山谷,傳來激蕩的回音,悲哀婉轉的聲浪,很長時間才能消歇。所以漁歌中歌唱道:
巴東地方有個三峽,
頂數那個巫峽最長,
猿猴哀嚎只三聲喲,
人已流淚濕透衣裳。
江水又向東流,流過狼尾灘而又途經人灘。袁山松解釋說:“這兩個灘相距有二里,人灘的水勢特別迅速,南岸有塊青石,夏天水漲淹沒有江中,待冬季時水位低又露出江面。那塊石頭高大峻拔,在數十步大小的范圍里全然量現出人臉的形狀,有的大、有的小,那些明顯的,似乎連須發都很齊備,因此被叫做人灘。
江水又向東流去,流經黃牛山下,有個灘子名叫黃牛灘。在南岸有幾層山嶺重重疊立在那里,在最外一層山的高崖中間有塊石頭,它的形狀顏色很象個人背著柴刀,牽著耕牛,人色黑,牛色黃,形狀色彩非常清楚。這個地方既然是人跡罕至之處,也就沒有辦法仔細考察了。這座山巖已經很高,再加上長江流急曲折,雖然路過這里的船從這里出發已馳行了兩夜,但還是能看到這個黃牛。因此路過這里的人便留下了這樣的歌謠:
早上出發自黃牛,
晚上住宿在黃牛,
走了三天又三夜,
可這黃牛卻依舊。
這是說這段水路的曲折,雖然走出很遠,但向來路一看,卻好象仍在老地方一樣。
江水又向東流,經過西陵峽。《宜都記》說:“江水從黃牛灘向東流入西陵界到峽口有一百多里,山勢和水的流向都很曲折紆回,而兩岸高山重重地屏障著江面,要不是中午或半夜,是看不到太陽和月亮的;岸上的絕壁有的高達千丈,壁上的石頭的顏色狀態,有很多類似某種什么東西的形狀。林木高大茂密,由冬到春四季都如此。猿的叫聲非常凄清,山谷間傳遍回聲,此伏彼起。所說的三峽,這是其中一道。山松說:時常聽說峽中水流很快,書上的記載與口頭的傳說都是講登臨此地令人非常恐懼,以此來告誡游人,沒有人稱道這山水之美的。等我親自來登臨這個地方,一到就感到非常歡喜。這時我才相信耳聽不如親眼所見的說法。那種重迭的山崖、挺秀的高峰、奇異的構造、特別的形態,實在是難以用語言來敘述它的美妙。林木高大森密,繁榮茂盛,而是在霞光霧氣之外。抬頭欣賞那高山遠樹,俯身玩賞江水倒影,越熟悉這風光越覺得美好。在此盤桓一兩天,不覺就會流連忘返。我所親身經歷過的風景,從未見過有如此美妙的。自己既然很高興地得以飽覽這里奇異的景色,山水如果有靈的話,也該為之驚喜,千古以來終于遇到我這個知己了吧!
【集評】 清·劉熙載《藝概·文概》:酈道元敘山水,峻潔層深,奄有《楚辭》《山鬼》、《招隱士》勝境,柳柳州游玩,此其先導耶?
【總案】 劉熙載對酈道元文學成就的評價非常有趣而且警辟。它實際上,一,指出酈的《水經注》在文學史上有承先啟后,繼往開來的地位。這就是上承《楚辭》,下開“柳文”。二《水經注》的文學成就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題材上的,一是藝術風格上的。
先說藝術風格上的,這也是劉熙載說的“奄有……勝境”。《楚辭》本有許多方面可以繼承,看《文心雕龍·辯騷》可知,但劉為什么特標出《山鬼》等篇,這實際上便已指出酈文有煙水迷離中詭奇幽深的風格,這一點《山鬼》已啟先聲,而酈文頗得神髓。
再說題材上的。把自然山水專門作為描寫對象,換言之,成為“模山范水”的專業作家,酈道元是第一人,自然山水可以如此這般的大事描寫,可以情景兼具地這般描寫,這些無疑給了柳宗元深刻地啟發。
當然,話說回來,酈把《水經注》并非當作“純文學”來創造的,他首先是進行地理學的著述,但也正因此,從文學成就來看就難能可貴,《水經注》之所以被當代地理學者看作是“人文地理學”,除了它具有風土民情,歷史掌故的大量記載外,更在于那滲透在字里行間濃郁的詩思情愫,這一點終使它進入文學大國而無愧色。
在酈文之前,文苑中并非沒有寫山水風光的大家,如漢大賦,魏晉南北朝的山水詩,但與酈文不同在一,體裁不同,酈是散文,二,懸想虛擬多于實寫。
柳宗元山水游記的主要成就在于將主觀的情愫引入客觀的描寫,使自然界變成“有情宇宙”,而從如下文字中:“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于千古矣。”難道便聽不到這種聲音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