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原文,注釋,譯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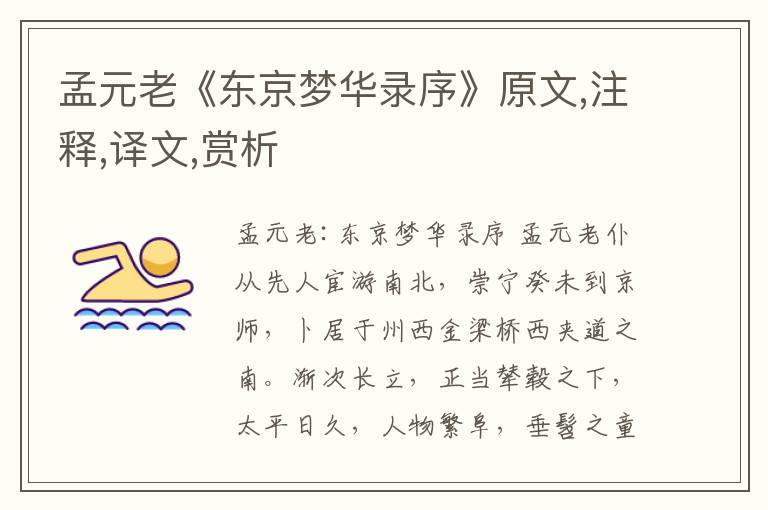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
孟元老
仆從先人宦游南北,崇寧癸未到京師,卜居于州西金梁橋西夾道之南。漸次長立,正當輦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jié)相次,各有觀賞。
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于天衢,寶馬爭馳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街,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qū)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游;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瞻天表則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頻觀公主下降,皇子納妃。修造則創(chuàng)建明堂,冶鑄則立成鼎鼐。觀妓籍則府曹衙罷,內省宴回;看變化則舉子唱名,武人換授。
仆數(shù)十年爛賞迭游,莫知厭足。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來,避地江左,情緒牢落,漸入桑榆。暗想當年,節(jié)物風流,人情和美,但成悵恨。近與親戚會面,談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浸久,論其風俗者,失于事實,誠為可惜,謹省記編次成集,庶幾開卷得睹當時之盛。古人有夢游華胥之國,其樂無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悵然,豈非華胥之夢覺哉!目之曰《夢華錄》。然以京師之浩穰,及有未嘗經從處,得之于人,不無遺闕。倘遇鄉(xiāng)黨宿德,補綴周備,不勝幸甚。此錄語言鄙俚,不以文飾者,蓋欲上下通曉爾,觀者幸詳焉。
紹興丁卯歲除日,幽蘭居士孟元老序。
序,一般總是對作品內容、寫作目的及有關情況的說明。對此,《四庫全書目錄提要》是這樣介紹的:“(孟元老)于南渡之后追憶汴京繁盛,而作此書也。 自都城坊市節(jié)序風俗,及當時典禮儀衛(wèi),靡不賅載。”因此,本書可與后來的《夢粱錄》和《武林舊事》并讀。
本序言簡意賅,文短情長。讀時應深味其事中之情,情中之意,注意作者感情的起伏。
一、起——憶舊都繁盛的歡樂。作者自幼寓居于宮西金梁橋畔,是當時社會生活的見證人,因此皆有真切的感受。同代人趙師俠說:“若市井游觀,歲時物貨,民風俗尚,則所見聞習熟,皆得其真。”因而,此錄堪稱時代的畫卷。雖然,北宋末年,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銳,但汴京仍維持著表面的繁榮。因此,作者不忘當年的“人物繁阜”和一年四季的佳節(jié)相次。元夕、乞巧的良辰美景;教坊池苑、青樓畫閣的新聲巧笑;御街車馬的豪奢,柳陌鋪肆的繁華。還有以相國寺為中心的市易,家家歡樂在簫鼓喧空之中:這是介紹汴京繁盛之一,是從都市生活這點上概述的。同時,又追憶了朝政清明、政通人和方面的情況:
一是元夕或內宴時,教坊弟子進宣德殿表演雜劇。皇帝賞于樓上,百姓觀于樓外,留下了“宣和與民同樂”的情景。二是郊壇祭天祀地的隆重典禮,象征著社稷穩(wěn)固。三是公主出嫁、皇子納妃的盛況。四是大興土木、宴游歡樂的升平景象。五是朝廷取士、武官授職的朝政肅然。這是繁盛之二,是從國家典章儀衛(wèi)上概述的。
二、伏——嘆人世滄桑的悲哀。作者追憶昔日的繁盛,決不是“閑坐說玄宗”似的聊慰寂寞的晚景,而是因為南渡后的“后生”輩對舊都種種已“妄生不然”,“直把杭州作汴州”,這樣長此以往,“論其風俗者,失于事實,誠為可惜。”對此,清人錢曾在《讀書敏求記》中譽曰:“南渡君臣,其獨有故都舊君之思如元老者乎?”的確,他的故都舊君之思,意在讓后生輩從書中引起深切反思,與當時的茍安局面形成強烈對比,使后生之心隨著自己那巨大的感情落差起伏而不漠然。因此,在敘寫昔日盛況的歡樂未斂,而悲痛之淚已灑的悵然中,作者忽然有“華胥夢覺”的哀嘆,使人頓興《黍離》、《麥秀》的遺恨。明人毛晉評說道:“一時綺麗驚人風景,悉從瓦礫中描畫勾相。”一語點破作者的苦心。
“華胥之國”原系道家傳說中的和平安樂之國,作者引為書名,且呼喚鄉(xiāng)黨宿德補綴周備,甚至不惜以鄙言俚語為文,而使上下通曉,足見其呼喚愛國的拳拳心跡。正如前人所言,作者雖有不勝身世之感,但奇情壯采,筆墨橫姿,令人讀之心目俱眩。了解了這一點,即使不讀全書,作者的目的也已達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