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宋遼金元兵法·岳武穆遺文》原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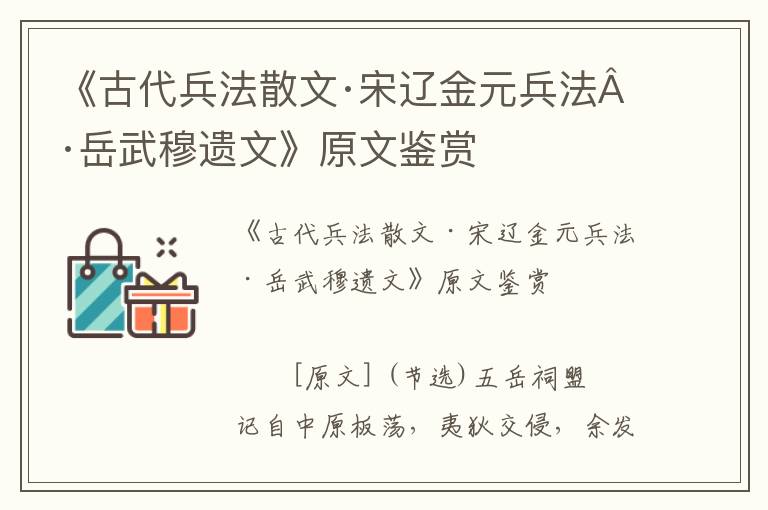
《古代兵法散文·宋遼金元兵法·岳武穆遺文》原文鑒賞
[原文] (節選)
五岳祠盟記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發從軍,歷二百余戰,雖未能遠入荒夷,洗蕩巢穴,亦且快國仇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
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勵士卒,功期再戰,北逾沙漠,喋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圣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元虞,主上莫枕: 余之愿也。
遺 札
軍務倥傯,未遑修候。恭惟臺履康吉,伏冀為國自珍!
近得諜報,知逆豫既廢,虜倉卒未能鎮備,河洛之民,紛紛擾擾。若乘此興吊伐之師,則克復中原,指日可期。真千載一期也!乃廟議迄無定算,倘遲數月,事勢將不可知矣! 竊惟閣下素切不共之憤,熟籌恢復之才,乞于上前力贊俞旨,則他日廓清華夏,當推首庸矣。
輕瀆清嚴,不勝惶汗! 飛再頓首。
乞止班師詔奏略
契勘金虜,重兵盡聚東京,屢經敗衄,銳氣沮喪,內外震駭。聞之諜者。虜欲棄其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杰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
[鑒賞]
《岳武穆遺文》,又名《岳忠武王文集》,南宋岳飛著。今有清乾隆間黃邦寧校刊本,8卷。包括奏疏、書啟、詩詞等,又附年譜、遺事等1卷。
岳飛(公元1103年—公元1142年),南宋名將,字鵬舉,相州湯陰(今河南湯陰縣)人。家貧力學,好《春秋左氏傳》及孫武、吳起兵書。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金人再度南侵,岳飛任少保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大敗敵兵,進軍朱仙鎮(在今開封市南)。秦檜恐飛阻梗和議,一日內降十二道金字牌召還。次年以“莫須有”之罪殺害。岳飛一生征戰,善于領兵治軍。他重視選將,愛護士卒,其軍以“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著稱。金軍嘆服“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岳飛無專門軍事著作遺留,其軍事思想,治軍方略,散見于書啟、奏疏、詩詞等。
一、《五岳祠盟記》是作者轉戰途中,題寫在宜興五岳祠墻壁上的誓詞。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金兵再次進攻常州(今江蘇常州市),岳飛率部迎敵,六戰六捷。金兵統帥兀術逃回建康(今江蘇南京市),岳飛在牛頭山設埋伏,出奇兵大破金軍。兀術逃竄淮西,岳飛乘勝收復了建康城(《宋史》本體)。觀文中“建康之城,一鼓敗虜”諸句,可知是這次勝仗之后所作。此文披肝瀝膽,豪邁雄健,充滿強烈的感發力量。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文章在對從軍以來戰斗經歷的回憶中落筆,氣勢極壯。“中原板蕩,夷狄交侵”寫出當年中原地區異族侵擾,社會動亂的局面。《板》、《蕩》原是《詩經·大雅》反映周代動亂的二篇古詩,后世就用“板蕩”二字形容社會的動亂。作者正是激于民族義憤,投身抗金救國的事業。“發憤河朔,起自相臺”,說自己從河朔相州的家鄉奮起參軍。河朔,指黃河以北的地區。相州而稱作相臺,是因為后漢時曹操在此地建筑了銅雀臺的緣故。古代男子年至二十要束發加冠,表示成年。岳飛從軍在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剛好是加冠的年紀。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己經身歷二百多次戰斗。雖未能盡如人愿,也可以稍慰我心了。筆觸所至,洋溢著一個愛國將士的自豪之情。
接下來,以“今又”二字提起,轉進一層,簡括地寫出收復建康一戰。“一旅孤軍”言軍隊數量很少。《宋史·岳飛傳》謂“(建炎)四年,兀術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可見這次戰斗是從宜興起兵的,所以這里說“振起宜興”。在上面一段中,一面回顧戰績,寫“發憤河朔”,寫“振起宜興”,一面又時時以尚未實現的遠大目標自勉,恨“未能遠入荒夷,洗蕩巢穴”,“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表達出奮勇進擊的強烈愿望。
第二段“故且”一轉,立下哲言:首先“養兵休卒,蓄銳待敵”;隨即“喋血虜廷,盡屠夷種”;最終實現“迎二圣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的抱負。本文一氣貫注,奔瀉而下,處處表現了高昂的愛國熱情,表現了消滅敵人,恢復中原的決心和信心,讀來令人鼓舞,對后世有深遠影響。
二、《遺札》是南宋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偽大齊皇帝劉豫被金人廢黜,當時在抗金前線的岳飛于軍務倥傯中立即致書南宋當權者,建議乘此良機,興師北伐,一舉收復中原。言詞懇切,報國激情溢于辭表。
起首是問候語。“軍務倥傯,未遑修候。恭惟臺履康吉,伏冀為國自珍!”大意說,無奈軍務繁冗急迫,來不及致書問候,惟愿您飲食起居,一切康平,請為國家保重身體。這封信大約是寫給朝廷的一位要員的。故而有“為國自珍”之語,含有推許對方“身系社稷重任”的意味,當然只為表示謙敬的態度而已。
文章層層剖析,條理明晰。“近得諜報,知逆豫既廢,虜倉卒未能鎮備,河洛之民,紛紛擾擾。”劉豫被廢,敵偽遑遑,民心憂憂。不需再著一字,已把形勢說透。劉豫,原任濟南知府,后來降金,金人冊為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縣地),僭位八年,配合金兵攻宋屢遭失利,為金人廢黜而死。“若乘此興吊伐之師,則克復中原,指日可期。真千載一期也!”提出建議。乘敵之敝,吊民伐罪,克復中原,這是非常有膽識的見解。“指日可期”,語氣間充滿自信。“千載一期(遇)”感嘆機會難得,不可坐失。為強調抓住時機對于取勝的重要性,敦促執政早作決策,作者又反面作一假設:“乃廟議迄無定算,倘遲數月,事勢將不可知矣!”真是刻不容緩。廟議,指朝廷商議決策。建議的主要內容已經寫出,為了爭取對方的支持以不誤國事,下面又作一番鼓勵。“素切不共之憤,熟籌恢復之才”,謂對方亦痛恨不共戴天的敵人(金人),而且是謀劃恢復故國大計的賢才。“乞于上前力贊俞(御)旨,則他日廓清華夏,當推首庸矣。”請求對方在皇帝面前悉力支持興師北進的主張。說如果此議為朝廷采納,那么中原收復之日,閣下當推為首功。“力贊俞旨”,把恢復故土說成皇帝的意志,是表敬的婉辭。事實上,宋高宗趙構貪生怕死,又為佞臣迷惑,只圖茍且一日便滿足了,哪里有心談什么恢復故疆?果然,此書寫出后,朝廷并沒有采納岳飛的意見。而作者在信中言“迄無定算”,等等,似意識到進言之難了。結尾以謙敬之語作結。
這篇短簡不過百十字,卻寫得言辭懇切,充滿昂揚健武的氣概。直截了當,屢用感嘆之語,尤其是文字洗煉暢達,可稱軍事范文。
三、《乞止班師詔奏略》是一份珍貴的史料,它對于了解當時宋金兩國的戰略形勢。岳飛的處境及最后被害的原因,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金兵大舉南侵,岳飛率軍經過苦戰,在郾城(今屬河南省)大敗金兵。金兵都元帥宗弼退駐臨潁(今河南省中部),岳飛派遣楊再興率3百騎兵突擊,殺敵2千余人,戰況激烈異常,楊再興戰死,身上中箭百余。后張憲率部增援,擊敗宗弼,追殺15里。宗弼退至潁昌,岳云率騎兵8百與之決戰,步兵從左右兩翼助攻,殺金兵副統帥。接著岳飛親率大軍在朱仙鎮再創敵軍,宗弼退守汴京。朱仙鎮距開封僅45里,且敵軍屢戰屢敗,“銳氣沮喪”。形勢對宋軍十分有利。然而,正當這千載難逢的好時機,宋高宗卻下詔班師。岳飛為此而寫下這篇奏略。作為一位久戰沙場的杰出軍事家,他向皇帝簡略而具體地分析了戰況,指出了宋軍的有利條件:其一,敵軍屢經戰敗,銳氣己喪失殆盡。其二,情報表明,敵軍已不想固守汴京,準備渡河北撤。其三,中原淪陷區義軍烽起,金人統治己搖搖欲墜。其四,宋軍士氣極盛。因此岳飛提出了“功及垂成”的結論。這里的“功”。不僅是指克復舊京,平定中原,還包含著直搗黃龍府的決心。
但是,這篇奏略換來的卻是一道又一道催促班師的嚴令,而一場陷害忠良的陰謀也已經醞釀成熟。岳飛被迫回到京師,遂以“莫須有”之罪名就戮于風波亭,造成了一樁震驚千古的大冤案。這一冤案的真正罪魁禍首,其實不是秦檜,而是宋高宗。他之所以要殺害岳飛,阻止北進,完全是出于一種陰暗心理。一方面,對武將的不信任,乃是其先祖趙匡胤的祖傳家法。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倘如北進成功,迎還被擄去的欽宗,他的皇位又怎么辦?明人文徵明吊岳飛的《滿江紅》詞云:“但徽欽一返,此身誰屬?”正是誅心之論。所以,岳飛這篇奏略對高宗來說,引起的不是歡快之情,而是恐慌之意。因此,它反而催促高宗加快了謀害岳飛的步伐。作為歷史的見證,這篇奏略給后人留下了無窮的遺憾。
從文章本身來說,岳飛當時作為大軍統帥,身系天下,當然無暇細細考究。但它自然而然形成一種特殊的風格。全文不過78個字,卻包含了極其豐富的內容:當前的戰局、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對形勢變化的預見、對皇帝的懇切期待。句句從大處落筆,極其簡練明快,同時顯露了作者既為勝利而興奮、又因皇帝的班師詔令深感不安的復雜心情。真所謂大將風度,烈士情懷。古人常用“擲地作金石聲”稱譽好文章,此足以當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