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師表·諸葛亮》全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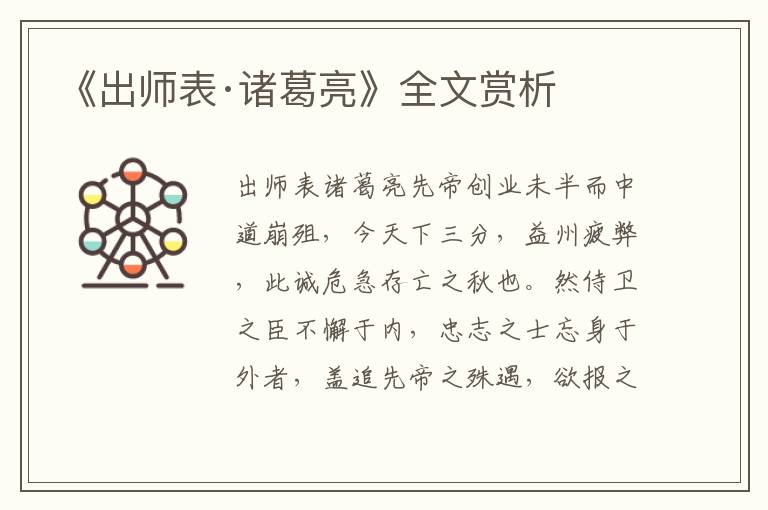
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圣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祎、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愿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后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托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祎、允等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譯文
先帝開創的大業未完成一半,卻中途去世了。現在天下分為三國,我蜀國困苦窮乏,這實在是國家危急存亡的時期啊。不過宮廷里侍從護衛的官員不懈怠,戰場上忠誠有志的將士們奮不顧身,大概是他們追念先帝對他們特別的知遇之恩,想要報答在陛下您身上。陛下實在應該擴大圣明的聽聞,來發揚光大先帝遺留下來的美德,振奮有遠大志向人的志氣,不應當隨便看輕自己,說不恰當的話,以至于堵塞人們忠心地進行規勸的言路。
皇宮中和朝廷里的大臣,本都是一個整體,獎懲、功過、好壞,不應該有所不同。如果有做奸邪事,犯科條法令和忠心做善事的人,應當交給主管的官,判定他們受罰或者受賞,來顯示陛下公正嚴明的治理,而不應當有偏袒和私心,使宮內和朝廷獎罰施法不同。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祎、董允等人,這些都是善良誠實的人,他們的志向和心思忠誠無二,因此先帝把他們選拔出來輔佐陛下。我認為宮中的事情,無論事情大小,都拿來跟他們商量,這樣以后再去實施,一定能夠彌補缺點和疏漏之處,有很大好處。將軍向寵,性格和品行善良公正,精通軍事,從前任用時,先帝稱贊說他有才干,因此大家評議舉薦他做中部督。我認為軍隊中的事情,都拿來跟他商討,就一定能使軍隊團結一心,好的差的各自找到他們的位置。親近賢臣,疏遠小人,這是西漢之所以興隆的原因;親近小人,疏遠賢臣,這是東漢之所以衰敗的原因。先帝在世的時候,每逢跟我談論這些事情,沒有一次不對桓、靈二帝的做法感到嘆息痛心遺憾的。侍中、尚書、長史、參軍,這些人都是忠貞誠實、能夠以死報國的忠臣,希望陛下親近他們,信任他們,那么漢朝的興隆就指日可待了。
我本來是平民,在南陽郡務農親耕,在亂世中茍且保全性命,不奢求出名在諸侯之中。先帝不因為我身份卑微,見識短淺,降低身份委屈自己,三次去我的茅廬拜訪我,征詢我對時局大事的意見,我因此十分感動,就答應為先帝奔走效勞。后來遇到兵敗,在兵敗的時候接受任務,在危機患難之間奉行使命,到現在已經有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我做事小心謹慎,所以臨終時把國家大事托付給我。接受遺命以來,我早晚憂愁嘆息,只怕先帝托付給我的大任不能實現,以致損傷先帝的知人之明,所以我五月渡過瀘水,深入到人煙稀少的地方。現在南方已經平定,兵員裝備已經充足,應當激勵、率領全軍將士向北方進軍,平定中原,希望用盡我平庸的才能,鏟除奸邪兇惡的敵人,恢復漢朝的基業,回到舊日的國都。這就是我用來報答先帝,并且盡忠陛下的職責本分。至于處理事務,斟酌情理,有所興革,毫無保留的進獻忠誠的建議,那就是郭攸之、費祎、董允等人的責任了。
希望陛下能夠把討伐曹魏、興復漢室的任務托付給我。如果沒有成功,就懲治我的罪過,用來告慰先帝的在天之靈。如果沒有振興圣德的建議,就責罰郭攸之、費祎、董允等人的怠慢,來暴露他們的過失;陛下也應自行謀劃,征求、詢問治國的好道理,采納正確的言論,以追念先帝臨終留下的教誨。我將感激不盡。
今天我將要遠離陛下,面對這份奏表,禁不住熱淚縱橫,也不知說了些什么。
作者介紹
諸葛亮(181年—234年),字孔明,號臥龍(也作伏龍,與鳳雛齊名),謚號忠武侯,在世時被封為武鄉侯,后世稱諸葛武侯,瑯玡陽都(今山東省沂南南)人。三國時期蜀漢丞相,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散文家、發明家,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忠臣與智者的代表人物。東漢末年(207年),隱居鄧縣隆中(今湖北襄樊市襄陽區),劉備三顧茅廬時,他在“隆中對”中建議劉備占據荊、益兩州,聯合孫權對抗曹操,形成三足鼎立之后一統江山。諸葛亮任蜀漢丞相期間,勵精圖治,賞罰分明,推行屯田政策,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六出祁山之時,病逝于五丈原軍中,享年五十四歲。發明木牛流馬、孔明燈、諸葛連弩等。通天文,曉地理,有著胸懷坦蕩的大智慧。諸葛亮在后世受到極大的尊崇,成為后世忠臣的楷模,智慧的化身。成都有武侯祠,杜甫作千古名篇《蜀相》贊揚諸葛亮。陳壽《三國志》: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誡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其文學成就主要為散文,代表作有《前出師表》《后出師表》《誡子書》《隆中對》等。原集25卷已佚,明人輯為《諸葛亮丞相集》一卷,今人有整理本《諸葛亮集》。
賞析:耿耿忠心日月鑒,肌理縝密情在先
表,是中國古代臣子向帝王上書陳情言事的一種特殊文體。是封建社會臣下對皇帝有所陳述、請求、建議時用的一種文體。在古代,臣子寫給君王的呈文有各種不同的名稱。戰國時期統稱為“書”,如樂毅《報燕惠王書》、李斯《諫逐客書》,“書”是書信、意見書的總稱。到了漢代,這類文字被分為四個小類,即章、奏、表、議。表的主要作用就是表達臣子對君主的忠誠和希望。統觀眾多表文,盡管具體內容不同,但都離不開抒情手法的運用,因此,“動之以情”也可以說是這種文體的一個基本特征。此外,這種文體還有自己的特殊格式,如開頭要說“臣某言”,結尾常有“臣某常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之類的話。
《出師表》是出兵打仗前,主帥給君主上的奏章。這種表,或表明報國之心,或呈獻攻城掠地之策。歷來以戰名世者甚眾,以表傳后者頗少。唯獨諸葛亮的《出師表》不僅存之典冊,而且粲然于文苑。
諸葛亮上《出師表》是在蜀漢后主建興五年(227年),率兵北伐之時。這時蜀偏居一隅,國力疲敝,又“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諸葛亮為了實現劉備振興漢室、一統天下的遺愿,“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平定了南方,有了較鞏固的后方,并抓住了曹魏兵敗祁山、孫吳兵挫石亭的時機,揮師北伐,擬奪取魏的涼州(今甘肅部分地區),向后主劉禪上了兩道表文,“前表開守昏庸,后表審量形勢”,即出名的《前出師表》《后出師表》。我們選的是《前出師表》。
諸葛亮自劉備于建安十二年(207年)“三顧茅廬”后,即忠心耿耿地輔佐劉備,以完成統一大業。經過長期奮戰,使寄寓荊州的劉備,一躍而為與魏、吳對峙的蜀漢之主,雄踞一方,到章武元年(221年)劉備即帝位。章武二年(222年)吳蜀彝陵之戰后,劉備敗逃白帝城,次年病死。劉備“白帝托孤”時對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對諸葛亮無比信賴。諸葛亮回答說:“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劉備吩咐劉禪說:“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劉禪繼位,即后主。劉禪黯弱昏庸,親信宦者,遠避賢能,胸無大志,茍且偷安,是個“扶不起的阿斗”。諸葛亮主張出兵擊魏,侃侃陳詞,力排眾議,申明大義以拯其愚,吐露忠愛以藥其頑,既有政治家的眼光,又有軍事家的頭腦,且嚴守人臣下屬的身份。
《出師表》前半部分是臨行時的進諫,后半部分乃表明此行奪勝的決心。劉禪雖為蜀主,而蜀之安危成敗,實系于諸葛亮之身,因而率眾出征時,當促使后主保持清醒的頭腦,具備正確的觀點,采取得力的措施,才能保證前方順利進軍;同時表明自己忠貞死節之心,既是自勉自勵,也是預防小人惑主。
諸葛亮向后主提出三項建議:廣開言路,執法公平,親賢遠佞。這三項建議,既是安定后方的措施,也是施政的正理。為了治愚醫頑,作者在行文上頗費深思。由勢入理,起筆崢嶸。表文第一節向后主提出“開張圣聽”的建議,可是卻從形勢敘起,這能起振聾發聵的作用,又能激發繼承遺志的感情。表文開筆即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深痛劉備壯志未酬身先死,深誡后人繼承父業不可廢,以追念先帝功業的語句領起,至忠至愛之情統領了全文。繼而以“今天下三分”,點明天下大勢,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誰手;復直言“益州疲敝”,自身條件很差,地少將寡,民窮地荒;進而大聲疾呼:“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大有危在旦夕之勢,如不救亡存國,將會出現國破身亡的慘局,筆勢陡峭,崢嶸峻拔。在凸顯形勢的情況下,以“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他們不忘先帝恩德,不改對后主的忠心,轉危為安,化險為夷還是有依傍的,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在這樣的基礎上,提出“開張圣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的建議,規勸不可“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表文將是否廣開言路,從關系國家存亡的角度來談,從關系忠于先帝的高度來說,使人聞之驚心,思之動心。如果表文只是一般地申述廣開言路的意義,平平道來,那對一個昏聵愚鈍的君主來說,顯然是不會有多大觸動的。
由主而次,肌理縝密。以情動人,更要以理服人。說理應主次分明,先后有序。表文主要是向后主進言的,因而首揭“開張圣聽”,以打開進言之路。在打通了忠諫之路的前提下,再言執法公平、親賢遠佞兩項。談執法公平,又先總提“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繼而就宮中、府中兩方面分述之。分述時,又切緊“開張圣聽”的精神,宮中之事,向郭攸之、費、董允這些志慮忠純之士請教,而且要“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則“必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對于府中之事,向“性行淑均,曉暢軍事”的向寵請教,“營中之事,悉以咨之”,也“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最后提出“親賢臣,遠小人”的利弊。三項建議,既可獨立成項,又相互關聯。廣開言路,是開的忠諫之路,而非為讒邪開方便之門。親賢臣遠小人,才能廣納郭攸之、向寵等人的良言,才能“昭平民之理”,不讓奸邪得勢,造成內外異法,賞罰不明。君主昏庸,主要就在于貪于私欲,蔽于視聽,昧于事理,因而忠奸不分,賢愚不辨,是非不清,賞罰不當。諸葛亮針對后主寵信宦官黃皓,無視創業勛臣的做法,對癥施藥,既說得委婉深曲,又入情合理。所列三項,廣開言路是前提,執法公平是關鍵,親賢遠佞是核心。嚴密的說理,再愚的人也會得到啟發。
由近及遠,思路開闊。表文為了說明親賢遠佞的利弊,以先漢的“興隆”和“傾頹”的歷史事實,作為前車之鑒,并以先帝嘆息痛恨桓帝、靈帝昏庸誤國為告誡,促使后主親信賢臣,并以“漢室興隆,可計日而待”為鼓勵,由近及遠,借古鑒今,成敗并舉,顯得衢路交通,經緯成文。
諸葛亮因為后主是個“妄自菲薄,引喻失義”的昏庸之徒,理要說得明,語又不可用得重,既要循循善誘地開導,又要不失臣下尊上的分寸。因而以“形勢”使對方震動,明示已臨“危急存亡之秋”,如不勵精圖治,勢必國破身亡;以“情感”打動對方,連呼先帝,聲聲熱淚,其業系先帝首創之業,其臣為先帝簡拔之臣,其將為先帝稱能之將,怎不光先帝之遺德,竟先帝之遺業;以“措施”教之,告知治國理政的具體辦法,切實可行,行必有效;以“事業”勵之,告誡后主要完成“先帝創業未半”的業,使天下歸一,漢室興隆,促使他有遠大的抱負,完成千秋大業。表文從各個方面規箴后主,情真理足,詞婉心切,因而雖屬奏章表文,卻感人至深。
表文的第二部分,由敘自己生平而至言伐魏的意義,進而表明自己“興復漢室,還于舊都”的決心,也寫得慷慨深沉,動人心魄。
由人推己,文勢跌宕。表文從第一部分的進諫,到第二部分,忽以“臣本布衣”起筆,另入蹊徑,別開生面。敘寫自己二十一年來的情況,歷數先帝之殊遇,——一是三顧茅廬使之出山效命,一是傾覆之際使之出任丞相,使之由布衣身份一躍而為極位重臣,由躬耕隱士一舉而成三軍主帥。這一節敘述,好像是逸枝衍蔓,與上下文聯系不緊。其實,它與上下文貌分神合,明疏實密。這是因為:第一,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說明以上進言純屬忠諫,叫后主聽來覺得舒徐入耳。第二,以自身不負先帝殊遇舍命驅馳,作為后主不忘先人之業的榜樣,進一步啟發后主奮發圖強。第三,二十一年不平凡歷程,說明創業艱難,激勵其不可半途而廢,更不能前功盡棄。第四,寫出先帝的榜樣,不以孔明“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茅廬,事不分大小,悉以咨之,于敗軍之際,危難之間,仍委以重任,可見他任人唯賢,唯才是舉,叫后主效法先帝知人善任。第五,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盡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遺,使后主托之以討賊興復之任,既可避免因自己率師北伐,小人進讒而壞了大局。諸葛亮的這段敘述,系進一步打動后主的心,樂于接受前面的進言,又是臨別時的表白,實有深衷曲意。文章由進言轉而為自敘生平,宕開了筆墨,使文勢波瀾起伏,更為可觀。
由敘而誓,推上高潮。表文繼敘二十一年遭際之后,續述白帝托孤“夙夜憂嘆,平定南方”,進而表明北定中原的決心。前面的論世、進言、抒情,到此結束,《出師表》文的特點由此完全挑明。追言托孤之事,交代這次出師的歷史根源,“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托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說明這次出師的思想基礎。“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指出這次出師的物質準備。在充分敘說條件的基礎上,提出“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于舊都”,鏗鏗振響,熠熠生光。《出師表》至此才徑言出師,切入本題。前面的進言,是為了保證有出師的條件,中間敘事,是說明自身具有出師條件,至此兩線歸一,提出宜乎出師,也就如瓜熟蒂落,孕足而娩。
歸納前意,總綰全篇。表文結束之前,將出師與諫言兩層意思攏合一起。一方面提出“愿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另一方面還提出“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諸葛亮主動領受任務,并表示如失職,甘愿受罰,以顯示“平明之理”。最后還不放心,諄諄告誡,要后主“深追先帝遺詔”。先帝臨終時訓示后主:“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唯賢唯德,能服于人。”最后又回復到“開張圣聽”的問題上來,可見修明內政與北伐勝敗的關系。這也就將前面兩部分內容聯系在了一起。
表文以“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作結,其聲嗚咽似泣,其情沛然如注,勤勤懇懇之態如現,耿耿忠心盡袒。
“出師未捷身先死”,可惜諸葛亮此行未能如愿卻先逝世,后人對此頗多惋嘆。杜甫曾寫道:“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蜀相》)宋代文天祥身陷囹圄,還高唱“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正氣歌》)陸游更是多次提到《出師表》:“《出師》一表通古今,夜半挑燈更細看。”(《病起書懷》)“《出師》一表千載無”(《游諸葛武侯臺》),“一表何人繼出師”(《七十二歲吟》),“凜然《出師表》,一字不可刪。”(《感狀》),“《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書憤》)總之,這道《出師表》,因其深情厚誼寄翰墨,忠肝義膽照簡編,一直為人所樂道。
《出師表》能寫到如此地步,絕不是偶然的。文章皆有所為而發。時當北伐在即,作為主帥的諸葛亮要向君主上一道表文,他不是作為例行公事,而是從北伐的全局上考慮,只有后主修明政治,才能保證北征順利,因而先進安后之言,再表奪勝決心。表文又極為注意收表對象的特點,因而絕不是一般的表文,列述方策,而是熔議論、敘事、抒情于一爐,啟愚矯頑。諸葛亮是后主的丞相,又是受“托孤”的對象。他給后主上表文,既不宜用訓斥的口吻,又不便用卑下的聲氣,寫得不卑不亢,方為得體。尤其文中連稱先帝,最為合宜。全文稱先帝凡十三次,顯得情詞十分懇切。諸葛亮自敘“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確實“諸葛一生唯謹慎”,細玩本文,從慮事到措詞,無不體現了“謹慎”精神,這也是此表被之為“至文”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