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名言·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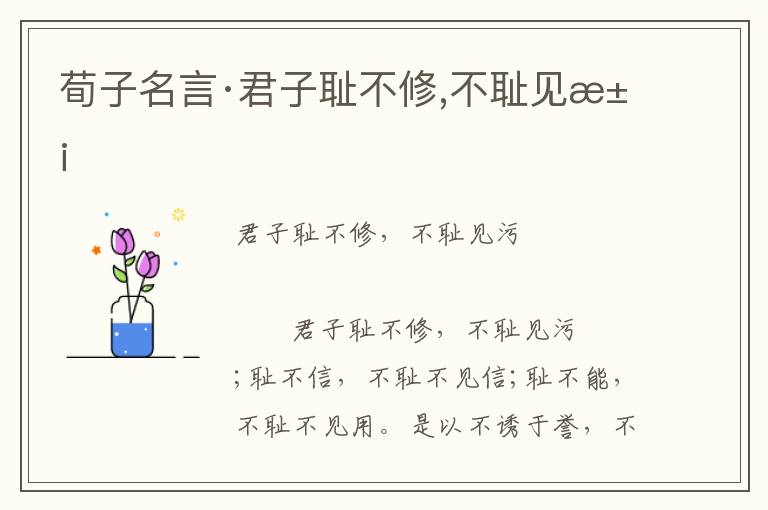
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污
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污;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于譽,不恐于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非十二子》)
【鑒賞】 這是荀子的“恥”論。
應該說,儒家是很看重“恥”的。“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禮記·中庸》)“恭近于禮,遠恥辱也。”(《論語·學而》)“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孟子·離婁下》)“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孟子·盡心上》)這樣談“恥”的言論在儒家經典中幾乎俯拾即是。
那么,究竟什么是恥?恥,應該是內心深處升起的一種羞辱感。“見污”、“不見信”、“不見用”,在荀子那個時代便是很常見的三種“恥”。那時一個人如果能將這三種“恥”銘記在心,應該說已經很難得了,“知恥近乎勇”。
可真正的君子所“恥”之處卻并不在此。與“見污”、“不見信”、“不見用”這些外在的際遇相對,君子所“恥”的“不修”、“不信”、“不能”更偏向于內在的心理體驗。以內在的心理體驗為本,視外在的人生際遇為末;恥不能秉持這個內在的“本”,而不恥能否因此而獲得外在的“末”,這便是孔門的“內省不疚”(《論語·顏淵》)。
但這并不是說,君子就應該如《漢書·董仲舒傳》所說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不管外在的功利。對真正的君子而言,任何外相變動,都不能干擾心中的大局(“不誘于譽,不恐于誹”)。正如圍棋國手,每下一子,都要全盤考慮整個棋局的大勢一樣,真正的君子亦已在自己平淡的生活中建立了一種生命的“內時空”。每當外相人心,他首先不是對這個外相做簡單的價值判斷,而是為它在自己生命的“內時空”中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譽也罷,毀也罷,都不會去聚焦,不管它有多么強大,終究會在心中最合適的位置落下。而我只是“率道而行,端然正己”,在這獨一無二的國土里做個“觀自在菩薩”。
達到這種境界當然是很不容易的。這里真正的難點,還不在于外在的“他譽”、“他毀”,而在于由這“他譽”、“他毀”而引起的“自譽”、“自毀”。“他譽”、“他毀”的力量再強大,畢竟只存在于與人交接的一時,但其引起的“自譽”、“自毀”以及與此相關的種種成見卻要縈繞在生活的時時刻刻。這才是真正的“物”,這才是真正的“心中賊”(王陽明語)。面對這萬分強大的“心中賊”,你能做到“不為物傾側”么?
做一名超道德的“誠君子”,實在比做那種恪守道德的道學先生更難。
怎么辦呢?孟子曰:“守約。”這個“恥”字畢竟是來自普遍認可的社會規范,為什么不試著轉化它,讓它成為“內時空”的一部分呢?在這個過程中,先“恥不修”、“恥不信”、“恥不能”,以期最終有資格“不恥見污”、“不恥不見信”、“不恥不見用”。說實在話,倘若沒有“恥不修”、“恥不信”、“恥不能”的心理經驗,卻偏要說著“不恥見污”、“不恥不見信”、“不恥不見用”的話頭,這就真的有點“無恥”了。“無恥之恥,無恥矣。”中國文化在宋以后的衰敗,正與這種好高騖遠的心態有關。
畫虎不成反類犬,儒門的向上一路,難學,但中國文化要發展,中國士人要成熟,恐怕也只有這一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