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雜篇·盜跖》原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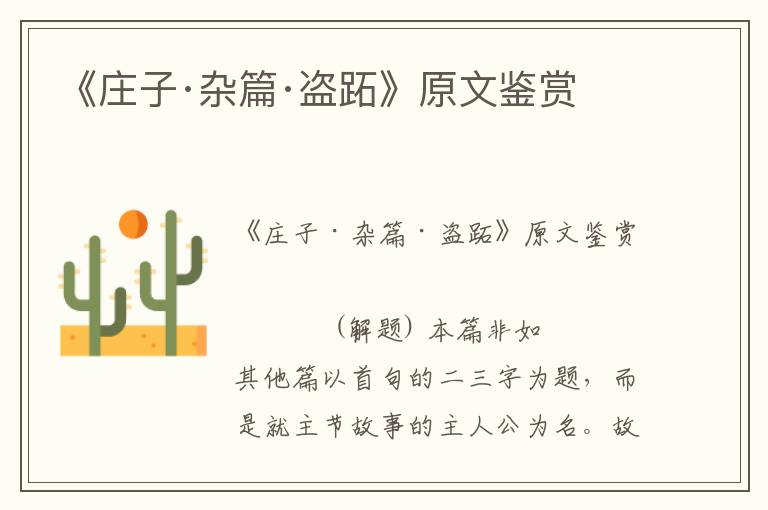
《莊子·雜篇·盜跖》原文鑒賞
(解題) 本篇非如其他篇以首句的二三字為題,而是就主節故事的主人公為名。故事是虛構的。
主旨在以無識無知,與鳥獸同居為至德之世,以求悅其志意,養其壽命。反對有為制作。對于名利,以為 “名利之實,不順于理,不監于道”。
原 文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一),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二),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人保(三),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 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四),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泉涌,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 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五),往見盜跖。
解 說
(一)“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魯大夫。長孔子八十余歲,非同時人物,不能為友,故此故事為虛構。本節篇幅較長,為了閱讀方便,分數段校譯。
(二)“穴室樞戶”: “樞”門軸,名詞,與“戶”連結,似難解通。先輩有的以為當為“摳”,苦溝反,探取之意。但“摳”字生僻,古籍少用。本篇行文平易,不會用此生僻字。且探取與“戶”連結,也難成義。實應讀如字。“樞戶”是與“穴室”并列的。“穴”洞也,就是名詞,用為名動詞,便成挖洞。同樣,“樞”是門軸,用為名動詞,便是轉動門軸。“戶”為門的一邊。也就是門。把門軸轉動,便是打開,因而“樞戶”便是破門而入。
(三) “小國入保”: “保” 通堡。
(四) “雖今先生之辯”: 句本通。但依漢語習慣,“雖今”,“今” 當在“雖”前,既在其后,當另有說,實為“令”之誤。
(五) “子貢為右”: “右” 《說文》 “助也”。“為右”作為助手,即是跟車的。
語 譯
孔子和柳下季交情很厚,柳下季有一個弟弟名叫盜跖。盜跖指揮之下有九千人,橫行于天下,侵擾諸侯國家。挖墻壁破門戶,搶奪人家的牛馬,掠取良家的婦女。一味貪求貨財,拋棄親戚,不顧父母兄弟,不祭祀祖先。所經行的地方,大國堅守城池,小國退進城堡里。廣大民眾深受其害。孔子對柳下季說: “做父親的,一定能夠管束他的兒子; 做兄長的,一定能夠教導他的弟弟。如果父親不能管束他的兒子,兄長不能教導他的弟弟,還要父子兄弟這樣的親屬關系干什么!就先生來說,乃是當代有作為的人,弟弟是盜跖,成為天下的禍害,卻不能教導,我確實替你感覺有點羞愧,請讓我來替你勸說一下。”柳下季說: “像先生所說做父親的一定能夠管束他的兒子,做兄長的一定能夠教導他的弟弟,假若兒子不聽父親的管束,弟弟不接受兄長的教導,即使先生說得天花亂墜,又能夠怎樣呢?而且跖這個人,心思像翻滾的泉水,意念像盤旋不定的旋風,勇力足以擋住對手,口才足以掩飾過錯。順合他的心意就高興,違逆他的心意就氣惱,隨隨便便就給人以難堪,先生千萬不要前去。”孔子不聽,顏回駕了車子,子貢作為助手,前去拜訪盜跖。
原 文
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 “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一)。”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發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 ‘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二),帶死牛之脅(三),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幸于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四),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 “丘得幸于季, 愿望履幕下(五)。”謁者復通。盜跖曰: “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 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 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 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六),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七)。此圣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愿也。”
解 說
(一)“敬再拜謁者”: 這是謙詞。“謁者”服事者。本來要見主人,不直言,而言“再拜謁者”,表示沒有資格晉見主人。
(二)“冠枝木之冠”: “枝木”或以繁飾為解,甚為牽強。孔子儒者,儒冠無多繁飾,故亦不類。先輩有疑為“枯木”之訛的,頗近是。與下句的“死牛”正好相對。形容其圓柱形之冠如一個死樹疙疸。“枝”與“枯”形近致誤。
(三) “帶死牛之脅”:“死牛之脅”或以為牛革之帶。但“死牛”并無皮革之意,“脅”肋骨也,亦非帶。而“帶”在句首,與上句第一“冠”字相對,用為動詞,佩也。非是名詞,不能作衣帶之帶解。故此解非是。從世傳孔子的畫像看,腰佩短劍,大概是有所本的。“死牛之脅” 當即喻這短劍。
(四) “子之罪大極重”:“極” 注家以為 “殛” 之假,誅也。是,應從。
(五)“愿望履幕下”: 這是謙詞。“履”鞋子。“幕”帷帳。本是要到其住處與本人相見,卻說能看到他的鞋子在他帷帳之中。表示本身的卑賤。
(六) “面目有光”: “面” 當是“兩” 的誤字。
(七) “共祭先祖”: “共” 讀供。
語 譯
盜跖正在泰山的南端休整隊伍,吃著切細了的人肝。孔子下車走向前,見到負責傳達的人,說:“魯國人孔丘,景仰將軍崇高的風范,特來拜見您的傳達人員。”傳達人員進去做了報告。盜跖聽后大怒,瞪圓雙眼有若明星,頭發豎起沖冠直上,叫道:“這不就是魯國那個裝腔作勢的孔丘嗎?替我轉告他: ‘你編八造謀,冒稱什么文王、武王,戴著死樹疙瘩式的圓筒帽子,佩帶死牛肋樣的短劍,有的沒有的亂說一氣。不種田而有飯吃,不織布而有衣穿,只憑耍弄兩片嘴和翻動舌頭,任意搬弄是非,來迷惑各國的國君,弄得天下從學的人丟開了根本,胡亂講求什么孝悌,用來僥幸騙取功名富貴。這樣一個家伙,罪極大惡至重,快些走開!不然的話,我就把你的肝拿來給我白天的飯里添上一點菜。’” 孔子請傳話人再傳達說:“我有幸和令兄季交上朋友,希望能在您的帳下見到您。”傳達人員又為上報。盜跖說: “讓他進來!”孔子緊走幾步進得帳來,離著座位退后幾步,向盜跖再拜施禮。盜跖怒氣沖沖,伸直兩腳,手撫劍柄,瞪大眼睛,像個哺乳期的母虎大聲吆喝說:“孔丘這邊來!你的話中我心意饒你不死,違反我心意就不用想活。” 孔子說: “我聽人說,天下的人品有三類: 長得體形高大,俊美無比,不分老幼貴賤,人人見了人人夸,這是上等的人品;智力維系了天地,才能能辨清各類事物,這是中等的人品;英勇強悍膽大敢為,集結隊伍率兵打仗,這是下等的人品。不論是誰,只要為其中的一類,就足夠南面稱王的。現在將軍三類兼備: 身高八尺二寸,兩眼光芒照人,嘴唇像丹砂那樣鮮紅,牙齒像排貝那樣整齊,聲音洪亮配比黃鐘,卻被稱為盜跖,我確實替將軍想也太不值得了。將軍如果聽我的話,我就南去吳、越,北去齊、魯,東去宋、衛,西去晉、楚,請他們給將軍建造幾百里的大城,規劃安居幾十萬戶的地方,尊奉將軍為諸侯,在天下另起爐灶。解散隊伍不再打仗,聚養兄弟族人,奉祀祖先。這是圣明和有才干的人的做法,是天下人所希望的。”
原 文
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夫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我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 湯、武立為天子,而后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 ‘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糜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以后,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后世。縫衣淺帶(一),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 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 ‘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于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圣人邪,則再逐于魯,削跡于衛,窮于齊,圍于陳、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二),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三),子之道豈足貴邪! 世之所高,莫如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四),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五),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六)。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于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于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七),皆離名輕死(八),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 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九),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于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十),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
解 說
(一)“縫衣淺帶”: “縫衣”大衣。“縫”通逢,“逢”大也。“淺帶”舊之服飾,大衣者往往系以寬帶,因有“寬衣博帶”的成語,于是有的注家便以博帶或寬帶釋之。但“淺”無寬、博之義。其本義應為褊,是小的意思。“淺帶”實是小帶子。大衣服小帶子,乃有戲弄之意。
(二) “子教子路菹此患”: “菹”乃“蒞”之訛,臨也。涉上“身菹于衛東門之上” 而致誤。二字形極近。
(三)“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就孔子“不容身于天下”及“教子路菹此患” 而言。
(四)“禹偏枯”:“偏枯”半身不遂。所言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等人,都在指說他們品德不高,惟獨禹卻指其身體的缺陷,似乎所擬不倫,因而推定必有訛誤。或以“枯”乃“酤”之訛,以為貪酒。但這是不合實際的,孔子有言“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孟子·離婁下》),禹不會貪酒。“枯”當是“沽”之訛,買賣也。“偏沽”意為一頭的買賣,指天下,就是說,他獨自占有了天下。
(五)“世之所高,莫如黃帝……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黃帝以下,列有堯、舜、禹、湯、文、武,共計七人,而謂為 “此六子者,數目不符。有謂“六”乃“七”之誤的,有謂不包括黃帝在內的,都無證可據。又有的注家指出,“文王拘羑里”不當在其中。這說法是對的,一則拘羑里不是品德問題,與他人不相類; 再則如確實應在其中,亦當在武王之上。此句當刪,這是后人加上的。
(六)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 注家以 “伯夷、叔齊” 之上,脫“莫若”二字,是。其上“世之所高,莫若黃帝”,其下“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都是如此結構。“伯夷、叔齊”上有“莫若”二字始通,應補。
(七)“無異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磔”,《說文》:“辜也。”段注以為當訓枯。“磔犬”意為干癟的死狗,以指餓死的那些人。“流”灌也。“流豕”灌滿水的豬,即俗所謂河漂子以指投水淹死的那些人。“操瓢而乞”拿著瓢討飯,以指介子推。
(八)“皆離名輕死”: “離” 羅也。“離名” 搜求好名聲。
(九)“除病瘦死喪憂患”:“瘦”先輩以為“瘐”之訛,病也。是。
(十)“子之道狂狂汲汲”: “汲汲” 急切營求。
語 譯
盜跖大聲喝道:“孔丘這邊來!那種可以用利益來籠絡而拿話來勸說的,不過都是些沒有識見的平常人罷了。至于身形長大,俊美無比,人人見了人人夸,都是父母遺傳給我的品質。你就是不來贊揚我,難道我自己不知道嗎? 而且我聽人說,好當面奉承人的,也好在背后說人的壞話。現在你對我說什么大城眾民,就是有意拿利益來籠絡我,把我當成一個平常人來看待,怎么能長的了啊! 要講城大,沒有比天下再大的。堯、舜擁有了天下,子孫連立個錐子尖的地方都沒有; 湯、武做了天子,他們的后代也不能保持住,不就是因為那個利益大的緣故嗎? 而且我聽人說,早年時候,禽獸多,人類少,因此為躲避禽獸,人們都筑巢而居。白天揀拾橡栗等野果,晚間睡在樹上,所以就叫做 ‘有巢氏的人’。早年人們不懂得穿衣服,夏天盡可能多積些柴草,冬天用來烤火,所以就叫做 ‘懂得怎么活著的人’。神農時代,躺下去舒服熨帖,起身活動自由自在。人們認識他們的母親,不認識他們的父親。和野鹿生活在一起,種地吃飯,織布穿衣,彼此都沒有擾亂的念頭。這是大德最盛的時候。可是黃帝不能伸張德行,和蚩尤在涿鹿地界戰斗起來,血流百里。堯、舜興起,建立了朝廷,湯趕走他的君王,武王把紂殺掉。從此以后,強的欺凌弱的,多的制服少的。湯、武以下,都是些亂人之輩啊。現在你修治文、武的做法,把持天下的輿論,來教導后來的人。穿著大袍子,系著小帶子,裝腔作勢,迷亂各國的國君,想著借此來撈取富貴。盜是沒有大過你的,天下人為什么不把你叫做盜丘,卻來管我叫盜跖呢? 你甜言蜜語地說服了子路。使子路摘去武士的高帽,解去長劍,接受你的教育。天下的人都說:‘孔丘能夠制止粗暴禁止為非作歹。’其結果是,子路謀殺衛君失敗,本身在衛國東門之上被剁成肉醬,這是你教導的不到家。你自以為是個有才干的人,是個圣明人嗎?卻兩次被趕出魯國,在衛國難以立足,窮困在齊,被圍在陳、蔡,在天下不能存身。你教子路遭受這樣的禍害,上不能保全自己,下不能存活別人,你的做法有什么可值錢的呢? 世間所推崇的,誰也比不過黃帝,可黃帝不能保持德行,在涿鹿地界戰斗,血流百里。堯不慈愛,舜不孝順,禹私有天下,湯趕走他的君王,武王把紂殺掉。這六個人,是世人所推崇的,認真評論一下,都是為了利益迷亂了本真,盡力地違反他們的情性,他們的行為是極其可恥的呢。世人所稱道的賢士,誰也比不上伯夷、叔齊,可伯夷、叔齊不肯做孤竹的國君,而餓死在首陽山上,連尸骨都沒有人葬埋。鮑焦自命清高,不與世俗同流,抱樹而死。申徒狄進諫未被接受,抱了大石自己投入河中,喂了魚鱉。介子推最忠心了,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給晉文公充饑,文公〔得國〕后把他忘掉,子推一氣之下離去,抱著大樹被火燒死。尾生和一女子約定在橋下相會,女子沒有如時到來,大水涌來他也不肯離去,抱住橋柱被水淹死。這六個人,就像干癟的死狗,灌滿水的豬,拿著瓢討飯的一樣,都是為了掙點名聲而不把死當回事,是不考慮根本頤養天年的人啊。世人所稱為忠臣的,誰也比不上王子比干、伍子胥,可子胥被投擲江中,比干被剖腹。這兩個人,是世人所稱道的忠臣,但結果卻為天下所恥笑。從上面所舉的這些來看,以至子胥、比干,都沒什么可尊貴的。你所用來說服我的,如果對我說鬼事,我是不大清楚的; 如果對我說人事,也不過就是這些了,都是我聽說過的。現在我來跟你講講人的真實情況:眼睛用來觀看事物,耳朵用來察聽聲音,嘴巴用來品嘗滋味,心意要求充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去疾病、死傷、憂患,在這時間里張開嘴大笑的,一月之中也不過四五天的光景。天和地是無窮盡的,人的死是有一定時間的。拿著有一定時限的家伙,寄托在無窮盡之間,那個快勁就和快馬躥過空隙差不多。凡是不能夠使其心意愉悅、頤養天年的,都不是明白事理的人。你所說的那些,都是我所拋棄的東西。快些走開,不要再說了! 你那瘋子似的急于營求的做法,是一些欺詐奸滑虛情假意的玩意兒,不能夠表達本真,哪里值得講啊!”
原 文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如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一),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 “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二)。疾走料虎頭(三),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解 說
(一) “今者闕然”: “闕”空隙也。引申為閑暇。
(二)“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 “灸”用艾燎烤的醫療方法。“無病而自灸” 即俗所謂沒病找病。
(三)“疾走料虎頭”: “疾走”緊追著。“料”撩撥也。
語 譯
孔子拱手施禮緊走兩步退了出來,走出門來登上車子。手握的韁繩幾次掉了下來。他愣愣地直瞪著眼睛,臉色死灰一樣地蒼白。低著頭伏在車前的橫檔上,喘不過氣來。回到了魯國的東門之外,正好遇到了柳下季。柳下季說: “今天閑在啊,幾天沒見,車馬有出門的樣子,莫不是去訪問跖了吧?”孔子抬起頭嘆了口氣說: “是的。”柳下季說: “跖是不是頂撞你還像以前那樣呢?”孔子說:“是的。我這是沒病找病啊。緊追著撥弄老虎的頭,捋老虎的胡須,差一點就給老虎吃了呢。”
原 文
子張問于滿茍得曰:“盍不為行(一)?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于心(二),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三)!”滿茍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于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日: ‘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茍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人嫂,而管仲為臣; 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四)。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 “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 滿茍得曰: “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子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于理,不監于道。吾日與子訟于無約。”
曰(五): “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于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六);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七),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八),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 鮑子立干,申子不自理(九),廉之害也; 孔子不見母(十),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解 說
(一)“盍不為行”: “盍”何也。或以“何不”為釋,則與下之“不”字犯重,故非是。“行” 品也。
(二) “反之于心”: “反” 義有二說: 一為悖反,一為返回。成疏: “反,乖逆也。”是第 一說,這是對的。“之”承上”若棄名利”代表名利。“棄名利”,內心必予排除。返回之說不恰。
(三) “不可一日不為乎”: 句有誤。“不可”之”不”衍,涉下致誤。
(四)“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田成子常”即田恒。“孔子受幣” 史無記載。在此事發生時,孔子曾請魯君討田恒。
(五)“吾日與子訟于無約,曰”:“日”或以昔日為釋。“曰”則是滿茍得陳述無約的話。但這樣的解釋有不合情理處。滿茍得與子張爭辯,是在難定孰是孰非的情況下才想找無約評理的。如果早已有無約評過理,怎么還會再來爭辯呢?顯然不會是這樣。“日”是“且”的誤字,因“且”下部漫漶所致。“曰”后是無約的話。其上脫“無約” 二字,涉上致誤。
(六) “反殉而天”: “而”通“爾”,取“此” 義。下同此句法的,同。
(七) “面觀四方”: “面” 為“而”之訛,應與“觀”互易其位。
(八) “無轉而行”: “轉” 先輩以為應讀 “專”,是。
(九) “申子不自理”: 各本所記不同。“申”有的本子作“勝”。“不自理”有的作“自理”。作“不自理”的 “申子”指晉獻公之子公子申生; 作“自理”的為申徒狄。還有把“自理”寫作“自埋”的。何者為是,不予考證。只就所據本照譯。
(十)“孔子不見母……義之失也”:所指為孔子父母的結合,沒有依據當時婚姻的程序。孔子以為不義而不見母。“義之失也”或以孔子此舉有失于義,非是。應是這是講求義的過錯。
語 譯
子張向滿茍得問道:“你怎么就不能規矩一點呢?不大規矩就要被人瞧不起,被人瞧不起就不會委以重任,不委以重任就難以獲利。所以注意著名,計算著利,在道理上真是正確的。如果拋開名利,不把它放在心上,那么,士人們做事,就可以一天都不去管它嗎?” 滿茍得說: “無恥的人富起來了,被人重視的人名聲顯赫了。名利最大的,就在無恥而被人重視。所以注意著名,計算著利,被人重視是真的正確的。如果拋開名利,不把它放在心上,那么,士人們做事,難道就都是抱著天嗎?” 子張說: “當初桀、紂身居天子的地位,擁有整個天下,如果對奴隸聚來說: ‘你的行動活像桀、紂。’ 他就會臉色改變,心感不快,因下層人都鄙棄他們。仲尼、墨翟,只是個沒地位的百姓,要是對宰相說: ‘你的行動活像仲尼、墨翟。’ 他就會面容整肅,連稱不敢當,因這些士人確實是高貴的。所以天子的權位未必尊貴,沒官位的百姓未必卑賤。貴賤的區別,就在于行為的好壞。” 滿茍得說: “小偷小摸的要被關押,竊國的大盜就做諸侯,在諸侯的門里,就有懂理的士人存在。當年齊桓公小白殺掉兄長收納了嫂子,可管仲做了他的臣;田成子恒殺掉齊君竊取了齊國,可孔子接受了他的聘禮。雖口頭上瞧不起這些人的,可實際上卻甘居其下。這樣,言行的實際就在心里發生了碰撞,不也太不體面了嗎! 所以古書里有這樣的話: ‘究竟誰好誰壞,成功的就擺在前面,失敗的就甩到后邊。’”子張說: “你不照規矩辦事,就要親疏不分,貴賤失宜,長幼無序。五紀六位的綱常,還怎么能保持其區別呢?” 滿茍得說:“堯殺掉長子,舜流放母弟,親疏分清了嗎?湯趕走夏桀,武王殺掉殷紂,貴賤得宜了嗎? 太子的小兒子王季做了嫡子,周公旦殺掉兄長,長幼有序了嗎? 儒者假稱仁義,墨子講求兼愛,五紀六位的綱常能夠區分清楚嗎?再說,你正是為著名,我正是為著利。名利的內涵,既不是遵循了情理,也沒有參照著大道。我就來和你同去無約那里申辯一下。”
無約說:“下層人為貨財去拼死,上層人為聲名來賣命,他們所用以變其真情、易其本性的東西是不同的,但在丟棄他們所有的樣子而去追求他們所不應有的樣子這一點上卻是相同的。所以說,不要學下層人那樣,還是翻轉來追求天吧; 不要學上層人那樣,還是按照天的道理辦事吧。不管是曲還是直,注視著天的最遠方,察看著四方,隨著時光來流變; 不管是對還是錯,緊握中心樞紐,獨自形成信念,和大道一路同行。不要一意孤行,不要有固定的成見,那會把應該做的事情弄壞;不要為財富而奔競,不要為成就而拼死,那樣就會把天丟掉。比干被剖腹摘心,子胥被挖掉眼睛,是忠招來的禍災; 直躬證父竊羊,尾生水至不去而溺死,是信的禍患; 鮑子抱樹而死,申子不自明理而亡,是廉的禍害; 孔子母死不奔喪,匡子終生不見父,有失于義。這都是上代所流傳、下代所認為的士人。話不虛言,行為果斷,因而就甘受其殃,身遭其難了。”
原 文
無足問于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一)。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二)?”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四)。與俗化世(五),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 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于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于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于患也。”無足曰:“夫富之于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埶,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六),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于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七)。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八),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余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九);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于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十),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十一),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厄而不死者也。” 知和曰:“平為福,有余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嗛于芻豢醪醴之味(十二),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于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十三),可謂苦矣; 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十四),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 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 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十五),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十六),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體而爭此(十七),不眾惑乎!”
解 說
(一) “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 “卒”徒也。
(二) “故推正不忘邪”: 字有誤。“故”有意。“推”辭也。“正” 為“而”形近而誤。“忘”或本作“妄”,是。句意是,故意推辭而不妄取呢?
(三)“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在一個長句里,運用兩個“以為”,語氣不順,于義亦無補,因推定其有誤。前一“以為”衍“為”,后一“以為”衍“以”。句為“以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
(四)“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句難解,字有誤且淆亂。句當為“是所以專主而無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所以”上提置于“是”下,“無”后移置“覽”上,“正”為“而”形近而誤。“專主”意為主觀臆斷。
(五)“與俗化世”: 字有誤倒。“世”當在“俗”字前,“世俗”為一詞,涉上“絕俗過世” 而誤。
(六)“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俠”通挾。句與下之“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相并列,為句法的一律,當衍“而”,義已足。
(七)“體不待象而安之”: “象”,“像”之本字,模仿。
(八)“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百姓”無足與知和之辯,在個人的品性,與百姓無關。“姓”實為“性”之誤。后之錄者更加以“百”。“百”衍。句為“知者之為,故動以性”,以與“不違其度”相接。
(九)“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勢”與“貴”互易,于義為長。一般都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并論,本文也應是這樣,下文便是“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勢” 與 “財”也正好相對。
(十)“堯、舜為帝而雍”:“雍”和也。雖亦能通,但與帝位問題的關系不大,當是“讓” 的誤字,其形甚近。
(十一)“則可以有之”:接在“而天下稱賢焉”句下,意便是天下稱賢的這種事是可能有的。但在什么情況下是這樣的?則不明確,因而其間缺少了表明其情意的一個環節。句有誤倒。其文為“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此皆就其利,辭其害”應與“而天下稱賢焉”互易其位,句成“天下稱賢焉。此皆就其利,辭其害,則可以有之”。
(十二) “口嗛于芻豢醪醴之味”: “嗛” 音愜 (qie),快意也。句與上“耳營鐘鼓管籥之聲”相對稱,當衍“于”字。
(十三) “侅溺于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 “侅”音該 (gai),飲食過量而氣逆。“馮氣”盛氣。“行”名詞,旅裝也。“若負重行而上也” 成疏以為“猶如負重上阪而行”,故注家多謂 “也”乃 “阪”之誤。但何以“阪”誤為“也”,并無說處。實際不改也通,故不改。
(十四) “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 “耳”或以聽官之耳為釋。“堵”通“杜”,非是。“耳”語詞,“堵”垣也。“滿若堵耳”積累多到像墻一樣高了。成疏即以 “堵,墻也” 為釋
(十五)“內周樓疏”: “樓” 重屋。“疏”窗也。
(十六)“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單”通“殫”,與上之“盡”、“竭”同義。“盡性”、“竭財”各為一事,“殫”與之并列,亦當為一事,下脫一字。“性”為本性。“財”為富。與富并列的為貴,顯示貴的為勢,因可推定,“殫”下所脫的為 “勢” 字。
(十七)“繚意體而爭此”:“繚”擾亂也。“繚意體”或本作“繚意絕體”,“絕體” 正好與 “繚意”相對稱,可從。“體”上補“絕”字。
語 譯
無足向知和問道:“人們沒有不去抬高名奔競利的。你富了人們就歸附于你,歸附就處在下位,處在下位就把你抬高了。他人來處下位而自己被抬高,正好是延長生命安適體魄舒暢心情的方法。可你竟然不注意這些,是沒有認識到呢? 還是認識到而力不從心呢? 還是有意不做而不肯亂來呢?” 知和說: “現在有這么個人,認為和自己同時存活,同一個地區居住的人,乃是超凡越代的人,這是主觀臆斷而沒看到古今的不同、是非的分野。與世俗合流,扔掉那最重要的,拋棄那最尊貴的,來做那所想做的。就這樣講求延長生命安適體魄舒暢心情,不也太遠了嗎? 痛苦的疾病,愉悅的健康,身體對它都無所警惕; 驚心動魄的恐懼,興高采烈的歡欣,內心都不為所動,只知道在做事但不知為什么要做。照這樣,尊貴到做了天子,富有得蓋過天下,也是免不了憂患的。”無足說: “富有對于人,沒有不好的地方,包容了所有的好事,占居很高的地位,至人不能比,賢人也趕不上。依仗別人的勇力顯示威風,憑借別人的智謀顯示眼光,靠著別人的品德充做賢良,沒有擁有國土卻像國君那么威嚴。至于聲色、滋味、權勢對于人,用不著學習內心早就喜歡上了,用不到模擬身體就已適應了。再如喜愛、厭惡、遠避、接近,本來就不必有人來教,這是人的本性。縱然天下都說我不對,可有哪個人能不這樣呢?” 知和說: “聰明人做事,都是根據本性來行動,不越出它的范圍。所以感到滿足就不去爭取,沒有企圖就不去追求。不滿足就去追求,到處爭取也不覺得是貪;有了剩余就舍掉它,放棄了天下也不覺得是廉。廉貪的實際,不是就外部來衡量,反轉來是遵照自己的尺度。尊貴到天子的份上,并不以權位傲視別人; 富有到蓋過天下,也不以財力而瞧不起別人。衡量一下它的毛病,考慮一下它的另一面,認為有害于本性,所以推辭不予接受,并不是想博取名譽啊。堯、舜為帝位進行禪讓,并不是仁愛天下,而是不因為美好來損害生命;善卷、許由得到帝位不予接受,并不是假意辭讓,而是不因為外界事物擾亂了自己。天下人都說他們是好樣的。這都是為了靠近有利的,避開有害的,倒是可能這么做的,而不是借此來抬高身價啊。” 無足說: “一定要取得名位。苦害身體,有福不享,緊縮給養來維持生命,也就成多年患病、長期在困苦之中還沒有死的人了。”知和說:“適度是幸福,多余是禍害。什么東西都是這樣,資財是最厲害的。說起富人,耳聽鐘鼓管蘥的樂聲。口嘗鮮肥香酒的美味,用以滿足他的欲念,而不考慮他該做的事,可以叫做亂了; 過盛的心氣憋得要死,像背著重大的包袱爬高一樣,可以叫做苦了; 貪求貨財要達到滿足,貪求權勢要達到最高,閑下來的時候就像被淹沒一樣,身體胖得都喘不過氣來,可以叫做病了。為了想發財而追逐貨利。所以財貨堆得像墻高了還不想歇一歇,還緊抓著不放,可以叫做可恥了; 財貨積累起來并不使用,心里在盤算就是不往外拿,心煩氣躁,還不停地想著再多再多,可以叫做操心了; 家里懷疑有侵奪的賊害,在外又怕有盜寇的禍患,家里四周建樓設窗,外出不敢只身單行,可以叫做懼怕了。這六種情況,是天下最大的災害,卻都甩開它而不予注意。及至禍到臨頭,再求盡其本性丟光財貨、權勢來換取一天的無事,已經辦不到了。所以注意于名卻顯不了名,計算著利卻不能得利,可費盡心機使足全身力氣去追求這些東西,不也太糊涂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