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發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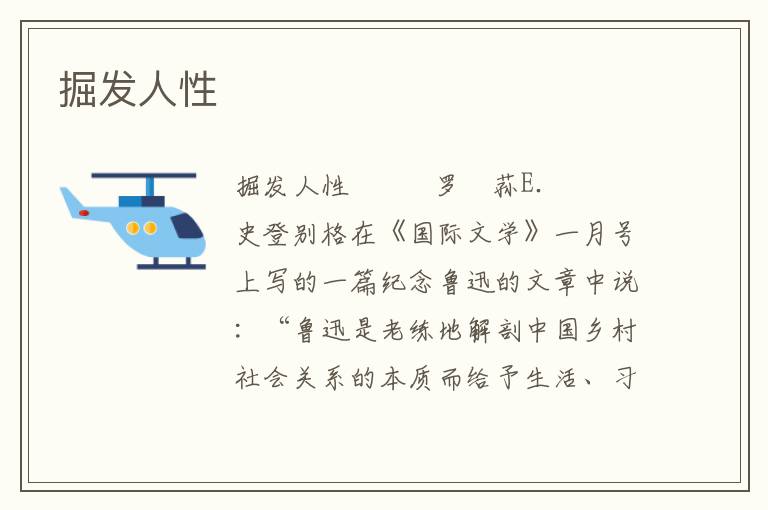
掘發人性
羅 蓀
E.史登別格在《國際文學》一月號上寫的一篇紀念魯迅的文章中說:“魯迅是老練地解剖中國鄉村社會關系的本質而給予生活、習慣、道德的真實描寫。阿Q之成為中國文學里最普遍的形象并不是偶然的。”這是不錯的,正因為魯迅發掘了真正中國人民的人性,剖解了這個老中國的國民性,展示給我們看了——這末一幅阿Q相,這末一個阿Q精神。自然,有些人惱怒了,有些人笑笑就算了。而更聰敏的卻是一種變戲法的手段,那就是有一個時期所宣傳的阿Q精神的被槍決。實際上,這個“人性”仍然活在我們的土地上。被槍決是另外一種。我說的這另外一種,也確乎渺小,但也頗有傷于體面的。我很清楚的記得民國二十四年的北平,氣焰已然很高的敵人曾經強迫我們把掛在鼓樓上的一塊匾摘了下來,這塊匾上寫著“明恥樓”①三個字。嗯,誰都知道那時候的華北是怎樣的情形吧,“明恥”怎末能成呢。但是連這種欺騙的慰藉方法也不準存在的時候,我們不是又看見了水龍和大刀么·雖不免有傷于體面,而那威嚴卻仍然在的。然而,阿Q精神卻實實在在還活著。魯迅的許多雜文,是幫助我們發掘中國人性的寶庫。在《忽然想到之四》中,他說:“其實這些人是一類,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的精神是不會完的,——因為都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倘有不信,請看清朝的漢人所做的頌揚武功的文章去,開口‘大兵’,閉口‘我軍’,你能料到被這‘大兵’、‘我軍’所屠殺的就是漢人自己么·你將以為漢人帶了兵將別一種什么野蠻腐敗民族殲滅了。”又說:“然而這一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久存在。在中國,惟他們最適于生存,而他們生存著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掉反覆著它的命運。”這一流“永遠勝利”著的人,不是到今天還活神活現的在我們眼前擺著“威風”么·他們不但有一套“安天知命”的哲學,他們更有一套“適于生存”的方法,那就是投機。這就是“中國雖完,他們仍然不完的”,因為他們還有新的“主子”,新的“我軍”。而且,他們更多有一套“反來覆去”的戲法,只要“適于生存”,今天去了,明天又回來;今天稱“逆”,明天仍然可以稱為“氏”的。這不是只有他們才是“永遠勝利”著嗎·這是一。還有,魯迅在一篇通訊中解釋了所謂“聽天任命”,所謂“中庸”,并不僅僅是人的惰性,“其實是卑怯”。他說:“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②的時候,多是兇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于圣道。”這正是“卑怯”的一種最好的解釋,“命運”和“中庸”恰恰是欺人騙自己的一種“慰藉”,也就是“精神勝利”的一種。我們不是常常看見一些人物,縱做奴隸,也還有一篇洋洋灑灑的宣言。倒并非是不甘寂寞,而是表示自己的“勝利”的存在。縱為“奴隸”,也還有個“總管”的地位。這一幅“奴才相”,不僅是“注定的命運”,而是早已是“老家法”了。這是二。還有,那就是“暴君”和“奴才”可以同時薈萃于一身,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奴隸總管正是。魯迅在《忽然想到之七》中說:“他們是羊,同時也是兇獸;但遇見比他更兇的兇獸時便現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兇獸樣。”這是卑怯的人性,這是“奴才暴君”的本相。不是阿Q當趙老太爺怕起革命的時候,也曾幻想著對于仇敵們的報復么·但是那種“兇獸樣的羊”一經幻滅,立刻就是更加懦弱而可憐的羊了。這是三。凡這些,都是蒙住人性的假面,雖是卑怯,卻要裝出勇敢相來,雖是奴隸,卻要扮做總管模樣,真話,實相便漸漸少下去,剩下來的是好聽的假話,好看的假面。魯迅揭了它,還它以原相。為什么魯迅要一再的說,中國的得救,“只好先行暴君各樣的劣點,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要“對手如兇獸時就如兇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這就是要有中國的真正的人性,要發掘那卑怯的,丑陋的,自私的人性;暴露那擺在表面的好看的假面。而要有能敢說、敢笑、敢怒、敢罵、敢打的勇于正視生活的人性。只有這樣,才能把阿Q精神從我們中間掃除掉;只有這樣,才能撕毀被“老法子”沿下來的一幅面團團相;只有這樣,才能換上新的胚胎;只有這樣,才能有中國的真正健康的人性。作于1940年10月15日選自1943年版《小雨點》
〔注釋〕 ①明恥樓:即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營建的北京鐘鼓樓。據談遷《北游錄》記載,清順治十一年(1654年)二樓毀于火災,乾隆時重建,嘉慶五年(1800年)重修。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京師時,鐘鼓樓上文物遭到了破壞,建筑幸免于毀。1923年將鼓樓改為明恥樓,第二年復改為齊政樓。1957年鐘鼓樓被列為北京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鐘鼓樓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②護符:一種佩飾,被認為對佩戴他的主人有神奇的保護力量。〔鑒賞〕 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揭開了人性中軟弱、狡詐和勢利眼的一面,阿Q這個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類本性的一個側面。在阿Q身上,暴露出中國病態的國民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統治下中國人卑瑣情狀的縮影。如果說,魯迅這篇小說是暗示性的,那么他的雜文對中國人身上的阿Q精神就直截了當,毫不客氣,大加筆伐了。1928年有人撰文,說阿Q時代已經死去,它沒有代表現代的可能,把阿Q的形骸與精神一同埋葬了罷!羅蓀的《掘發人性》寫于1940年,他明確指出:“實際上,這個‘人性’仍然活在我們的土地上。”當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肆無忌憚地蹂躪中國大地的時候,中國人甚至連做阿Q的顏面都沒有。1935年的北平,氣焰囂張的敵人強迫中國人把掛在鼓樓上標有“明恥樓”的匾摘下,中國人知恥的精神慰藉方式也被剝奪了。這就是“阿Q精神的被槍決”。中國人只允許在“水龍和大刀”之下,老老實實做侵略者的順民。這是何等悲哀!更為可怕的是,“阿Q精神卻實實在在還活著”。這是作者對國人的當頭棒喝,是對國人靈魂的警醒。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羅蓀是一位積極投身抗戰的愛國作家和文化戰線上的斗士。在他看來,魯迅的許多雜文,就是“幫助我們發掘中國人性的寶庫”,沒有過時。他從魯迅所開列的一些社會現象,加之他自己對現實的觀察和思索,對國人的人性中仍然存在的阿Q精神給予痛心疾首的揭露、嘲諷和批判,揭示了改造阿Q精神的艱巨性和長期性,并呼喚“中國的真正健康的人性”,因而顯得意味凝重、深長。文中舉出當時社會中仍然存在的阿Q精神的三種表現。其一,善于見風使舵,在任何處境中都能夠像“變色龍”,伶俐活潑,趨時附勢,自鳴“永遠勝利”。城頭變幻大王旗,對他們來說根本無所謂,他們早已謀算,只等拿出表演技能,不論是非,可以應變,玩“反來覆去”的戲法,去適應新的主子,去干傷天害理的壞事。那些人揮舞對著自己國人的屠刀,“活神活現的在我們眼前擺著‘威風’”。“他們不但有一套‘安天知命’的哲學,他們更有一套‘適于生存’的方法,那就是投機。”其二,以“聽天任命”,滿口“中庸”、“命運”為自己的卑怯行為辯解。既騙人,又騙己,也是“精神勝利”之一種。這種人縱然做了奴隸,“也還有一篇洋洋灑灑的宣言。倒并非是不甘寂寞,而是表示自己的‘勝利’的存在”。其三,暗喜于縱然是奴隸,還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奴隸總管,露出洋洋得意的“奴才暴君”的本相。畢竟手中有權,管著眾多奴隸,是可榮耀的。在他們眼里,這樣的位置還是有社會地位的,有體面的,故欣欣然也。這也是魯迅曾刻畫過的人,見著比他更兇的便現出羊貌,見著比他更弱的便現出兇獸貌。故羅蓀說:“但是那種‘兇獸樣的羊’一經幻滅,立刻就是更加懦弱而可憐的羊了。”這些是典型的阿Q精神的再現。魯迅之所以一再說,要“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就是提倡要有光明磊落的真正的人性。羅蓀忠實地繼承了魯迅的主張:“要發掘那卑怯的,丑陋的,自私的人性;暴露那擺在表面的好看的假面。而要有能敢說、敢笑、敢怒、敢罵、敢打的勇于正視生活的人性。”今天人們早已告別了那個黑暗的時代,但腐朽的東西依然存在,封建主義的幽靈沒有完全消失,而且會穿上新衣,打扮得很美麗。作為個人,對社會進步應當擔負起社會責任。盡管一己之力微不足道,也要正視社會現實,思考如何挺起脊梁骨,堂堂正正地做人,敢于向生活中負面的東西、荒謬的現象宣戰,以誠實的努力,伸張正義,表現自己的喜怒哀樂。唯利是圖,蠅營狗茍,一切向錢看,或卑瑣委頓,見風使舵,或安于現狀,不思進取,是戕害、腐蝕人心的一副毒藥。時代的進步,促使人們思考如何正視社會和自身的不足,從自身做起,自省自勵,發掘人性中健康向上的東西。讓新的健壯的胚胎生長起來,增強自我提升的能力。這對于社會的揚善懲惡,有著積極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