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外篇·駢拇》原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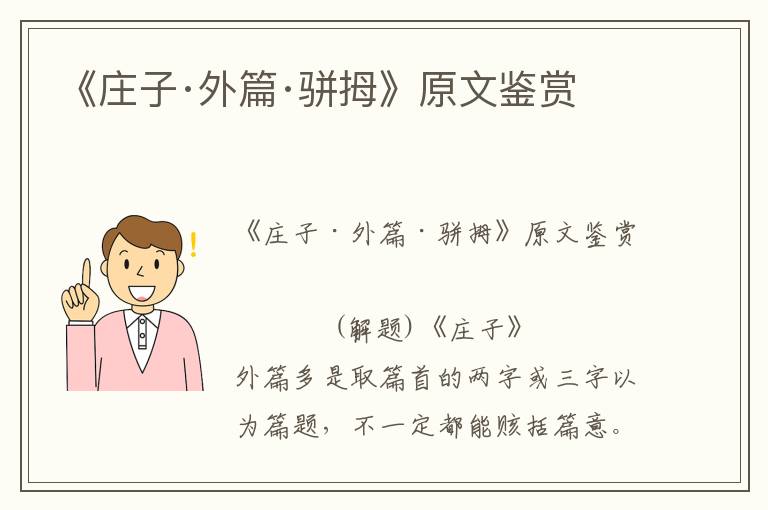
《莊子·外篇·駢拇》原文鑒賞
(解題)《莊子》外篇多是取篇首的兩字或三字以為篇題,不一定都能賅括篇意。這是春秋、戰國時代作品的一般做法。本篇即是取篇首的兩字為題的。
主旨在以駢拇、枝指以喻仁義之于情性,主張任其“性命之情”。
原 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一);附贅縣疣出乎形哉(二),而侈于性;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三),列于五藏哉(四); 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于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于五藏之情者(五),淫僻于仁義之行,而多方于聰明之用也。是故駢于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于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于辯者(六),累瓦結繩竄句,游心于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七)?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八),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九);長者不為有余,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十)。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且夫駢于拇者,決之則泣;枝于手者,龁之則啼。二者或有余于數,或不足于數,其于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解 說
(一)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 “拇”足之拇趾; “駢”并也。“駢拇”拇趾與二指相連。“指”手指; “枝”指外多生之指。“枝指”俗謂六枝。“性”應以“生”為解。《莊子》書中“性”與“生”常混用。“侈”多出也。“德” 由本始派生之性。
(二)“附贅縣疣出乎形哉”:“附贅縣疣”見于《大宗師》,未做解說,譯為“疙疸瘤子”。“形”外形,以與“性”本生相對。
(三)“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方”因后有“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推知 “方” 即為 “旁” (曹礎基《莊子淺注》 有此說)。與 “多”應是二詞,“多”是多余,“旁”是外加,以與駢、枝相稱合。
(四)“列于五藏哉”:“五藏”即“五臟”,概言之,為內部,本意在指心。
(五)“多方駢枝于五藏之情者”:注家多以“多方”衍。以后有“多方于聰明之用也”句,兩個多方犯重,是。但還有應該考慮的,“駢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義之行,而多方于聰明之用也”這一長句,語境不適。應是:“淫僻于仁義之行者,駢枝于五藏之情,而多方于聰明之用也。” 句有誤倒。
(六)“駢于辯者”:文中所引以為病的是駢、枝、多、方四事,后總之為“多駢旁枝”之道。而這段文字所提為“駢于明者”,“多于聰者”,“枝于仁者”,“駢于辯者”,并出兩個“駢”,而缺“旁”,當有其一為“旁”方合。
(七)“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跬”為“掛”之假,畫也。“跬譽”為一詞,意為空頭提說。
(八)“彼正正者”: 注家多以第一個 “正” 為 “至” 之誤,是,當從。
(九)“而枝者不為跂”:“跂”注家多以為“歧”之誤,是。因形近致誤。從上句“故合者不為駢”看,此句當是“歧者不為枝”,方相對應。“枝”與“歧”誤置。
(十) “無所去憂也”: “去”往也。
語 譯
足的拇趾與二趾相連和手的六枝是與生俱來的啊,可不符合派生于本始的品性; 多余的大瘤子是在外形之上的啊,可不符合原生之質; 額外加上一個仁義來施用,擺在心臟里了啊,可不是本始和所派生品性的本來面貌啊。說起來,足的兩指連在一起,是連起了沒有用途的肉; 手指成為六枝,是戳立了一個沒有用途的手指;那種邪門歪道地施行仁義的,乃是對內心情性的連肉添枝,而外加于外部官能的施用呢。這么說,在視覺上連肉的,不就是搞亂五色,毀壞文彩,弄得五顏六色光亮刺眼嗎? 離朱就是這么做的。在聽覺上添數的,不就是搞亂五聲,毀壞六律,做成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嗎? 師曠就是這么做的。在仁上長枝杈的,不就是拔高品德,抑塞本性來沽名釣譽,讓天下人吹吹打打地遵奉那沒法做到的模式嗎? 曾、史就是這么做的。在論理上另外加碼的,不就是在堅白、異同等問題上費盡心力,空頭提出些沒用的言論嗎?楊、墨就是這么做的。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多余、連肉、外加、生枝的路數,不是天下最正規的東西。那最正規的東西,不違及事物的本然情性。所以,相合的并不是連肉,分歧的并不是生枝,長的不是有余,短的不是不足。因此,野鴨的腿雖然短,接上一塊就感覺不便; 鶴的腿雖然長,截去一段就大為痛苦。所以本來是長的就不必截斷,本來是短的就不必接長,用不著操這種心。看來仁義并不是人的情性啊,那些仁人們干什么多操這股心呢! 再說足的拇趾與二趾相連的,強行割裂就疼得哭泣; 手生六枝的,把它咬斷就疼得長號。這兩種情況一個是比應有的數多了出來,一個是比應有的數缺了一點,可遺憾是一樣的。當今的仁人們,緊皺雙眉關心社會的苦難; 不仁的人,沖破事物本然的情性去奪取貴富。這樣看來,仁義并不是人的情性啊!從夏、商、周及其以后,天下怎么竟是這樣吵吵嚷嚷呢!
原 文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一),是侵其德者也; 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二)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三),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三),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四),天下莫不奔命于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圣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于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谷(五),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 問谷奚事,則博塞以游(六)。二人者,事業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 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 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于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七);屬其性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八);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九);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解 說
(一)“待繩約膠漆而固者”:“繩約”從下文“約束不以纆索”及“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來看,此二字當是“纆索”。先輩已言及此,當從。
(二) “屈折禮樂,呴俞仁義”: “屈折”有委曲自己之意。“呴俞” 《集韻》:“色仁也。”愛撫之意。又《馬蹄》文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語意為足。“屈折禮樂”下當補“以匡天下之形”為是。
(三) “故天下誘然皆生” “同焉皆得”: “誘然” 互相吸引,表示聯系。“生”指生活。“同焉”共同,表示一致。“得”稱心如意。
(四)“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自虞氏”依史書之例,以為舜之稱,“虞氏”之上,必有“有”字,故當為之補出。但有的注家以 “自”為“有”之誤,似可商榷。因從句之結構言,有此“自”字,語氣方足,故非誤,而是下脫“有” 字。“撓”擾亂。
(五) “臧與谷”: “臧”“谷” 均是古代奴仆的名稱。
(六)“則博塞以游”:“博塞”成疏:“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所以有的注家以如擲骰子為解。不過,“博”是表示游戲的通辭,用它為稱的很多,如稱下棋為博奕,意思是決勝負,也就是“×賽”。因此,“博塞”就是“塞”的比賽。怎么個玩法,已不清楚。但從谷之為童年的奴隸,在郊外牧羊,大概不會太復雜,可能就是揀幾塊石子或瓦礫做博具,在地上劃幾個格子做盤,兩人共玩,互相截堵,被堵死的為負的一種玩法。
(七)“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 “臧”非上 “臧與谷”之臧,訓善,即美妙。下同。
(八)“屬其性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此處提出“五味”,顯得突然。其上并沒有講過五味,其下也沒有為之解說,孤立文中。不僅如此,文中提到“屬其性”的,都是接以“乎”字,獨此“五味”,所接的則是“于”。“非吾所謂”,就其所論的事項,各有專詞,獨此“五味”,以論仁義之“臧”來充任。有此數端,疑此為好事者,以文中有“五聲”、“五色”,認為也應有“五味”,便任意添入其中。《莊子》之書,行文結構謹嚴,文詞俏麗,決不會有此疏漏。故這幾句話當刪。
(九)“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 上有:“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兩提“仁義”顯然重復。所以致此,正由于再上提出過“屬其性于五味”,也像“屬其性乎仁義”一樣,謂為 “非吾所謂臧也”。因此,“非吾所謂臧”一個屬于 “仁義”,一個屬于“五味”。屬于“仁義”的為“臧于其德而已矣”固無問題。再一個當是“五味”,但“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則非“五味”所能承受。本文原是“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于其德,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于是裂“臧于其德”與“任其性命之情”為二,“任其性命之情”仍以“仁義”出之,遂成此重復現象。前既把“屬性于五味”刪除,在此亦當恢復本文原狀。
語 譯
再說那種必須用鉤繩規矩等工具來弄規正的,這是在削剝它們的本性啊; 那種必須用繩索膠膝等材料來弄堅實的,這是在侵害它們的品質啊; 拘制成禮樂來匡正天下人的形體,愛撫成仁義來撫慰天下人之心,這就損毀了他們的自然的本態。天下有著自然的本態。自然的本態,彎的不靠鉤,直的不靠繩,圓的不靠規,方的不靠矩,粘連不靠膠漆(附注: “附離” 同“附麗”),捆結不靠繩索。所以天下萬物都在相互聯系著生活,而不知為什么就來生活; 都在共同一致自由自在著,而不知為什么就自由自在。無論古今都是這樣,是無法改變的。那么,干什么仁義又接二連三地像膠漆繩索一樣在原始的本然、其派生的品性那里晃來晃去;弄得天下人糊里糊涂呢! 小的糊涂會使人改變方向,大的糊涂會使人改變本性。怎么知道是這樣呢? 自從虞舜揭出仁義擾亂天下以來,天下人都在為仁義而拼命,這不是把仁義用來改變他們的本性嗎? 且來試論一下: 從夏、商、周以來,天下人就都在把外物用來改變他們的本性了。下層的人不要命地逐利,士階層不要命地求名,貴族們不要命地為著家族興旺,圣人不要命地為著天下的治理。這幾類人做的事不同,名義也不一樣,但是就人損害本性、不要命的勁頭來說卻是一樣的。臧和谷兩個奴隸,一同放羊而都讓羊跑掉了。問臧干什么去了,他在捧著竹簡讀書了; 問谷干什么去了,他在玩“塞”的游戲了。兩個人做的事是不同的,可是就把羊跑掉來說卻是一樣的。伯夷為了名死在首陽山下,盜跖為了利死在東陵上。兩個人的死的目的是不同的,可是就殘害生命損害本性來說,都是一樣的,怎么一定認定伯夷就對而盜跖就不對呢?天下都在拼命,他們所拼的是仁義,世俗就說是君子;所拼的是貨財,世俗就說是小人。他們在拼命上是一樣的,可就有君子,有小人。可像他們那樣殘害生命損害本性,盜跖也就是伯夷了,又在其中怎么分君子、小人呢! 再說,那把本性交給了仁義的,雖然好到曾、史那樣,我也不認為美妙; 把本性交給了五聲的,雖然好到師曠那樣,我也不認為能聽; 把本性交給了五色的,雖然好到離朱那樣,我也不認為能看。我所認為美妙的,指的并不是仁義,修好品德,任從本然的情性也就是了; 我所認為能聽的,不是說能聽別的東西,能聽自己也就是了; 我所認為能看的,不是說能看別的東西,能看自己也就是了。那種不能看自己而能看別的東西,不能自己快意而求別的快意的,這是快別人的快意而不快自己的快意的,是安于別人的安適而不安于自己的安適的啊。那樣安于別人的安適而不安于自己的安適,不管盜跖還是伯夷,同樣是邪門歪道。我怕玷污了本然和它派生的品性,所以上不敢為仁義的操守,下不敢去做邪門歪道的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