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虎丘》原文,注釋,譯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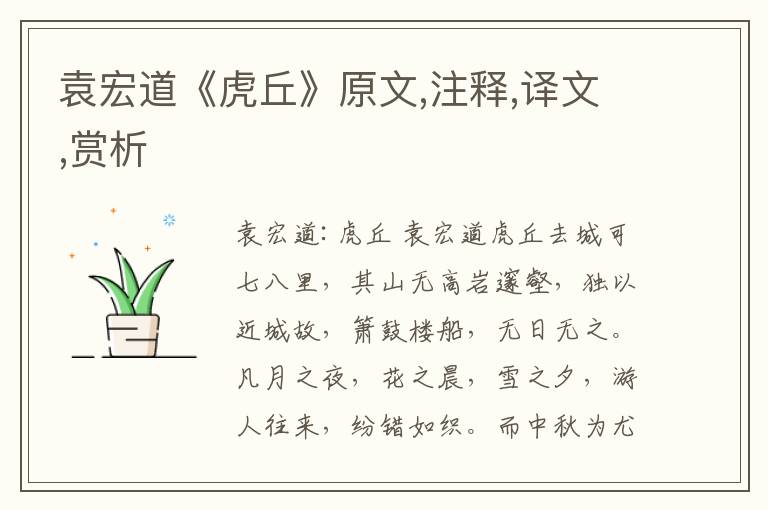
袁宏道:虎丘
袁宏道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
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云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shù)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fā),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fù)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fā),響徹云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云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余與江進之謀所以復(fù)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于其中,而病尋作;余既乞歸,恐進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后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余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余言否耶?
袁宏道于萬歷二十三年(1595)二月由京都赴吳縣令職。兩年之后,于萬歷二十五年(1597)春解官。即在此年寫下這篇虎丘游記,綜合記敘了為官二載六登虎丘的深切感受。
文章開頭“虎丘去城可七八里”一句,不僅在于交代其方位,更主要的是強調(diào)其臨近蘇州的優(yōu)越位置。虎丘名勝聞名遐邇,袁宏道數(shù)次登臨,耳聞目睹,對虎丘之盛自有卓見,認為“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此即虎丘名勝與名山大川的不同處。也正因如此,“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招來紛錯如織的游人。足見虎丘風(fēng)物具有無限誘人的魅力。作者間接寫虎丘的山水之美,進一步補充游人眾多“獨以近城故”,同時也點出領(lǐng)略虎丘風(fēng)采的好時辰。“而中秋為尤勝”,作者以一個“尤”字,強調(diào)出游賞虎丘以中秋節(jié)最佳,從而暗示虎丘之盛的最佳境界,以誘發(fā)讀者對良辰美景中的虎丘風(fēng)韻的神往。
那是一種什么情景呢?“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此非夸張之語。蘇州舊俗,中秋之夜有“走月亮”之舉,而以虎丘為目的地。所以此間上至“衣冠士女”,下至“蔀屋”的細民,都按照傳統(tǒng)的習(xí)俗,“靚妝麗服”,至虎丘“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這就出現(xiàn)一個十分熱烈的場景:“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云瀉”。千人石在虎丘中心,是一塊由南向北傾斜的平坦大盤石,約有一二畝之大。在這寬闊平坦之處,人們似魚鱗和梳齒一般密集地排列著,所攜之檀板多至如丘積,紛紛傾酒又好似云瀉。這是何等動人的情景啊!接著,作者更以獨具只眼的審美目光,作出奇妙的比喻:“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這是一個充滿著詩情畫意的場面。那密密層層的人群正象平沙之落雁,觀其色恰如江上之鋪霞,聞其聲又似雷鳴電閃。作者以視覺與聽覺相兼并出的方法,描摹了虎丘中秋之游給人的美感。對其境界之美,作者“無得而狀”,覺得簡直是妙不可言。
虎丘之盛尚不僅如此。作者在從總體上作出鳥瞰描述之后,又轉(zhuǎn)入更為具體的藝術(shù)描繪,展現(xiàn)“中秋為尤勝”的另一番精彩的情景。作者仿佛在記敘一場美妙的音樂會。這里有“聲若聚蚊,不可辨識”的千百人齊唱;又有數(shù)十人搖頭頓足之舉;也有三、四人“屬而和者”;還有“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更有“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fā),響徹云際”的妙境。從“布席之初”到“明月浮空”,再到夜深人靜之時,歌唱者由多至寡。這是隨時間推移而出現(xiàn)的實況,記敘得井然有序。同時,作者也確在逐步地推出自己審美意趣的所在。袁宏道在敘述布席之初熱鬧非凡的場面以后,特別勾畫出兩幅美景:“明月浮空,石光如練”,“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只有此時,“竹肉相發(fā),清聲亮徹”,才令“聽者魂銷”;也只有此刻,“簫板亦不復(fù)用”,屏息聆聽那“音若細發(fā),響徹云際”的一夫歌唱,才有“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的神奇妙境。這就是虎丘徹夜笙歌的盛況。動人的習(xí)俗,誘人的風(fēng)光,在作者筆下呈現(xiàn)出迷人的境界。這該是袁宏道眼里“中秋為尤勝”的原因吧。
然而,虎丘亦有其勝景。因此作者又調(diào)轉(zhuǎn)筆鋒描繪其自然景色,對虎丘風(fēng)光之盛作出有力的補充。此時,作者不再作面面俱到的描繪,只是信手拈出一二景物來。那因“飛巖如削”,而顯得“深不可測”的劍泉;“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的千頃云山;“晚樹尤可觀”的文昌閣;“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的平遠堂舊址。這些都是虎丘特有的自然景致。作者一邊記敘,一邊講述自己的感受。言千頃云山的競秀,就有了“最可觴客”的意念;言其“過午則日光射人”,即有“不堪久坐”的想法;因欲復(fù)平遠堂祠韋蘇州、白樂天之事未成,而發(fā)出“山川興廢,信有時哉”的感慨。對自然景物的描繪,正體現(xiàn)作者審美意趣的選擇,而主觀感情的融入,又使其形成一種新的審美意境。這正是袁宏道“情與景會,頃刻千言”(《敘小修詩》)的藝術(shù)追求。
作者對虎丘風(fēng)光何以有如此深的感受呢?“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是其主要原因。他六上虎丘,足以說明對虎丘山水風(fēng)光的深切迷戀。作者最后一次登臨虎丘,竟出現(xiàn)“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的事,使其游興受挫,因而感慨系之:“甚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在他看來,正是這頂“烏紗帽”,使自己連游覽虎丘都不能盡興。在客觀上顯示出官與民之間的對立。同時,其對官場生涯的鄙棄和對山水風(fēng)光迷戀之情亦躍然紙上。因此,他在追述虎丘風(fēng)光勝景時,慶幸自己解官稱“吳客”,而遙問上天:“虎丘之月,不知尚識余言否耶?”以表白自己寧去官以戀山水的癡情。我們欣賞《虎丘》,似在觀賞一件色彩明麗、姿態(tài)萬千、情趣盎然的虎丘風(fēng)光繡品。應(yīng)該說,這一藝術(shù)珍品,正是以虎丘的自然風(fēng)物為經(jīng),以作者內(nèi)心情感為緯繡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