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之十)》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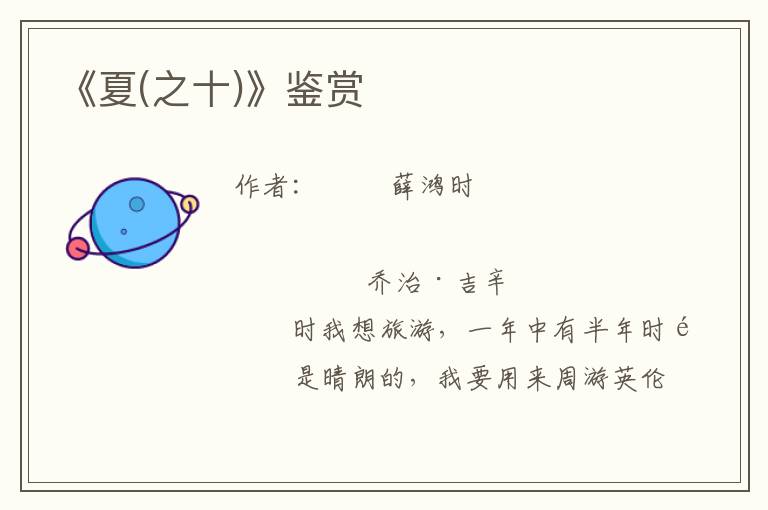
作者: 薛鴻時
喬治·吉辛
有時我想旅游,一年中有半年時間是晴朗的,我要用來周游英倫三島。那里有很多我從未看過的美好而又有趣的東西。對于我這可愛的家園,如果有一個角落沒有游到,我會死不瞑目的。我經(jīng)常在幻想中閑逛著所有我知道的地方。有些地方,地名熟悉,但其形景在頭腦中沒有印象,這使我坐臥不安,渴望一游。我書架上陳列著一排排郡縣旅游指南(它們擺在書攤上時,總使我禁不住要買),使我神往;其中唯一使我感到枯燥無味的是那些描述工業(yè)生產(chǎn)城市的篇章。然而,我決不會作這種遠(yuǎn)游了,我太老了,生活習(xí)慣已經(jīng)定型了。我不喜歡坐火車,也不喜歡住旅館。如果離開我的藏書室、花園,和我窗外的風(fēng)景,我真會懷思鄉(xiāng)病。而且,我有一種恐懼:怕死在異鄉(xiāng),而不是死在自己的家里。
曾經(jīng)魅惑過我們的地方,或是,在回憶中似曾吸引過我們的地方,一般說來最好只在幻想中重游。我說似乎魅惑過我們,因為對于自己曾經(jīng)留戀過的地方,我們的記憶經(jīng)過了相當(dāng)時間后,往往和當(dāng)時得到的印象只有輕微的相似。那些事實上極為一般的賞心樂事,或那些受內(nèi)心情緒與外界環(huán)境很大影響的樂趣,久后回憶起來,顯得分外歡樂,或顯得分外深切。在另一方面,若是記憶不能創(chuàng)造幻象,而某些地方的名字又與生命中某個黃金時刻聯(lián)系在一起,要想在再一次訪問中重獲過去的感受,便是一種魯莽的想法。因為人們看到景物并不是引起歡樂與寧靜的唯一原因,無論那個地方多么可愛,無論那兒天空多么燦爛,這些外界事物并不足以使心中快樂;只有作為一個人的基本要素的心靈激動時,才能得到快樂。
今天下午,我在讀書時,我的思想開了小差,我發(fā)現(xiàn)自己在回憶著薩福克的山坡。二十年前仲夏的一天,走了一段長路后,我坐在那兒休息,昏昏欲睡。一種強烈的渴望抓住了我,我想立即出發(fā),再找到那高高榆樹下的地方。在那兒,我含著煙斗,從容吮吸,聽得見周圍金雀花的花莢在正午艷陽下裂開,畢畢剝剝地響。如果憑著這種沖動行事,我有什么機會重享我記憶中所珍藏的那一時刻的樂趣呢?不,不,我所記的并不是那個山坡,而是那個生命的時刻,由當(dāng)時的環(huán)境、心境幸福地湊在一起的那個時刻。我能否夢想在同一山坡,在同樣的艷陽天吸著煙斗,就能嘗到當(dāng)時那種樂趣,或獲得同樣的安慰呢?我腳下的草皮會和當(dāng)時一樣的柔軟嗎?大榆樹的枝葉會那樣愉快地隔開照耀其上的中午陽光嗎?當(dāng)休息時間過去了,我會象從前那樣跳躍而起,急于再次使出我的力量嗎?不,不,我所記憶的僅只是我早期生命的一個時刻,偶然地與薩福克的風(fēng)景畫面聯(lián)系在一起。這個地方不再存在了,除了對于我之外,它永遠(yuǎn)也不存在了。我們的心靈創(chuàng)造了周圍的世界,縱使我們肩并肩地站立在同一個草地上,我的眼睛決看不到你所看到的一切,我心中的感受決不會與你相同。
(鄭翼棠 譯)
本篇選自英國作家喬治·吉辛(1857—1903)的名著《四季隨筆》,此書原名《亨利·賴伊克洛夫特私人文稿》,是吉辛的晚年作品,出版于他逝世的那一年。吉辛曾在日記中寫道:“我敢肯定,沒有人曾度過象我這樣悲慘的一生。”他才氣橫溢,早年是歐文斯學(xué)院公認(rèn)的高材生,幾乎拿到了學(xué)院的所有各項獎金、獎狀,但是在他19歲那年,因幫助一名妓女偷錢,結(jié)果被學(xué)校開除,斷送了成為專家、學(xué)者的前途。他在文學(xué)園地上辛苦耕耘二十余年,雖碩果累累但一生未能擺脫貧困,加上不幸的婚姻和嚴(yán)重的肺病,終于導(dǎo)致他的早逝。《四季隨筆》偽托亨利之名,實際上是吉辛的一部回憶往事的抒情散文,當(dāng)時他和加布里埃爾·弗勒里一起居住在法國,由于他未能與妻子伊迪絲·恩德伍德正式辦離婚手續(xù),所以他和弗勒里的婚姻是非法的,這就決定了他們永遠(yuǎn)不能回英國定居。此時吉辛已病入膏盲,對英國風(fēng)物、氣候甚至飲食都充滿懷戀,心境無限悲涼,只能通過回憶來排遣綿綿不盡的鄉(xiāng)愁。
第一段寫英國有半年時間天氣晴好,而山川景物絕佳,作者渴望游遍英倫三島的每一個角落,然而因年老體衰、生活習(xí)慣已經(jīng)定型而不能旅游了。這里所說的理由是托詞,其實是別有難言的苦衷。
第二段另起新意:即使有機會尋訪舊蹤跡也是枉然。因為,某種景物、風(fēng)光只有在某個特定的時刻與你當(dāng)時的心境相結(jié)合,才會使你激動并融入永久的記憶中。生命中的黃金時刻一去不復(fù)返,事過境遷,即使你重新見到曾帶給你賞心樂事的場景,你的感受也必定與當(dāng)時的印象截然不同。
第三段具體描繪珍藏在作者心底的薩福克郡的那個小山坡:高高的榆樹、柔軟的草皮、在艷陽下裂開的花莢……二十年前的情景宛如目前,讓人恨不得立即出發(fā)去找回當(dāng)時的感覺。然而,作者清醒地知道:僅僅存在于記憶中的良辰美景是永遠(yuǎn)也找不到的。接著作者又宕開去,發(fā)揮這樣一個想法:兩個人同時去往某地,面對完全一樣的景物,他們的感覺也是完全不同的,因為我們的感官在反映客觀世界時,我們的心靈卻在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世界。美是客觀的嗎?美僅僅是自然物的屬性嗎?這是不確的,因為“自然物的屬性只要沒有感官缺陷的人都能感覺到,而且所感覺到的彼此大致相同,美卻隨社會歷史條件不同,對于不同的人發(fā)生不同的效果。”(朱光潛)在這里,吉辛表達(dá)了一個真正藝術(shù)家的深刻感受,從中我們可以悟出“美是主、客觀的統(tǒng)一”這個道理。
這篇作品文字不長,但宛轉(zhuǎn)跌宕、一波三折,表現(xiàn)出吉辛那典雅而又清純、流麗,含蓄又充滿激情的風(fēng)格。吉辛早年寫過詩,他精通希臘、羅馬古典詩歌,深厚的學(xué)識修養(yǎng)使他的抒情散文達(dá)到了詩的境界,或者,它們就是散文詩。當(dāng)然,這一切只有從原文中才能充分品味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