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宋遼金元兵法·何博士備論》原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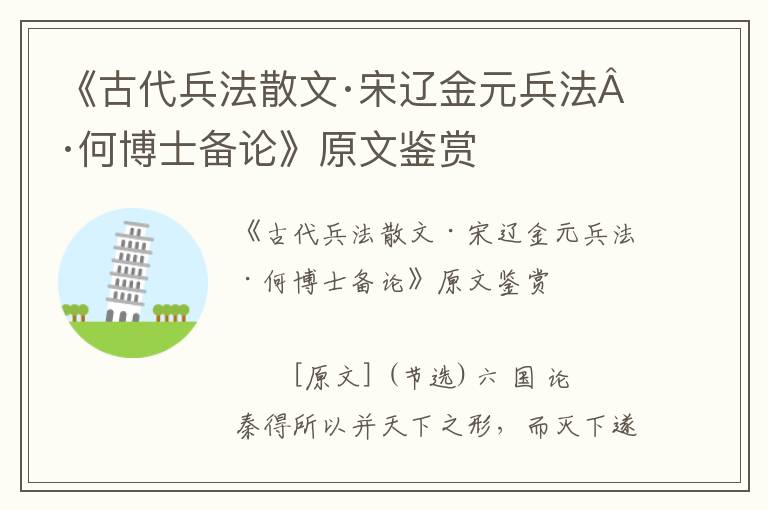
《古代兵法散文·宋遼金元兵法·何博士備論》原文鑒賞
[原文] (節選)
六 國 論
秦得所以并天下之形,而滅下遂至于必可并,六國有可以拒秦之勢,而秦遂至于不可拒者,豈秦為工于斃六國耶?其禍在乎六國之君,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仇故也!
秦之為國,一而已矣,而關東之國六焉。計秦之地,居六國五之一;校秦之兵,當六國十之一。以五一之地,十一之兵,而常擅其雄強,以制天下之命者,由其據形便之居,俯扼天下之吭,而蹈其膺背于足股之下故也。使六國之君,知夫社稷之實禍在秦,而相與致誠締交,戮力以擯秦,即秦誠巧于攻斗,則亦何能鞭笞六國,估之駢首西向而事秦哉?又況得以一一而夷滅之也?蓋其不知慮此,凡所以早朝而晏罷者,皆其自相屠斃之謀。此秦所以得收其敞,而終為所擒也。
蓋六國之勢,莫利于為縱,莫害于為橫。縱合則安,橫成則危,必然之勢也。方其為縱于蘇秦也,秦人不敢窺兵函谷關者十五年。已而為橫于張儀,而山東諸侯歲被秦禍,日割地以求事秦之歡,卒至于地盡,而國為墟。六國固嘗收合縱之利矣,然而終敗于為橫之害者,其禍在乎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仇故也!所謂戰所可親,忘所可仇者,秦人稍蠶食六國而并夷之,則關東諸侯皆與國也,宜情親勢合,以謀抗秦。然而齊、楚自恃其強,有并吞燕、趙、韓、魏之志,而緩秦之禍;燕、趙、韓、魏自懲其弱,有疑惡齊、楚之心,而脅秦之威。是以橫人得而因之,散敗從約。秦以氣恐而勢喝之,故人人震迫,爭入購秦,唯恐其獨后之也。曾不知齊、楚雖強,不足以致秦之畏,而其所甚忌者,獨在乎韓、魏也。韓、魏者,實諸侯之西蔽也,勢能限秦,而使之無東。秦茍有以越之,我得以制其后,此秦之所忌。使齊、楚、燕、趙審夫社稷之實禍在秦,而知韓、魏之為蔽于我,委國重而收親之。固守縱約,并力一志,以仇虎狼之秦,使其一下兵于六國,則六國之師悉合而從之,則秦甲不敢輕越函谷,而山東安矣!
或曰:韓、魏者,秦之錯壤也。奏兵之加韓、魏也,戰于百里之內;其加于四國也,戰于千里之外。韓、魏之致秦兵,近在乎一日之間。而其待諸侯之救,乃在乎三月之外。秦攻韓、魏,既歸而休兵,則四國之乘徼者尚未及知也。今徒執虛契以役韓、魏,則秦人固將疾攻而力蹶之,是使二國速被實禍,而齊、楚、燕、趙反居齒寒之憂,非至計也。噫! 齊、楚、燕、趙之民,裹糧荷戟以應秦敵者,無虛歲也,然終不能紓秦患于一日。四國誠能歲更各國之一軍,命一偏將提之以合戍韓、魏,而佐其勢,則是六國之師,日萃于韓、魏之郊,仰關而伺秦。秦誠勇者,雖日辱而招之,固不輕出而以腹背支敵矣。
夫蘇秦、張儀,雖其為術生于揣摩辨說之巧,人皆賤之,然其策畫之所出,皆足以為諸侯之利害,而成敗之。蓋蘇秦不獲終見信于六國,而張儀之志獨行于秦,此六國之所以見并于秦也。
嗟乎! 使關東之國裂而為六者,豈天所以終相秦乎?向使關東之地合而為一,以與秦人決機于韓、魏之郊,則勝負之勢蓋未可知。使齊能因其資而遂并燕、趙,楚能因其資而遂并韓、魏,則鼎足之勢可成。以其為國者六,是以秦人得以間其歡而離其交,終于一一而夷滅之。悲夫!
秦 論
兵有攻有守,善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
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強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卻之也。圖拒以卻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于轉戰,救敗之師利于固守,兵之常勢也。
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于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為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為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為向日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
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杰爭西向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倔起之匹夫,其存亡勝敗之機,敗決于一戰,其鋒至銳也! 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大險,渡漳逾洛,左馳右鶩,以嬰其四合之鋒,卒至于敗。而沛公之眾,揚袖而下控函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于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
夫秦役其民以從事于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于公斗、樂于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為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余。周文常率百萬之師附于城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關固守為救敗之師,關東之士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
或曰: 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于吳楚,以為不知杜成皋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皋者數十輩,遂至于敗亡。今豪杰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轉戰何也?嗟夫! 務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為兵亦疏矣!
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眾亦銳于亡秦,是以豪杰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為秦役矣。漢無可叛之釁,而天下之民無志于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為漢役者也。以不為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為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地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
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譏于后世。彼二子者,固非愚于事機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至于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楚 漢 論
王天下者,其資有三: 有以德得之; 有以力并之; 有以智取之。得之以德者,三代是也;并之以力者,秦人是也;取之以智者,劉漢是也。蓋以力則不若智之勝,以智則不若德之全。
至于項羽之爭天下也,其所執者為何資耶?德非羽之所得言者矣,其于智、力之資又皆兩亡焉。而后世之議乃曰:“項羽其亦不幸遇敵于漢,而遂失之。”嗟夫! 雖微漢高帝,而羽之于天下固將失之也。漢王之于智蓋疏矣! 以其能得真智之所在,此所以王。項羽之力嘗強矣! 以其不知真力之所在,此所以亡。
彼項羽以百戰百勝之氣,蓋于一時,手裂天下以王豪杰而宰制之,自以天下莫能抗也。觀其所賴以為資,蓋有類乎力者矣。雖然彼之所謂力者,內恃其身之勇,叱咤震怒足以威匹夫;外恃其眾之勁,搏卒決戰,足以吞敵人而已。至于阻河山、據形便,俯首東瞰,臨制天下,保王業之固,遺后世之強,所謂真力者,彼固莫或之知也。是以輕指關中天險之勢,燔燒屠戮,以逞其暴。卒舉而遺之二三降虜,反懷區區之故楚,而甚榮其歸。乃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能知者?”此特淺丈夫之量,安足為志天下者道哉?
后之數羽之罪者皆曰:“奪漢王之關中,負信義于天下,此所以亡。”嗟夫!使項氐無意于王,而徒奪漢王之關中,則謂其得罪于區區之信義,可也。如其有意于王而奪之,是得計也!惟其知奪而不知有,此所以亡耳! 古者創業造邦之君而為是之為者可勝罪哉!
韓信未釋垓下之甲,而高祖奪其兵,不旋踵而又奪其齊。然而智者不非而義者不罪者,以其為天下者重,而負人者輕故也。是以不顧意氣之微恩,而全社稷之大計也。漢高祖挾其在己之智術,固無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歸之者,蓋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則天下之智皆其資也。此所謂真智者也! 又其所負者帝王之度,故于其西遷也,則曰:“吾亦欲東耳!安能悒悒久居此乎!”此其與項羽異矣。
雖然,使無智術之士,以主其謀,則天下之事亦去矣。方其入關,乃封秦府藏還軍霸上,其畫婉矣。乃怵于妄議,一旦拒關無納東兵,以逆其眾集之鋒,幾不免于項氏之暴。使遂卑而驕之,當能舒徐拱揖,以得項王之歡心,莫枕而王關中,撫循其眾,徐為后圖,則天下不足定矣。幸而復獲漢中之遷,因思歸之士并三秦、定齊趙、收信越,以與項王親角者數歲,僅乃得之。
向使項羽據關而王,驅以東出,使與韓、彭、田、黥之徒,分疆錯壤以弱其勢,則關東之土尚可得兼哉?信乎!王者之興,固有所謂驅除者也!
晁 錯 論
古者持國任事有四臣焉:杜患于未兆,弭災于未形者,賢臣也;禍結而排之使安,難立而戡之使平者,功臣也; 國安矣,挈而錯之危世,治矣,汩而屬之亂者,非愚臣即奸臣也。蓋奸臣之不足者忠,愚臣之不足者知。忠、知不足而持國任事,禍之府也。
昔者晁錯嘗忠于漢矣,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權也。是以輕發七國之難,而其身先戮,于一人之言可不謂愚乎?彼錯者為申、韓之學,銳氣而寡恩,好謀而喜功之臣也。自孝景之居東宮,而錯說之以人主之術數也,固以知寵之矣! 及其即位,而以天下聽之。彼挾其君之以天下聽之也,欲就其所謂術數之效,是以輕為而不疑,決發而不顧,卒以憂君危國幾成劉氏之大變。而后世之士猶或知之,獨子云乃謂之愚。
子云之愚錯也,非以其知不足以衛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國未發之禍,而故趨之于亂也。東諸侯之勢誠強矣。強而驕,驕而反,其理也。然而束之而使無驕,御之而使無反者,豈固無術耶?而錯之策曰; 削之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是錯之術無他,趣之以速反而已。錯之所謂禍小者,以吾朝削其地而暮得其民故也。
安有數十年拊循之民,一旦而遂不為之役也?吳王所發五十萬之眾者,皆其削郡之民也。連七國百萬之師,西向而圖危關中,乃曰禍小者,真愚也! 夫七國之王,獨吳少嘗軍旅,為宿奸、故惡。其六王皆驕夫孱稚,非有高材絕器、挾智任術,足以就大計者。其謀又非前締而宿合之也。今一旦倘徉相視而起,皆吳實迫之,欲并以為東帝之資耳!
當孝文之世,濞之不朝,發于死子之隙,而反端著矣。賈誼固嘗為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包匿,不窮其奸,而以恩禮羈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余年而濞無他變也。濞之反于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吳者四十三稔矣。齒發固已就衰,而向之勇決之氣與夫驕悍之情、窺覬之奸皆已沮釋矣!今一旦奮然空國西向,計不反顧者,濞豈得已哉?有錯之鞭趣其后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濞者三郡,且南面而撫其國者四十余年。錯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趙諸齊皆以暗隱徽慝奪其封國之半,彼固知其地盡而要領隨之。是以出于計之無聊,為一決耳!
向使景帝襲孝文之寬殺而恩禮有加焉,而錯出于主父偃之策,使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弱其勢。則濞亦何事乎?白首稱兵冀所非望,而楚、趙諸齊不安南面之樂,而甘為濞役也?
吳王,反虜也,固天人之所共棄,未有不至于敗滅者。然亦幸其未為曉兵者也! 使其誠曉兵,則關東非漢有而錯之罪可勝戮哉! 方濞之起也,其謀于宿將,則曰:必先取梁。其謀于新將,則曰:必先據洛。二策皆勝策也。而吳王昧于所用,故敗亡隨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王,景帝之親母弟,國大而強。北距泰山,西界高陽。今釋梁不下,而兵遂西。則漢沖其膺,梁壽其吭,不戰而成擒矣。此宿將以先取梁為功者,圖全之策也。所謂以正合者也。洛陽阻山河之固,扼西兵之沖;積武庫之械,豐敖倉之粟。今不疾據而徐行留攻,則漢騎騰入梁楚之郊以蹙之,敗可立待也。此新將以先據洛為功者立奇之策也。所謂以奇勝者也。二策者皆勝策也。雖反國之虜無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數也。幸其當時無以雙舉而并施之以教之也。是以吳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據洛,此所以亟敗也。
所謂雙舉而并施者,銳師卷甲以趣洛陽,重兵疾攻以覆梁都。雖無能入關,而山東舉矣。知取梁而不知取洛,取漢兵得以東下。知據洛而不知取梁,則渠兵得以躡后。使銳師據洛,而重兵攻梁,洛已據則漢兵不能即東。漢兵不東,則必舉梁,梁舉而山東定矣。幸其不出于此,乃屯聚而不分,以壓梁壁。梁未及下,而亞夫之輩馳入滎陽而壁昌邑矣。求戰不得,欲去不可,傍徨無所之,而坐成擒。故曰: 幸其未為曉兵者也!
向使吳王兩用其策,而又假田祿伯以偏師,提之以趨武關; 周丘長驅,遂歷陽城之北,反雖不遲而禍實大矣! 嗚呼! 孰謂晁錯非真愚者哉?
漢武帝論
兵有所必用,雖虞舜、太王之不欲,固常舉之。有所不必用,雖蚩尤、秦皇之不厭,固當戰之。古之人君有忘戰而惡兵,其敝,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勢蹙于弱而不能振; 有樂戰而窮兵,其敞,天下皆得以乘之,故其勢蹶于強而不知屈。然則兵于人之國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矣!
西漢之興,歷五君而至于孝武。自高帝之起匹夫,誅強秦,蹙暴楚。已而平反亂,征不服,迄終其世而天下伏尸流血者二十余年。呂后、惠、文乘天下初定,與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其于兵也,固憚言而厭用之也,可謂知天下之勢矣! 孝景之于漢也,蓋威可抗,而兵可形之時也。然而即位未幾,卒然警于七國之變,故其志氣創艾,亦姑安天下之無事,未暇為天下之勢慮也。然其為漢之勢,亦浸以趨弱矣!
孝武帝以雄才大略承三世涵育之澤,知夫天下之勢將就弱而不振,所當濟之以威強,而抗武節之時也。方是時也,內無奸變之臣,外無強逼之國,而世為漢患者獨匈奴耳。
夫匈奴自楚漢之起,乘秦之亂,復踐河南之地而其勢始強。高帝曾以三十萬之眾困于白登之圍,蓋士不食者七日。已解而歸,不思有以復之而和親始議矣。高后被其媼書之辱,臨朝而震怒矣。終之以婉辭順禮,慰適其桀驁之情。凡此者皆欲與民息肩,姑置外之而不校也!
孝文之立,其所以順悅輸遺者,甚至飾遣宗女以固其歡。蓋送車未返,而彼已大舉深入,侯騎達于甘泉、雍梁矣。其后乍親乍絕,蓋為寇患,至于近嚴霸上、棘門、細柳之屯,以衛京都。以孝文之寬仁、鎮靜,攝衣發憤,親駕而驅之者再。乃至乎輟飯搏髀,而思頗、牧之良能也! 孝景之世,其所以悅奉之情與夫遺給之數又加至矣。然其寇侵之暴,紛然其不止也。
由是觀之: 漢之于匈奴,非深懲而大治之,則其為后患也,可勝備哉?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氣,選徒習騎,擇命將帥,先發而昌誅之。蓋師行十年,斬刈殆盡,名王貴人,俘獲百數。單于捧首,窮遁漠北。遂收兩河之地而郡屬之。刷四世之侵辱,遺后嗣之安強。至于宣、元、成、哀之世,單于頓顙臣順,謁期聽令以朝,位次比內諸侯。雖曰勞師匱財,而功烈之被遠矣。
使微孝武,則漢之所以世被邊患,其戍役轉餉以憂累縣官者,可得而預計哉?甚矣! 昧者之議,不知求夫天下之勢強弱之任所當然者, 而猥曰, 文、景為是慈儉愛民, 而武帝黷于兵師,祈至與秦皇同日,而非詆之,豈不痛哉?
使孝武不溺于文成、五利之奸,以重耗天下;攘敵之役止于衛、霍之既死,而不窮貳師之兵,則其功烈與周宣比隆矣。
李 陵 論
善將將者不以其將予敵,善為將者不以其身予敵。主以其將予故,而將不辭,是制將也;將以其身予敵,而主不禁,是聽主也。故聽主無斷,而制將無權,二者之失均焉。
漢武召陵欲為貳師將輜重也。而陵惡于屬人,自以所將皆荊楚勇士、奇才、劍客,愿得自當一隊,以步卒五千涉單于庭,而無所事騎也。夫所謂騎者,匈奴之勝兵長技也。廣澤平野,奔突馳踐,出沒千里,非中國步兵所能敵也。以匈奴之強,兵騎之眾,居安待佚為致敵之主,而吾欲以五千之士,擐甲負糧,徒步深入,策勞麾憊為赴敵之客,是陵輕委其身以予敵矣! 而漢武不之禁也,乃甚壯之而聽其行。上無統帥而旁無援師,使之窮數十日之力,涉數千里之地,以與敵角而冀其成功。陵誠勇矣! 雖其所以摧敗,足以暴于天下,卒以眾寡不敵,身為降虜,辱國敗家,為天下笑者,是漢武以陵與敵也。故曰:二者之失均焉。
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陵提五千之士,孤軍獨出當單于十萬之師,轉斗萬里,安得不為其所擒也。是以古之善戰者無幸勝,而有常功。計必勝而后戰,是勝不可以幸得也。度有功而后動,是功可以常期也。
秦將取荊,問其將李信曰:“度兵幾何而足?”信曰:“二十萬足矣!”以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君甚壯信,而怯翦也。遂以二十萬眾,信將而行,大喪其師而還。秦君大怒,自駕以請王翦。翦曰:“必欲用臣,顧非六十萬人不可也!”秦君曰:“謹受命。”翦遂將之,卒破荊而滅之焉。
冒頓單于媼辱呂后,漢之君臣廷議欲斬其使,遂舉兵擊之。樊噲請曰:“愿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 昔高祖以四十萬眾。困于平城。噲奈何欲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也!”呂后大悟,遂罷其議。向使王翦徇秦君,以將予敵而不辭;呂后聽樊噲,以身予敵而不禁,則二將之禍可勝悔哉!
夫李廣、李陵,皆山西之英將也。材武善戰,能得士死力,然輕暴易敵,可以屬人,難以專將。世主者茍能因其材而任之,使奮勵氣節,霆擊鷙搏,則前無堅敵,而功烈可期矣! 漢武皆乘其所任,二人者終僨蹶而不濟,身辱名敗,可不惜哉!
大將軍衛青之大擊匈奴也,以廣為前將軍。青徒廣出東道,少回遠,乏水草。廣請于上曰:“臣部為前將軍,令臣出東道。臣結發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臣愿居前,先死單于。”而青陰受上旨,以廣數奇,無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廣遂出東道。卒以失期自殺。夫以廠之材勇,得從大將軍,全師之出,其勝氣已倍矣。又獲居前以當單于,此其志得所逞,宜有以自效,無復平日之不偶也。奈何獨摧擯之,使其枉道他出,遂死于悒悒,而天下皆深哀焉?
至若陵也,又聽其以身予敵,而棄之匈奴,僥幸于或勝。及其以敗聞,徒延首傾耳,望其死敵而已,無他悔惜也!嗟夫! 漢武之于李反,不得為無負也!蓋用廣者失于難, 而用陵者失于易,其所以喪之者一也。
賈復,中興之名將也。世祖以其壯勇,輕敵而敢深入,不令別將遠征,當自從之。故復卒以勛名自終。
蓋壯勇輕敵者可以自從,而別將遠征之所深忌也。觀賈復之所以為將,無以異于陵、廣也,而世祖不令別將遠征,常以自從者,是明于知復,而得所以馭之之術也。故卒收其效,而全其軀。不然則復也亦殞于敵矣!嗚呼!任人若世祖者幾希矣。
蜀 論
或曰: 劉備之爭天下也,不因中原而西入巴蜀,此所以據非其地,而卒以不振歟! 曰: 有之也。備非特委中原而趨巴蜀也,亦爭之不可得,然后委之而西入耳! 備之西者,由智窮力憊,蓋晚而后,出于其勢之不得已也。
方其豪杰并起,而備已與之周旋于中原矣。始得徐州,而呂布奪之; 中得豫州,而曹公奪之; 晚得荊州,而孫權奪之。備將興復劉氏之大業,其志未嘗一日而忘中州也。然卒無以暫寓其足,委而西入者,有曹操、孫權之兵軋之也。備之既失豫州,而南依劉表也,始得孔明于羈窮困蹙之際。而孔明始導之以取荊取益,而自為資。孔明豈以中州為不足起,而以區區荊益之一隅足以有為耶?亦以魏制中原,吳擅江左,天下之未為吳魏者,荊益而已。顧備不取此,則無所歸者故也。是以一敗曹公,而遂收荊州,繼逐劉璋,而遂取益州者,孔明之略也。雖然,孔明之于二州也,得所以取之,而失所以用之。至于遂亡荊州,而勞用蜀民,功業亦以不就,良有以也!
夫荊州之壤,界于吳蜀之間,而二國之所必爭者也。自其勢而言之: 以吳而取荊則近而順,以蜀而爭荊則遠而艱。蜀之不能有荊,猶魏之不能有漢中也。是以先主朝得益州,而孫權暮求荊州。權之求之也,非以備之得蜀而無事乎荊也。亦以其自蜀而爭之不若乎吳之順故也。故直求之者,所以示吾有以收之也。蓋備一不聽而權已奪其三郡。備無以爭,而中分畀之。以分裂不全之荊州,而有孫權之窺聽其后,為之鎮撫則安,動復則危。亮不察此,而恃關侯之勇,使舉其眾以北侵魏之襄陽。故孫權起躡其后,殺關侯而盡爭其荊州。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荊也。然后備之所有獨岷益耳! 雖然,地僻人固,魏人不敢輕加之兵,而鼎足之形遂成。使備之不西,而唯徘徊于中州,則亦不知所以稅駕矣。
備之既死,舉國而屬之孔明。孔明有立功之志,而無成功之量:有合眾之仁,而無用眾之智。故嘗數動其眾而亟于立功。功每不就,而眾已疲。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蜀也。夫蜀之為國,巖僻而固,非圖天下者所必爭,然亦未嘗不忌其動。以其有以窺天下之變,出而乘之也。雖然,蜀之與魏,其為大小強弱之勢,蓋可見也。曹公雖死而魏未有變,又有司馬仲達以制其兵。孔明于此,不能因備之亡深自抑弱,以盈怠其心,使共無意于我,勵兵儲粟,伺其一旦之變,因河渭之上流,裹糧卷甲,起而乘之,則莫不得志。乃以區區新造之蜀,倡為仁義之師,強天下以思漢,日引而北以求吞魏,而復劉氏。故常千里負糧, 以邀一日之戰。不以敗還, 即以饑退, 此其亟于有功而亡其量以待之也。
善為兵者,攻其所必應,擊其所不備而取勝也,皆出于奇。孔明連歲之出,而魏人每雍容不應,以老其師,遂至于徒歸。而又以吾小弱而向強大,未嘗出于可勝之奇。蜀師每出,魏延常請萬兵趨他道以為奇。亮每拒之,而延深以憤惋。孔明之出者六,蓋嘗一用其奇矣。聲言由斜谷而遂攻祁山,以出魏人之不意。一旦而降其三郡,關輔大震。卒以失律自喪其師,奇之不可廢于兵也如此! 而孔明之不務此也,此銳于動眾而無其智以用之也。嗚呼! 非湯武之師,而惡夫出奇卒以喪敗其眾者,可屢為哉?雖然,孔明不可謂其非賢者也。要之黠數無方以當司馬仲達,則非敵故也。
范蠡之謂勾踐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范蠡自知其所長,而亦不強于其所短,是以能濟。孔明之于蜀,大夫種之任也。今以種、蠡之事,一身而二任之,此其所以不獲兩濟者也!
[鑒賞]
《何博士備論》,北宋武學博士何去非所著,何去非,字正通。生卒年不詳。浦城人(今福建浦城縣)。宋神宗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被任命為右班殿值武學教授博士。《何博士備論》是他評論從秦漢到五代興廢成敗、22個軍事人物用兵得失和戰略策略的書。紀曉嵐在《四庫總目提要》中稱它“其文雄快踔厲,風發泉涌”。全書共28篇,現存26篇。而在《歷代名賢確論》中,除現存26篇外,還有《論鄧禹》1篇。
《何博士備論》從歷史經驗與教訓中,總結戰略和戰術規律,研究一些重要人物業績,提出了一些發人深省的論斷。本書選錄了《六國論》、《秦論》、《楚漢論》、《晁錯論》、《漢武帝論》、《李陵論》、《蜀論》7篇,茲擇其要點,分述如下:
《六國論》中指出:從秦的實力與六國實力相比較看,秦的幅員為六國的六分之一,兵力為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而六國終于為秦所滅,那是因為六國分別為秦所各個擊破的緣故。這是“連橫”對“合縱”的勝利,是政治策略的勝利。因為有了這個政治策略的勝利,各個擊破六國的戰略方針,才得以順利實現。從這個觀點看來,何去非已明確地認識到“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和“政治策略決定戰略的成敗”的道理。從而全面地論述了秦滅六國與戰略的關系。所以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說:“蘇洵作《六國論》咎(譴責)六國之賂秦(即側重六國政治策略的錯誤);蘇轍作《六國論》咎四國之不救(即譴責齊楚燕趙不救韓魏的戰略錯誤)。去非所論,用蓋二意(即是把政略與戰略聯系起來研究。)”
《秦論》中指出: 當“天下交臂事秦”之時,秦軍東出而滅六國;“當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之時,章邯率秦軍東出而覆滅。問題不在于秦軍是否應該東出,也就是不在于戰略上攻、守是否得宜,而在于民心之得失。并進一步用西漢周亞夫率軍東出而平七國之亂來證明上述論點。他用這些歷史事實闡明了“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和“兵茍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的真理性。
《楚漢論》中,項羽之敗于劉邦,在于“漢高(劉邦)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則天下之智皆為其資”;項羽只憑血氣之勇,有人才而不能用,“知奪而不知有”,只知奪取地方,而不懂統治的方法,不會利用有利的形勢。以致愚昧無知地“捐關中天險之勢……反懷區區之故楚,而甚榮其歸”。從而指出:智謀必然戰勝愚勇。
《漢武帝論》中指出“兵有所用……有所不用。”以漢、匈和與戰的經過為例,說:“高帝滅秦楚,征不服,天下流血二十年。呂后、惠、文乘天下初定,與民休息。”對匈奴不惜忍辱和親而不肯用兵,是因為用兵條件尚不具備。到景帝時,雖有了用兵的條件,又逢七國之亂,也“姑持安天下之策”。至此,漢已經歷五世,他們都既不用兵,也未忘戰,并為此而積極準備。到武帝時,才“選徒習騎,擇命將帽,先發而倡誅之。行師十年,斬刈殆盡……刷四世之侵辱,遺后世之安強”。這是由于此時條件已經成熟了。所以,“古之人君,有忘戰而惡兵,其敝,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勢蹙于弱而不能振;有樂戰而窮兵,其敝,天下皆得以乘之,故其勢方于強而不知屈。然則兵之于入之國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矣”。關鍵是要看用兵的主客觀條件是否已經具備。這對北宋當時所處的情況,無疑有其可以借鑒的地方。
《李陵論》中指出:“李陵以步卒五千當敵騎十萬之從”雖然是“英勇悲壯”,但其結果還是全軍覆沒。認識到:“古之善戰者,計必勝而后戰”的重要。也就是我們現代所說的“不打無把握之仗”,反對“冒險主義和拼命主義”的意思。
《蜀論》認為諸葛亮對荊、益二州“得所以取之,失所以用之,至于遂亡荊州而勞用蜀民,功業亦已不就,良有以也”。其意思就是說,關羽攻襄陽,以至失荊州;諸葛亮六出祁山,都是“勞蜀之民”。總之,認為不應攻魏,對于孔明“聯吳抗魏”的戰略與策略,看來是不理解的。荊州之失,主要在于關羽,既不能聯吳,又疏于防吳;“蜀民之勞”,在于劉備執意伐吳,才有虎亭之敗,蜀國元氣大喪。這兩項都是劉、關破壞了孔明“聯吳抗魏”的策略所招來的失敗,文章作者卻把這些都算在孔明的帳上,歸咎于他,這是不公允的。至于“六出祁山”,已在荊州既失,夷陵慘敗之后,是“以攻代守”的策略,也就是戰略上的防御,戰術上的進攻。所以孔明拒絕出奇制勝,拒絕魏延建議。這一點也是文章作者所未能理解的。他對孔明的評論,歸根到底,就是說,不應攻魏,而應防守待機。須知防御也有積極防御(攻勢防御)與消極防御之別,這一點,看來文章作者和北宋士大夫們一樣,都卷入了消極防御的思潮中去了。這也可說是“時代烙印”吧!
此外,《晁錯論》指出:晁錯之愚,就在于既不能防“七國未發之禍”,反而促使七國加速叛亂,不知“上兵伐謀”的道理。繼之,又指出吳王濞不懂“兩面作戰必須集中力量擊破一方”的原則。《李廣論》指出軍紀的重要性。《霍去病論》提出:“善用兵者,不以法為守,而以法為用”,也就是說要靈活運用作戰原則,而不能死搬教條墨守成規。《魏論》從曹操用兵中,闡述了“兵以詐立”的原則。《司馬仲達(懿)論》和《陸機論》中,論述了封建時代君將矛盾。《鄧艾論》論述了“偷渡陰平”作戰中的創造性和冒險性。《吳論》從孫氏三世治吳,說明“因勢利導”,“量力而行”的重要。《晉論》指出分封宗室導致了八王之亂。《符堅論》指出符堅淝水之敗的原因是:戰爭既非正義的,戰略、戰術上,也違背了“以寡遇(敵)眾,其勢宣合(集中兵力);以眾遇寡,其勢宜分(分路前進)”的原則。把眾多的兵力集中在一點上,兵力既展不開,前后也不相屬,所以失敗。《宋武帝論》指出戰機之不可失。《唐論》指出方鎮擁兵自重,是唐代的亂源。《五代論》著重指出:“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獲暮失”,都是由于“強將驕兵”的迭相篡奪。
通觀《何博士備論》有三個主要特點:一是明確地對戰爭性質作了區分。認為不能籠統地肯定或否定戰爭,戰爭既“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重要的是要看是否合乎“德”,合乎“順逆之情”、“利害之事”。二是集中論述了戰略方面的問題。在中國古代軍事學術史上,戰略、戰役、戰術三種概念從來是不加分別的,統稱為“謀”、“略”、“計”或“智”,反映在兵學著作上更是如此。《何博士備論》卻不同,它除兩三篇講的是對戰爭的看法和治軍問題外,其作都是關于戰略方面的論述,近乎戰略專著的古代兵書,不僅在它問世之前是沒有的。三是寓事于理,論從史出。我國古代兵書,一般都是純理論性的著作。而《何博士備論》則把對戰略問題的觀點見諸于“歷代所以廢興成敗”的評論之上,融匯于重要軍事歷史人物用兵得失的探討之中,這種史論結合的論兵方法,是很獨特的。
《何博士備論》對研究我國古代戰略形成和發展有著一定的借鑒作用,對后人從戰略指導的實踐中去評價軍事歷史人物也有著良好的影響,它豐富了我國古代軍事理論的寶庫。日本人曾據該書的《浦城遺書》本進行重刊。歐洲一位名叫佛郎塞爾的學者還用英文翻譯出版了這部兵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