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春秋兵法·國語》原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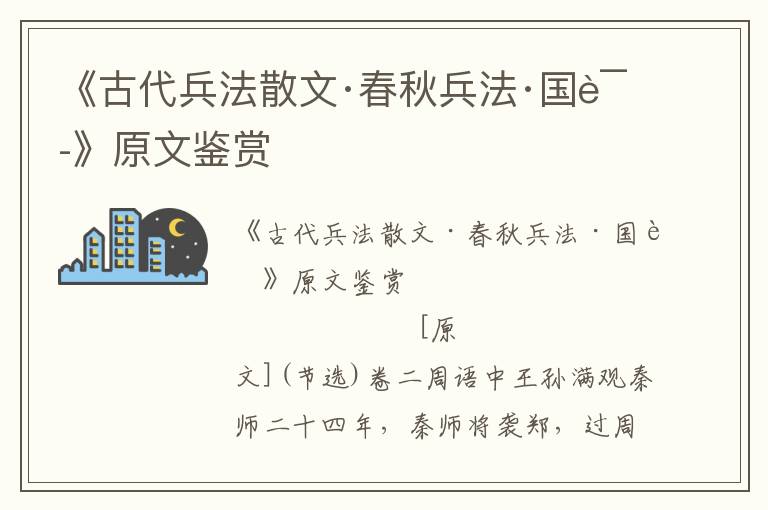
《古代兵法散文·春秋兵法·國語》原文鑒賞
[原文](節(jié)選)
卷二周語中
王孫滿觀秦師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皆免胄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
王孫滿觀之,言于王曰:“秦師必有謫。”王曰:“何故?”對(duì)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xiǎn)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謫,是道廢也。”
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崤,獲其三帥丙、術(shù)、視。
單襄公論郤至
晉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
明日,王叔子譽(yù)諸朝。郤至見邵桓公,與之語。邵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yù)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dǎo)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己實(shí)謀之,曰:“微我,晉不戰(zhàn)矣! 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qiáng)之。背宋之盟,一也;德薄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 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罪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 有辭,一也;得民,二也; 軍帥強(qiáng)御,三也; 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zhàn)。欒、范不欲,我則強(qiáng)之。戰(zhàn)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zhàn)也微謀,吾有三伐; 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 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 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
“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于四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
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 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圣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wǎng),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后庇焉,則能長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丑,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
“晉之克也,天有惡于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之功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奸仁為佻,奸禮為羞,奸勇為賊。夫戰(zhàn),盡敵為上;守和同,順義為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叛戰(zhàn)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叛國即仇,佻也。有三奸以求替其上,遠(yuǎn)于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
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
卷十晉語四
文公救宋敗楚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公率齊、秦伐曹、衛(wèi)以救宋。宋人使門尹班告急于晉,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告楚則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借之告楚。我分曹、衛(wèi)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wèi),必不許齊、秦。齊、秦不得其請(qǐng),必屬怨焉,然后用之,蔑不欲矣。”公說,是故以曹田、衛(wèi)田賜宋人。
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曰:“請(qǐng)復(fù)衛(wèi)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舅犯慍曰:“子玉無禮哉! 君取一,臣取二,必?fù)糁!毕容F曰:“子與之。我不許曹、衛(wèi)之請(qǐng),是不許釋宋也。宋眾無乃強(qiáng)乎! 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fù)曹、衛(wèi)以攜之,執(zhí)宛春以怒楚,既戰(zhàn)而后圖之。”公說,是故拘宛春于衛(wèi)。
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既陳,晉師退舍,軍吏請(qǐng)?jiān)唬骸耙跃艹迹枰病G页熇弦樱財(cái) :喂释?”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偃也聞之: 戰(zhàn)斗,直為壯,曲為老。未報(bào)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其眾莫不生氣,不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眾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zhàn),楚眾大敗。君子曰:“善以德勸。”
文公稱霸
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duì)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對(duì)曰:“民未知禮,盍大搜,備師尚禮以示之?”乃大搜于被廬,作三軍。使郤殺將中軍,以為大政,郤溱佐之。子犯曰:“可矣。”遂伐曹、衛(wèi),出谷戍,釋宋圍,賊楚師于城濮,于是乎遂伯。
卷十二晉語六
范文子不欲與楚戰(zhàn)
鄢之役,晉伐鄭;荊救之。大夫欲戰(zhàn),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后振武于外,是以內(nèi)和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nèi)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zhàn),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xì),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xì)無怨而大不過,而后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于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為政,必有內(nèi)憂。且唯圣人能無外患,又無內(nèi)憂,詎非圣人,必偏而后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荊與鄭以為外患乎?”
卷十五晉語九
晉陽之圍
晉陽之圍,張談曰:“先主為重器也。為國家之難也,盍姑無愛寶于諸侯乎?”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可。”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于先子,不德而賄。夫地也求飲吾欲,是養(yǎng)吾疾而干吾祿也。吾不與皆斃。”
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jǐn)浪酪允刂湔l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shí)。”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shí)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 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
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沉灶產(chǎn)蛙,民無叛意。
卷十八楚語下
藍(lán)尹亹論吳將斃
子西嘆于朝,藍(lán)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dú)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者,與哀殯喪圾,于是有嘆,其馀則否。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舊,無有嘆焉。今吾子臨政而嘆,何也?”子西曰:“闔廬能敗吾師。闔廬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嘆。”
對(duì)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于色,身不懷于安,朝夕勤志,恤民之贏,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jì)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tái)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差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卷十九吳語
勾踐滅吳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唱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日臣嘗卜于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贏于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huì),奪之利,無使夫悛。夫吳之邊鄙遠(yuǎn)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zhàn),必不須至之會(huì)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zhàn)。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huì)也已,吾用御兒臨之。吳王若慍而又戰(zhàn),奔遂可出。若不戰(zhàn)而結(jié)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若師,將伐吳。
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勾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qǐng)問戰(zhàn)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duì)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于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zhàn)者?”王曰:“在孤之側(cè)者,觴酒、豆肉、簟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bào)吳。愿以此戰(zhàn)。”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zhàn)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bào)吳。愿以此戰(zhàn)。”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zhàn)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bào)吳,愿以此戰(zhàn)。”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戰(zhàn)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與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馀,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bào)吳,愿以此戰(zhàn)。”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zhàn)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bào)吳。愿以此戰(zhàn)。”包胥曰:“善哉! 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zhàn)也。夫戰(zhàn),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眾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fā)大計(jì)。”越王曰:“諾。”
越王勾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于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zhàn)奚以而可?勾踐愿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后庸乃進(jìn)對(duì)曰:“審賞則可以戰(zhàn)乎?”王曰:“圣。”大夫苦成進(jìn)對(duì)曰:“審罰則可以戰(zhàn)乎?”王曰:“猛。”大夫種進(jìn)對(duì)曰:“審物則可以戰(zhàn)乎?”王曰:“辯。”大夫蠡進(jìn)對(duì)曰:“審備則可以戰(zhàn)乎?”王曰:“巧。”大夫皋如進(jìn)對(duì)曰:“審聲則可以戰(zhàn)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于國曰:“茍?jiān)谌终撸栽煊趪T之外。”王乃命于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
卷二十一越語下
范蠡論戰(zhàn)
至于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對(duì)曰:“微君王之言,臣故將謁之。臣聞從時(shí)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于五湖。
吳人聞之,出而挑戰(zhàn),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jìn)諫曰:“夫謀之廓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shí)無怠,時(shí)不再來, 天予不取,反為之災(zāi)。贏縮轉(zhuǎn)化,后將悔之。天節(jié)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
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shí)以為紀(jì),無過天極,究數(shù)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 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后則用陰,先則用陽; 近則用柔,遠(yuǎn)則用剛。后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強(qiáng)以御,陽節(jié)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zāi),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jié),盈吾陰節(jié),而奪之利。宜為人客,剛強(qiáng)而力疾; 陽節(jié)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jié)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shè)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強(qiáng)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zhàn)。
[鑒賞]
《國語》,是我國最早的國別體史書,也是我國早期史學(xué)專著之一。它與《左傳》思想傾向相近,所載史料可以相互參證,《左傳》詳于記事,《國語》詳于記言,所以,前人有把《左傳》稱為《春秋內(nèi)傳》,《國語》稱為《春秋外傳》之說。
《國語》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漢書.藝文志》著錄于《六藝略》的春秋類,注明是與孔子同時(shí)的左丘明所作。后代研究者多以為是戰(zhàn)國初年人匯編各國史料而成。《中國古代史》(1979年南開大學(xué)歷史系編)則根據(jù)《國語》中《晉語》所占的篇幅較多,推說可能是戰(zhàn)國時(shí)三晉人所寫。這里,我們就不多探討,且依舊說。
《國語》系統(tǒng)清晰地反映了上起西周穆王(約公元前10世紀(jì)),下至東周貞定王(公元前468—前441年)間500余年的歷史,它既記載著當(dāng)時(shí)各國的重要事件,也載有一些瑣碎之事。該書語言豐富,表述靈巧,對(duì)后世奏議、言行錄等書籍的編纂有著較大的影響。
《國語》的體例,以國分類,每國以事為篇。以年代為先后,共8類(國)、20卷,約11萬余字,共記載著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的242件事件,每一件事的記載又可單獨(dú)成篇,其中《周語》3卷,記載著“祭公諫征犬戎,邵公諫厲王止謗,王孫滿觀秦師、單襄公論郤至”等33件周國之事;《魯語》2卷,記載著“曹劌問戰(zhàn)、里革論君過,諸侯伐秦、襄公如楚”等37件魯國之事;《齊語》1卷,記載著“管仲對(duì)齊桓公、桓公為政、管仲論足甲兵,諸侯歸桓公”等7件齊國之事;《晉論》多達(dá)9卷,記載著:“武公代翼、驪姬譖雜太子申生、秦晉之戰(zhàn)、重耳適齊、文公救宋敗楚,文公稱霸、趙宣子請(qǐng)師、范文子不欲與楚戰(zhàn)、祁奚薦賢、平公天欒民、叔向斷獄、晉陽之圍”等127件晉國之事;《鄭語》1卷,僅記載著:“史伯論興衰,平王之末”兩件事;《楚語》有2卷,記載:“申叔時(shí)論傅太子、白公子張諷靈王納諫、觀射父論施地天道、藍(lán)尹亹論將將斃”等18件楚國之事;《吳論》1卷,述“諸稽郢行成于吳,夫差伐齊,勾踐襲吳,勾踐滅吳“9件吳國之事。《越語》也分上下2卷,記載勾踐雪恥、范蠡論持盈定傾節(jié)事、范蠡論戰(zhàn)、范蠡鋅越王等9件越國之事。
《國語》作為以言記為主的史書,故然要涉及到軍事史料。本書選錄的有關(guān)軍事方面的論述,基本上能體現(xiàn)《國語》的軍事思想,現(xiàn)約略介紹如下:
一、實(shí)現(xiàn)了軍事行動(dòng)指導(dǎo)原則由“義、信、禮”到“智、勇、仁”的更新
西周自昭王時(shí),“由于王道微缺”,原來接受周封號(hào)的楚國率先不服,昭王為率六師南征,卒于江上,西周自此日趨衰敗,周穆王以后政治上進(jìn)一步“衰微”,各諸侯逐步與其疏遠(yuǎn),停止向西周朝觀,乃至“諸侯或叛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之后,歷史上雖稱之為東周,而實(shí)際上東周這個(gè)“共主”已是徒具虛名了。故歷史也稱東周前期(公元前700年-前475年)為春秋,東周后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為戰(zhàn)國時(shí)期。盡管如此,直至戰(zhàn)國時(shí)期,各諸侯國仍然要打著“天子”的旗幟,實(shí)行”“挾天子以令諸侯,天下莫敢不聽”的策略,意識(shí)形態(tài)方面基本上實(shí)行從西周沿襲下來的宗法等級(jí)制度等等。故然軍事行動(dòng)的指導(dǎo)原則在春秋初期也不能超出人們當(dāng)時(shí)的思想水平。《國語》在記載公元前600年前后軍事言論中,圍繞以“禮”為中心,提出了“義、信、禮”的軍事指導(dǎo)原則。公元前636年,子犯與晉文公言談時(shí),子犯勸文公要把握“義、信、禮”的原則,這里的義指是非大義,與人民對(duì)戰(zhàn)爭性質(zhì)的了解有關(guān);信指言必信、行必果,與人民對(duì)軍紀(jì)的遵守有關(guān);禮指上下尊卑的關(guān)系,與人民對(duì)上級(jí)的服從有關(guān)。公元前627年王孫滿觀秦師時(shí),以為秦師(諸侯國軍隊(duì))過周(天子之國)北門,戰(zhàn)士不下車表示敬意則為無“禮”;便想起了“原則”說:“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xiǎn)而脫,能無敗乎?”可見,當(dāng)時(shí)“禮”十分重要。到了公元前575年周單襄公評(píng)價(jià)剛戰(zhàn)敗楚國而到周國表功的晉臣郤至?xí)r,對(duì)“禮”的看法就存在分歧了。郤至說:“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單襄公則認(rèn)為:“奉義順則謂之禮”,指出戰(zhàn)斗中避讓縱敵的所謂“禮”和“仁”是錯(cuò)誤的,作戰(zhàn)的直接目的當(dāng)然是“盡敵為上”。
商鞅曾經(jīng)說過:“世事變而行道異”。隨著戰(zhàn)爭觀念的演變,到了春秋末年和戰(zhàn)國時(shí)代,軍事行動(dòng)的指導(dǎo)原則把以往的“禮”拋之九霄了、郤至的“仁”無人效法都注以新的內(nèi)涵了。楚大夫申胥與越王勾踐(公元前497—465年)論戰(zhàn)時(shí),申胥站在理論高度指出,把握軍事行動(dòng)的指導(dǎo)原則應(yīng)為“智、仁、勇”。“智”是軍事統(tǒng)帥高瞻遠(yuǎn)矚,深謀遠(yuǎn)慮,“勇”是要審時(shí)度勢(shì)、當(dāng)機(jī)立斷,“仁”包含的內(nèi)容就多了,包括采取一切措施爭取國內(nèi)人民的親附支持,采取正確的外交政策,爭取“國際”的同情等等。“智、仁、勇”這一原則的提出,不僅為當(dāng)時(shí)的越國起到了較大的作用,而且對(duì)后世也有相當(dāng)?shù)挠绊憽?br>
二、提出“爭者,事之末也”的軍事策略
春秋戰(zhàn)國時(shí)期,雖然是一個(gè)“戰(zhàn)亂多端”的年代,但是,人們通過對(duì)戰(zhàn)爭的實(shí)踐、認(rèn)識(shí)、再實(shí)踐、再認(rèn)識(shí),悟出戰(zhàn)爭這部“機(jī)器”不是隨便起動(dòng)的,一有不慎就會(huì)作繭自縛。越大夫范蠡于公無前495年,力勸越王勾踐不要輕舉伐吳時(shí)說:“夫勇者,德也,兵者,兇器也,爭也,事之米也。陰謀德、好用兇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勇敢,是一種德;兵器,是不詳?shù)墓ぞ?爭斗,是處理問題最后的手段。如果暗中算計(jì)動(dòng)武,一味偏好兇器,開始加之于人的,到頭來落在自己身上。)這一觀點(diǎn)與公元前496—453年間成書的《孫子》所說的:“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相一致。戰(zhàn)爭必慎的觀點(diǎn)在《國語》中提出當(dāng)然還有比這更早的。公元前575年晉中軍副帥范文子就提出了“戰(zhàn),刑也”的觀點(diǎn),認(rèn)為戰(zhàn)爭是一種刑罰,用兵亦如用刑,不可濫用,必須具備了充分的條件方可進(jìn)行。
三、指出了“親附人民”是進(jìn)行戰(zhàn)爭的根基
《國語》中雖不乏其“天命思想”的言表。但與殷周時(shí)期比較起來,“天命思想”要淡薄得多了。因?yàn)槿酥鸩揭庾R(shí)到純系子虛烏有的“神”,“上天”對(duì)戰(zhàn)爭的勝利幫不了多少忙,而傳統(tǒng)文化,宗教又非常敬畏“上天”與“神靈”,善于辯說的魯人曹劌于公元前684年給魯莊公巧妙地說:“民和而后神降之福”。這就是說,“民和”不僅能使敵人懼怕,連“神靈”也會(huì)受感動(dòng),而降福于他。這樣還愁霸業(yè)不成!如何才能做到“民和”呢?就是要懂得親附人民。《國語》就如何親附人民談了當(dāng)時(shí)的許多具體辦法,如《范蠡論用兵》中,越王勾踐談?dòng)H附人民的四條措施就非常具體,極得人心。即使是戰(zhàn)爭過程中,情況萬分危急的情況下,也不乏頭腦清醒之人,如公元前455年趙襄子遭晉、韓、魏聯(lián)軍的進(jìn)攻,面臨外無援助,內(nèi)難尋覓退守之處的困境中,有人勸他退守條件較好的長子和邯鄲。他卻說,長子雖距離較近,而且城墻厚實(shí)完整,但它是民眾精疲力竭修筑起來的,如果我現(xiàn)在跑去,要民眾舍死忘德去守衛(wèi)它,誰還能幫我出力呢?邯鄲雖倉糧很充實(shí),可以久守,但那是榨取民脂民膏才充實(shí)起來的,如果又因?yàn)槲业搅四抢锒顾麄兪艿竭M(jìn)攻和傷害,誰又能幫我出力呢?后來他決定退到先主尹鐸曾實(shí)行過寬仁政治的晉陽。趙襄子率部退避于群眾基礎(chǔ)好的晉陽,果然不錯(cuò),晉陽被敵軍決水灌城,連爐灶都淹在水里變成了青蛙出沒的地方了,人民卻毫無背叛趙襄子的意思。
四、提煉了“盡其陽節(jié),盈吾陰節(jié)而奪之”等一系列戰(zhàn)術(shù)原則
《國語》雖然不是一部軍事專著,但除以上的重大軍事方略之外,也有不少的具體戰(zhàn)術(shù)原則。如勾踐與后庸、苦成、文種、范蠡、皋如五位大夫論戰(zhàn)時(shí),就談到了賞罰嚴(yán)明、指揮靈活、熟悉使用兵器、熟悉金鼓、旌旗、號(hào)令的規(guī)定,能迅速完善地構(gòu)筑陣地工事等等。更值得一提的是《國語》的攻防戰(zhàn)術(shù)理論具有較高的層次。如范蠡論用兵時(shí)就提出了:后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yuǎn)則用剛……盡其陽節(jié),盈吾陰節(jié)而奪之”的戰(zhàn)術(shù)原則。比其孫子的“避其銳氣、擊其墮歸”要具體得多。所以《國語》也不愧為我國的一部古代兵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