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yú)、人和精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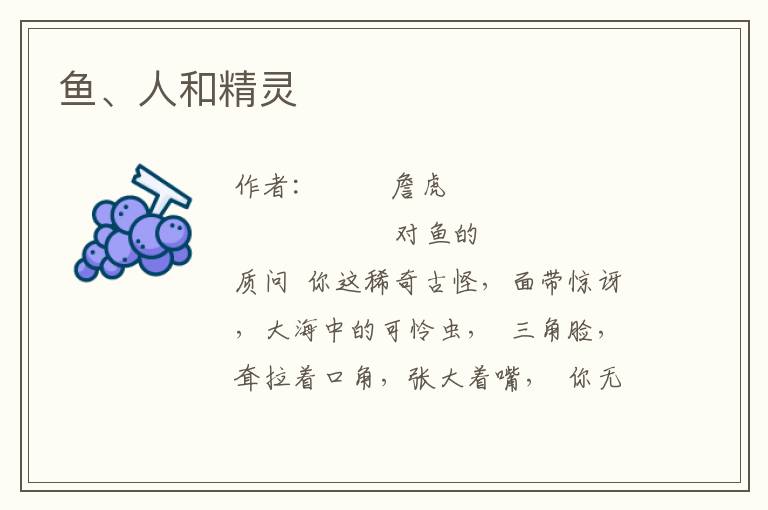
作者: 詹虎
對(duì)魚(yú)的質(zhì)問(wèn)
你這稀奇古怪,面帶驚訝,大海中的可憐蟲(chóng),
三角臉,耷拉著口角,張大著嘴,
你無(wú)止無(wú)休地吞進(jìn)大海中的鹽水;
你冷血,雖然你的血有幸被染成鮮紅,
你沉默,雖然你長(zhǎng)住在咆哮的浪濤中。
你呀,不管什么形狀,總是免不了魚(yú)性,
有的圓,有的扁,有的細(xì)長(zhǎng),都象鬼怪,
沒(méi)有腿,不懂得愛(ài),聲名狼藉地清清白白。
啊!又濕又滑又敏捷,瞪著大眼的鱗介之輩,
癡呆的凸眼兒,你在干些什么?怎樣生活?
那些卑賤乏味的日日夜夜,你是怎樣度過(guò)?
禮拜天你怎樣消磨?莫不是搖晃著肥大身軀,
整日價(jià)不停地沖洗?瞠目咧嘴,咬呀,喝呀!
莫非只有你受驚時(shí)潑刺一躍才算有點(diǎn)變化?
魚(yú)的回答
奇異的怪物,自從第一次看見(jiàn)你,
天知道,為什么我的同類就目不轉(zhuǎn)晴,
永遠(yuǎn)凝視?啊!扁平的、丑惡不堪的面孔,
陰森森地和下面的胸膛截然分離。
你總是在旱地上陰沉地走來(lái)走去,
岔開(kāi)身軀,邁著荒謬可笑的步子,
一叉又一叉,辱沒(méi)了一切優(yōu)美的風(fēng)韻,
你那廢置無(wú)用的長(zhǎng)鰭——毛茸茸,直挺挺,干巴巴,好不遲鈍!
你成天吸進(jìn)那刀劍似的、不堪呼吸的空氣,
你怎能生存下去?你這干癟的、抑郁的懶漢,
你在怎樣打發(fā)時(shí)光?既然那惟一可祝福的生活,
在白浪碧波的水中生活,你絲毫也不能分享?
有時(shí)我看見(jiàn)你們成雙成對(duì)走過(guò)海灘,
你的鰭挽著她的鰭,多難看,多不體面!
(魚(yú)變成了人,再變成精,接著說(shuō)道:)
如果你還在笑,請(qǐng)盡情地笑出你的嘲弄,
人啊!你可以恨這恨那,但總要有幾分真情。
萬(wàn)千品類必須在差異中證明各自的功用,
只有萬(wàn)籟齊鳴,寰宇才能充滿美妙的樂(lè)聲。
現(xiàn)在我也是一個(gè)精靈,可以隨心所欲,
寄身于眾生之列,不管是魚(yú)、鴿子、還是蒼鷹。
沒(méi)有憎恨,沒(méi)有驕傲,不在眾生之下,也不在眾生之上,
我只是一名過(guò)客,在造物主精心安排的輪回之中。
人的生命是溫暖的,有喜有悲,徘徊在恩愛(ài)與墳?zāi)怪g,
無(wú)窮無(wú)盡的希望,經(jīng)受了嚴(yán)峻的苦難而感到光榮,
兩眼望著蒼穹,渴望長(zhǎng)出天使的翅膀遨游太空。
魚(yú)啊!它動(dòng)作敏捷,需求甚少,朦朧而又清晰,
在滾滾的浪濤里,一個(gè)冷清、甘美、銀色的生命,
因?yàn)闀r(shí)常接觸到激蕩全身的恐懼而變得敏感靈通。
(黃宏煦譯)
(英國(guó))利·亨特
亨特在中學(xué)時(shí)代就與詩(shī)神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他與其兄約翰·亨特創(chuàng)辦過(guò)周刊《檢察者》,由于批評(píng)了未來(lái)的國(guó)王喬治二世,亨特兄弟被捕入獄,監(jiān)禁了兩年。二人在獄中仍繼續(xù)編輯、出版《檢察者》。1821年,應(yīng)著名詩(shī)人雪萊的邀請(qǐng),利·亨特?cái)y帶著妻子兒女赴意大利,幫助編輯雪萊和拜倫主辦的刊物《自由者》。然事有不測(cè),就在他們到達(dá)一周后,雪萊不幸于海中溺死,亨特于是前往希臘,不久返回英國(guó)。亨特有長(zhǎng)詩(shī)《里米尼的故事》,抒情短詩(shī)《阿布·本·阿德罕姆》和《珍妮吻了我》等,膾炙人口,流傳甚廣。
《魚(yú)、人和精靈》一詩(shī)帶有極強(qiáng)的哲理性,可以理解為詩(shī)人在探索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詩(shī)人選擇了“魚(yú)”作為與人并存而對(duì)立的形象。在希臘文字中,“耶穌基督、上帝之子、救世主”每個(gè)詞的第一個(gè)字母加起來(lái)是個(gè)“魚(yú)”字,魚(yú)就成為虔誠(chéng)和神圣的象征。此外,魚(yú)又是繁殖力最強(qiáng)的一種生物,因而古往今來(lái)詩(shī)歌中的魚(yú),常常作為情欲、配偶的象征。
然而亨特詩(shī)中的魚(yú)似乎沒(méi)有神圣的光環(huán),人對(duì)魚(yú)也似乎不大虔誠(chéng)恭敬,“有的圓、有的扁,有的細(xì)長(zhǎng),都象鬼怪,沒(méi)有腿,不懂得愛(ài),聲名狼藉地清清白白。”人們認(rèn)為魚(yú)在水中的生活是卑賤乏味的,“只有你受驚時(shí)潑剌一躍才算有點(diǎn)變化”。
魚(yú)對(duì)人的形態(tài)和生活反唇相譏,“扁平的、丑惡不堪的面孔,陰森森地和下面的胸膛截然分離。”尤其是對(duì)男女之間的情愛(ài)感到不可理解:“有時(shí)我看見(jiàn)你們成雙成對(duì)走過(guò)海灘,你的鰭挽著她的鰭,多難看,多不體面!”
魚(yú)變成了人,再變成了精靈,超然于二者之外,才悟出了生活的真締,“萬(wàn)千品類必須在差異中證明各自的功用,只有萬(wàn)籟齊鳴,寰宇才能充滿美妙的樂(lè)聲。”宇宙間的生靈都處于造物主精心安排的輪回之中,在自然法則之中皆為勿勿過(guò)客,人不必以自己的習(xí)性強(qiáng)求于魚(yú),魚(yú)也不必以自己的習(xí)性強(qiáng)求于人。人“有喜有悲”,經(jīng)歷苦難而不失希望,魚(yú)“朦朧而清晰”,接觸恐懼而敏感自通,又何必相互嘲笑呢?“與其譽(yù)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莊子·大宗師》)魚(yú)變成了精,就理解了人,人雖不是魚(yú),也可理解魚(yú)的樂(lè)趣。
全詩(shī)一問(wèn)一答,層層推進(jìn),結(jié)構(gòu)勻稱、寓理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