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雨青《一張發黃的照片》散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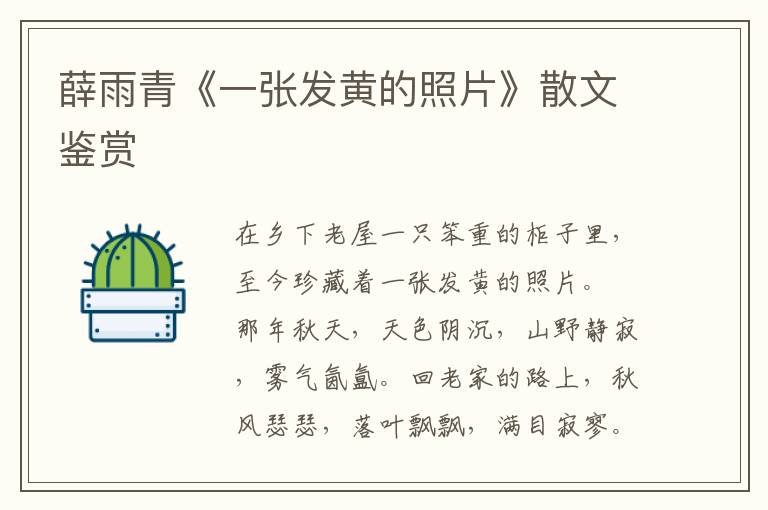
在鄉下老屋一只笨重的柜子里,至今珍藏著一張發黃的照片。
那年秋天,天色陰沉,山野靜寂,霧氣氤氳。回老家的路上,秋風瑟瑟,落葉飄飄,滿目寂寥。車子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行駛,一路顛簸,下午時分到了老家。
回到家里,院子里靜悄悄的,只有母親一人坐在廊檐下做針線活,身旁靜靜地臥著那只小花貓,瞇縫著一雙眼睛,懶洋洋的一動也不動。聽母親說,父親去山上干活了,還沒回來。
此時,家里只有母親和我兩人。我們嘮著家常,敘說著村中一些陳年舊事。嘮著嘮著,母親好像記起了什么,放下手中的針線,從老屋里間的柜子里摸摸索索拿出一個里三層外三層的小紙包,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張發黃的照片。
打開紙包,母親嘮叨著說,照片上,那個年輕的農婦是她,懷里抱的那個梳著羊角小辮大約一歲的小女孩,是我的表妹——大舅的女兒,身旁站著的一個留有小平頭約莫三歲的小男孩,是兒時的我。
瞅著模糊的老照片,戴著老花鏡的母親眼圈就紅了。在一聲聲嘆息里,她指著照片上的小女孩,對我說:“要是你這個妹妹還在,現在大概也40多歲了。”停了停,母親又對我說:“要是有一天我不在了,就再也沒有人告訴你這個秘密了。”
此時,天空突然響起了一群鳥雀的悲鳴,聲音非常凄厲。一遍又一遍瞅著照片的母親已是老淚縱橫,泣不成聲。而我,更是心如刀絞,猶如萬箭穿心。我不知怎樣才能安慰自己和母親。我不知道怎樣做,才能讓母親好受一點。
依稀記得,我兩歲時秋天的一個下雨的日子,淋著雨的大舅,懷里抱著個小女孩,背個補丁摞補丁的黃背包,手里拿著個臟兮兮的舊奶瓶來到了我家。小女孩穿著一件破舊的小花衣,凍得瑟瑟發抖。我可憐的大舅,邋里邋遢,目光呆滯,霜打的茄子一樣。母親從大舅懷里接過了小女孩,一邊擦著眼淚,一邊把臉緊緊地貼著那孩子的臉蛋。父親嘆息著,給凄凄惶惶滿臉無助的大舅,裝了一鍋旱煙。過了好一會兒,被煙嗆著的大舅,雙手抖抖索索地把奶瓶和半袋奶粉交給了母親,親了親小女孩粉紅的臉蛋,狠了狠心,哽咽著對母親說:“我走了,孩子往后就托付給你了。”然后消失在茫茫雨霧里……
據說,勤勞善良的大舅母,年紀輕輕不幸得了重病撒手人寰,留下一兒一女,兄妹倆相差只一歲。當時,處世不深的大舅,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只好將兒子留給了外婆,女兒托付給了我母親撫養,那是怎樣的撕心裂肺啊!
大舅一夜間白了頭發,外婆從此一病不起。那個年代,物質匱乏,人們生活貧窮,缺衣少穿。備受打擊的大舅,時不時來到我家,拿點奶粉、零花錢,給我的母親。每次來,他都遠遠地瞅著小女孩,眼里全是愛戀,讓孩子叫他舅舅。時間一長,小女孩習慣了叫他“豆豆”(舅舅)。
此后,我家多了一個孩子,鄰居們分外同情,有的老遠看見小女孩,偷偷淌著眼淚,給她一些好吃的。那個小女孩是我的表妹。我走哪兒,她就跟哪兒。母親說,她就是我的尾巴。她發音不準,每次都把哥哥叫成了“的的”。
第二年的冬天,大舅趕著一頭瘦驢,接母親去外婆家。我和表妹一同跟了去。見到打著響鼻的驢子,淘氣的表妹既恐懼又興奮,一路大呼小叫,說個不停。在外婆家小住了幾天,好端端的表妹突然發起了高燒。村醫來外婆家天天打針吊水,但表妹的神情一天不如一天。她兩眼無神,氣息奄奄,再也叫不出“的的”(哥哥)了。
那是一個北風呼嘯、寒冷異常的夜晚,我在熱炕上睡得稀里糊涂。半夜時分,突然,外婆家院子里一片哭聲,非常凄慘,我隱約感到發生了什么不幸。一會兒,院子里好像來了好多人,有鐵锨、镢頭的碰撞聲,男人們的吵鬧聲。還有母親、外婆、二舅母、三舅母呼天搶地的哭吼聲,大舅老牛一樣的嚎啕聲。后來我迷迷糊糊睡著了,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早晨,外婆家一片寂靜。沒有說話聲,也沒有人做早飯,大人們神情凄慘。小腳的外婆,步履蹣跚,如同冬天的一片枯葉,飄在了上房的炕上,再也沒有起來。母親紅腫著雙眼,披頭散發,完全沒有了人樣。從大人的表情上,我已想到了可能發生的不幸。我瘋了般,滿院滿屋、滿坡滿山尋找著表妹,但哪有她的影子?我哭著喊著要我的表妹,山風發出陣陣嘆息,鳥雀發出聲聲悲鳴,但哪里又有我的表妹……
看著哭得已沒有氣力的我,留著山羊胡子的外公,一把將我抱在了他的懷里。他眼中一顆渾濁的老淚,猛地砸到了我的頭上。經歷了太多世事滄桑和苦難的外公,給我揩了揩眼淚,摸著我的頭說:女女(表妹的乳名)昨晚去了你山里的大姨家,過幾天就回來了……那一夜,表妹就永遠永遠地走了,生命定格在了兩歲半的日子里。我多么希望上天能夠垂憐,讓我能看到表妹的身影……
好多年又好多年過去了,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了。親人們似乎忘記了過去,或許再也沒有人愿意提及,只有母親珍藏著那張照片,我知道這是母親此生永遠抹不去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