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明《家鄉入夢》散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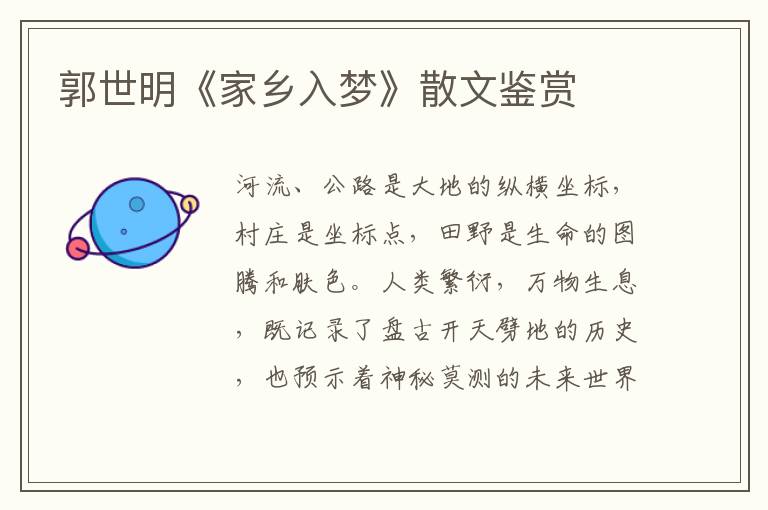
河流、公路是大地的縱橫坐標,村莊是坐標點,田野是生命的圖騰和膚色。人類繁衍,萬物生息,既記錄了盤古開天劈地的歷史,也預示著神秘莫測的未來世界。
沛縣是古城,千年古城。張柳莊是村莊,千年穿越。村莊和古城唇齒相依,相得益彰。村莊位于古城西北10公里,沛鴛公路、龍口河穿境而過。這里古稱千秋鄉,今屬朱寨鎮。
過去,這里是著名的黃泛區。住在這一帶的村民,從宋元時期,就開始頻頻遭遇黃河水患侵襲。當時,黃河決溢入泗水入淮河漸趨頻繁,北宋一百六十多年間,決溢入泗水入淮達10次。僅元朝末年,水、旱災八次,造成“湮沒田廬無算,死亡百姓無數,村莊城邑多成荒墟……”這里的村民歷經磨難,多災多難。
張柳莊莊名的由來很是奇怪。如今這個村莊有著2000多人口,張姓很少,只有三家,卻沒有一家姓柳的。據老人們說,張柳莊村名還確實有一段緣于張姓人家的傳說。
元朝末年,有一次黃水退后,家園早已又黃沙遍野,寸草不生。一張姓老人攜妻帶子居無定所,四處流浪。后來選擇在地勢較高的一棵大柳樹旁搭建了一所臨時草庵棲身。再后來柳樹周圍居住的人漸漸多了,便形成了村落,后人習慣稱張柳莊。雖然村莊陸續來了郭姓、趙姓、燕姓等其他族姓,且他們族姓人口繁衍較快,但村莊的名字卻世代流傳了下來。不過不熟悉這段經歷的外鄉人仍有時會把張柳莊說(寫)成張劉莊(其實村里沒有一家姓劉的。現在鹿樓鎮還倒有一個叫“張劉莊”的村子)。
老人們說,村莊西頭有一條縱貫南北的龍口河,洪水泛濫沖擊而成。就是這條連接著大沙河向北注入微山湖的河流養育了這里的一代又一代村民。即使天氣酷熱,干旱少雨,這條河也很少干涸過。勤勞的村民在河流的兩岸種上了樹木,耕種了莊稼。村民們用這條河里的水灌溉了莊稼,收獲了希冀,養活了子孫后代。當然,這里也曾是我們孩提時代的樂園。河寬大約三十米,河深處兩三米不等。河水清澈透明,魚蝦可見,陽光下,波光粼粼、流光溢彩。夏日洗澡,冬季滑冰;蘆葦蕩撿拾鳥蛋,水草叢逮魚摸蝦;捉迷藏,打水仗,其樂融融;柳樹跳水,河里沖浪,其樂無窮。在這里,度過了我無憂無慮的童年快樂時光。
村西曾經有一片張家的沙果樹(花紅樹)園。春天時節,一望無際的沙果樹,競相開放,吐蕊斗艷,遠觀如銀似雪,近看潔白如玉,素淡怡人,香氣襲人,給人以圣潔之美。沙果樹虬枝盤旋,低矮觸底,利于攀爬。秋冬季節,這里一度成了我們逃學玩耍、樹上捉迷藏的好去處。直到被張家女主人追趕了幾次后我們再不敢前往了。只是這片曾留有我美好童年記憶的沙果樹園不知道什么時候竟變成了一排排居民住房了。
村中間的郭家杏林從南到北,連成一片。杏花含苞時純紅色,綻放時粉紅色,花落時純白色,如紗,似夢,變幻迷離,如在仙境。杏花馥郁馨香,沁人心脾。杏花凋謝,點點青杏高掛枝頭。微風輕拂,杏葉下顆顆青杏忽隱忽現,蕩秋千似的,煞是惹人。杏子成熟季節,遠遠望去,滿樹鵝黃色的,金黃色的,令人垂涎欲滴。當然,總有幾個調皮的頑童會冒著被杏樹主人的驅趕、捉到的危險偷偷爬上樹,或騎著樹杈,或攀著高枝,飽享一頓美餐。
村莊的中間有一口老井。八十多歲的父親也記不清井是什么時候挖的。井口青石圍繞,高出地面20公分,從井口望下去,井深七、八米。白天能清晰地看到水面上的天空、人、樹的倒影和坑坑洼洼的井壁上斑駁的綠苔,晚上還能看到閃爍的星星和皎潔的月亮。井沿邊的青石被提水的麻繩勒出了一道道槽痕,也磨出了一段段塵封的歲月故事。經歷近百年風霜雪雨洗禮的老井,如同家鄉的老屋、老人一樣,永遠不會在我心里消失。
過去,農村娛樂方式很少,每年農閑時,總會有一連幾天的揚琴戲在老井北邊空曠處開演。這幾天是村里最熱鬧最奢侈最幸福的時候。太陽還沒有落山,小孩子們早早就來到老井旁搶占好的地盤。長條凳或者小板凳放好了,就在老井旁邊玩游戲,或焦急地等著父母和說書人的到來。孩子聽書不像大人們那么入迷,總是圖個熱鬧。開戲不久,孩子們上下眼皮打架是常有的事。每到散場,孩子們總會被父親背著或閉著眼睛牽著母親的手踉踉蹌蹌地跟著走回家。但記憶中的《岳飛傳》《楊家將》《薛仁貴征東》等歷史故事,都是我們在那個時候聽到的。
聽戲是大人們的享受,看電影卻是我們孩子們的最愛了。還記得小時候,也就是七十年代末,到大隊部放映的露天電影伴隨著我們快樂成長了好多年。只要一聽大隊喇叭筒說“今晚有電影”,我們小伙伴們就歡呼雀躍,或呼朋喚友,或扛著長板凳爭先恐后奔向大隊部搶占“有利地形”。戰斗片是我們最喜愛的,后來《少林寺》播出后,我們還一度愛上了武打片。當時,紀錄片、科教片在我們孩子眼里都是廣告片、加映片,很少能安靜地看或看完,當放映加映片時,我們要么在放映場打鬧追逐一番,要么安靜地躺在父母的懷抱里等著看正片電影。有時聽說幾里外的村莊有電影放映,即使月高夜黑,也全然不顧,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也必定會約上幾個小伙伴一塊兒去看。如果信息不準確,那里沒有放映電影,我們也不會垂頭喪氣,也會開心地說著“我們看了一場小英雄白跑路”。四十多年過去了,但那些耳熟能詳的《地道戰》《地雷戰》《鐵道游擊隊》《喜盈門》《少林寺》等經典影片,記憶猶新,恍若昨日,像母親的愛撫,氤氳在我的記憶里,又像一壇塵封的老酒,醇香綿長,揮之不去。
八十年代初期,電視機是個稀罕物件,黑白電視機幾個莊能有一臺就不錯了。年輕人的嫁妝主要是“三轉一響”,即自行車、手表、縫紉機和收音機,沒有電視機。尋常百姓人家根本沒有購買電視機的奢望和資本。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們村才有幾戶生活比較富裕的人家陸陸續續買上了黑白電視機。父母為了培養我和弟弟上大學,家里一直沒能買得起電視機,直到九二年,我結婚時,家里才有了一臺黑白電視機,還是作為妻子的嫁妝從娘家帶來的。八十年代末,盡管黑白電視機普及較快,但一個村能有一兩臺彩色電視機也簡直是天方夜譚。經濟條件稍好一點的陳紹華家、郭永軍家八十年代末最先買了彩色電視機。去他們兩家看彩色電視一度成了全村老少不少人每晚必不可少的節目。《霍元甲》《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西游記》《紅樓夢》《渴望》等電視劇,是那時陪伴我們成長的精神食糧和文化大餐。
記憶中的張柳莊村,民風淳樸厚道,熱情好客。村子里,無論是老人還是小孩,對人都非常熱情。如果有異鄉人進村,不管走到哪戶村民的家門口,他們都非常主動地和異鄉人打招呼。經常會問你從哪里來,到誰家里去,吃飯了沒有之類的客氣話,并且還會把你送到想去的人家……這里的人們經常滿臉掛著笑容,這笑容是發自內心的,是最真誠、最純潔、最樸實的。
村子西北角有一所遠近聞名的小學——千秋鄉小學。千秋鄉小學建于1920年,她的前身是由鄉賢燕振聲1910年創建的新式教育教學方法、傳播新思想的懷遠初等小學。懷遠初等小學1949年改稱張柳莊小學。2008年學校異地重建新校區,改名為朱寨中心小學至今。時千秋鄉小學順應時代發展,重教國文,強調“立品”,設有修身、國文、算術等后逐漸增設體育、衛生、勞動、歷史、地理等課目,將傳統國學教育和現代新式教育相結合,把新的教學內容、新的教育思想、新的教育教學方法引進學校。先進的教育理念和嚴格的教育管理,吸引了千秋鄉方圓幾十里的農家子弟前來就讀。時千秋鄉小學是沛西地區第一個黨的支部誕生地,與素有“江南燕子磯,江北青墩寺”之稱的城南青墩寺小學齊名,聲名遠播大江南北。李公儉等共產黨員相繼在千秋鄉小學任教,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傳播革命火種,培養了郝中士、張世珠、葛步海等一大批革命人才,千秋鄉小學成為當時沛西革命活動中心和學校教育高地。
張柳莊的村民們用自己勤勞的雙手創造著豐富的物質文化財富。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彩電手機互聯網自不必說,今天的張柳莊,更是人才濟濟,名人輩出,發展變化,日新月異。
郭姓、趙姓、燕姓、陳家等人家人丁興旺,人口占全村的四分之三有余。各行各業,各姓氏都是人才輩出,有的人做了燕局長,有的人做了趙校長,有的人做了李行長,有的人做了卞礦長……閆姓年輕人受父輩影響,技工型人才較多,建筑、裝潢多有絕技。總之,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狀元,村里各姓氏都有人成為家族的驕傲。值得一提的是郭氏家族,自元末遷入以來,人丁興旺,人口繁衍較快,目前郭氏人口占村莊人口的四分之一多。郭氏家族比較重視教育,現在平均每戶就出過一名以上大學生。這些大學生們大學畢業后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大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績。
日月輪回,四季交替,變化的是四季景色,不變的是我們的鄉音鄉情和鄉愁。隨著時代發展,社會變遷,鄉村的城鎮化,進城定居或外出讀書打工的人越來越多,記憶中的家鄉模樣也逐漸遠離了我們的生活,消逝在我們的視線里,溫馨柔美的家鄉記憶也越來越模糊起來了。
但我會告訴孩子們,根在張柳莊,那里有生養我們的土地和親人,還有我們一代人揮之不去的記憶和刻骨銘心的牽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