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縉《游江上諸山記》原文,注釋,譯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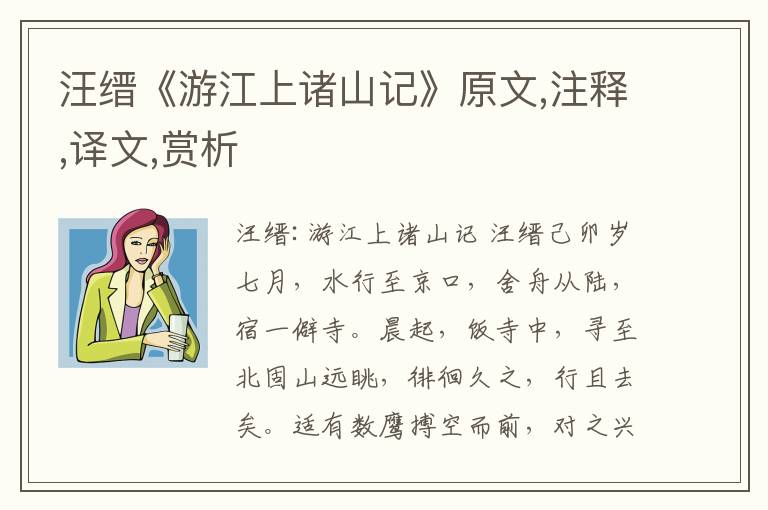
汪縉:游江上諸山記
汪縉
己卯歲七月,水行至京口,舍舟從陸,宿一僻寺。晨起,飯寺中,尋至北固山遠眺,徘徊久之,行且去矣。適有數鷹搏空而前,對之興發。遂露頂跣足,仰臥山之絕頂,目之所至,與鷹上下,一一送入蒼煙中。起視江色,夕陽千頃,面江城郭,在煙光明滅間,望之如萬灶焉。歸宿寺中。
質明而行至句容,飯中野,雨大作,少止。復行至下蜀街,雨又大作,即街上人家宿焉。質明,至龍潭,有告予以華山者。飯已而行。于時宿雨洗空,霽色千里,水從四山驟下,分注東西塍,灘聲遠近相應。行至一灘,有老僧坐樹腹中聽灘聲,予即樹旁選一石,與此僧對坐,共聽灘聲。久之乃去,行至華山道上,多高杉怪樹環道,峰連壑斷,夾一徑而上,至慧居寺。寺僧以日將夕,欲援予而止。然予奇愛暮游,遂行。
于時,日已西傾,沉沉下絕壁矣。四顧華山虧蔽處,天容盡缺,霞駁山黝,一息萬變,余光回照,四野蒼蒼,荒荒平林,遠峰參差,廬舍下隱下見。歸宿龍潭,夜中矣。質明,步入棲霞。西霞之勝,蓋在松石矣。寒翠蒼綠,深青淺碧,偃崖挺澗,升林墜壑,不可名狀。號九柯松者,歲月尤古,久坐其下,視過頂云日,宛若清霜白月也。有幽居庵者,庵有方池,入其門,見云氣從千尺松梢垂空而下,掛于池邊,盡成飛瀑。即而視之,乃石壁也。
予一日數至其地,是游,寓般若臺,居四日,乃行。步至金陵,入太平門也。
這篇游記實際上是一篇旅途的散記,全文不滿千字,卻包容了作者從鎮江至南京一路經過的名山勝跡。路線是沿著長江北行,所以稱之為“江上諸山”,主要寫了鎮江北固山、句容華山和金陵棲霞山的風光。
作者游及這些山川名勝之時并沒有去憑吊古跡,感嘆六朝興亡,緬懷昔日繁華;也沒有去形容江山壯麗,贊美江水浩渺,描摹山勢雄偉。這些都是前人詩文中反復吟詠過的。作者純從個人的體驗出發,抒發自己游山的獨特感受。如北固山遠眺,金山、焦山在望,又是歷來兵家爭斗之地,本可大加發揮,辛棄疾便有“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的名句,然而,作者寫登臨北固,僅用了“徘徊久之,行且去矣”八字。忽將筆鋒一轉,去寫鷹擊長空的景象,隨后抒寫自己的興發之情:“露頂跣足,仰臥山之絕頂,日之所至,與鷹上下,一一送入蒼煙中。”讀者由此見到的是一幕活生生的人物活動的畫面,而景色的描繪已退到了次要的地位。而正是從作者的游興與行動之中鋪寫出了山水的奇麗。這里作者個人的情感已化入到自然景物中去,主客體水乳交融。從他光頭赤腳,目送飛鷹的自我寫照中可以見到山水的魅力。又如寫句容縣的華山之游,也沒有用許多筆墨去刻劃山水的形態,而寫了自己在去華山途中坐聽灘聲的情態。然而,正是通過老僧的形象和自己的經驗,使讀者得以想見新雨之后灘水流淌之聲,以及景色的清新幽靜,令人想起岑參“酒影搖新月,灘聲聒夕陽”的詩句。風光的宜人,都于此中曲曲傳出。其他如寫自己的暮游,寫久坐九柯松下的情狀,也都景中有人,極富個性,一個聲色具備的活的漫游者的形象已隱然可見。我們在山中看到的不是通常的模山范水,而是作者個性的體現,它是汪縉于此時此地的真實見聞,而不是輿記地圖的照樣翻版。
本文對于景物的攝取也力避寬泛的描寫,試圖刻劃出最富于特征的場面和物象,就象高明的攝影師,避開了眾人擁擠的“景點;,而恁著自己的慧眼去探尋和發現自然之美。如寫北固遠眺,時在“晨起”之后,應為白日之事,然作者于遠眺所見未著一字,及至徘徊、仰臥之后,暮色降臨,于是“起視江色,夕陽千頃,面江城郭,在煙光明滅間,望之如萬灶焉。”為什么作者在北固山上徜徉了一整天,而到了暮色蒼茫之時才去刻劃其遠眺所見呢?這絕不是出于偶然,而是作者巧于安排的匠心所在,因為夕照中的江南與城郭最有特色,“望之如萬灶”,正是作者于此時的一種特殊感受。如此,便不同于泛泛而寫的登覽之作。又如寫棲霞之勝,歸于“松石”二字,于是作者將筆墨集中于描寫蒼松與怪石之上,特別介紹了九柯松與幽居庵兩地,層層集中,最后凝聚在兩個點上,使讀者的注意力聚集在最有特色的景觀上,如同電影藝術中用變焦距鏡頭的拍攝手段,由面及點地集中了觀眾的視線。至如寫幽居庵中形似飛瀑的石壁,用了畫龍點睛的手法,首先描繪出云氣垂空,飛瀑千尺自天而降的畫面,然后點出此為一石壁,頓令文筆跳蕩,具有驚心動魄,引人入勝的魅力。
總之,此文從剪材布局到記事繪景,無不表現出強烈的個性色彩,既體現了作者對大自然的酷愛,也反映了他個人的情趣。如高臥山顛,目極尺鷹,靜聽灘聲,久坐石松等行為都表現出一種欲與自然冥合,追求超逸散淡的心理。作者把對鎮江北固山和句容華山的描寫都安排在暮色之中,可見其對“暮游”的特殊愛好,反映了他對靜謐恬淡氣氛的向往和朦朧美的追求。 他的心境一如他所勾繪的清霜白月,明潔清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