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李愿歸盤谷序》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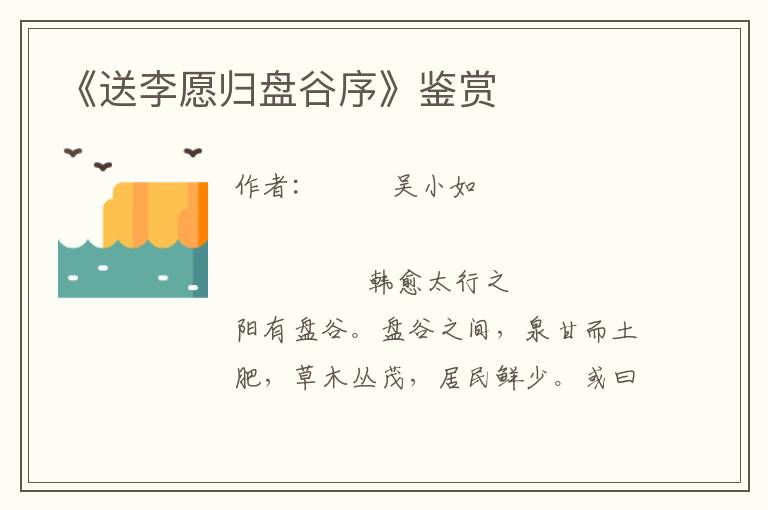
作者: 吳小如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1):“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2),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為也。
“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3)。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于山,美可茹(4);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后;與其有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車服不維(5),刀鋸不加(6),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于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
“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7),口將言而囁嚅(8),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儌幸于萬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為人賢不肖何如也(9)!”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10)。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11);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詳。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12),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曾表彰韓愈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其實,這只看到了韓愈提倡古文的一個方面。如果翻閱一下韓愈的全部文章,就會感到他寫的散文不僅要“起八代之衰”,而是企圖集古今之大成,在繼承先秦兩漢、魏晉六朝各體文學作品的基礎上走一條創新的路。
自六朝以來,有文、筆之分,所謂“有韻為文,無韻為筆”。《送李愿歸盤谷序》原是散文,但文中押韻的句子并不少(韻腳卻很自由),可謂融文筆為一。其文總的間架結構是散體,但具體描寫卻多偶句,可謂融駢散為一。鋪陳摹寫處文句有時有韻,有時無韻,儼然開唐宋古文賦(如《阿房宮賦》、《秋聲賦》、《赤壁賦》)之先河,而實際則直接繼承了漢魏六朝賦體的特點。篇末以有韻歌詞作結,這首歌前一半象《詩經》和《石鼓文》,后一半則全用《楚辭》句型,可以說做到《詩》、《騷》二體巧妙而有機的結合。難怪前人認為晉無文章,只有一篇陶淵明的《歸去來辭》而已(歐陽修語);唐無文章,只有一篇《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蘇軾語)。話雖稍近夸張,實足以說明其文之確具特色。
下面談談這篇文章的結構藝術。一言以蔽之,可以說它是以“偶”為主的。所謂“偶”,指兩兩相稱或彼此對比。但在相稱或對比之中又有所側重,顯得在排比對偶中有變化,并不要求整篇的布局絕對均衡。我試名之曰“偶中有奇(畸)”。如第一段寫盤谷,用傳統史書的術語說應屬于“記事”性質,而后面李愿的大段發言以及韓愈送行的歌詞,皆屬于“記言”性質。“記事”部分只說了簡短的一段,而“記言”部分則占了全文絕大部分篇幅。這就是偶中有奇。至于“記言”部分,又以李愿之言為主,韓愈相送的歌詞不過是陪襯之筆。但作者此文本為送人而作,理應作者是主而李愿是賓。今則以賓為重點,主反退居次要地位,這又是偶中有奇。李愿的話共劃分為三個自然段,人物雖屬于兩個范疇,卻包括著三種身分,這還是偶中有奇。對于“人之稱大丈夫者”,其描述共分在朝、出外和平居日常生活三層,這仍是偶中有奇。而對第三層的描寫,雖分外有“才俊滿前”,專門阿諛奉承和內有“粉白黛綠者”列屋爭妍這兩個方面,看似均衡布局,然而對后者的描寫筆墨偏多,以見其在荒淫享樂方面尤重于愛聽歌功頌德的話,依舊是偶中有奇。第二段寫“大丈夫不遇于時者之所為”,又分三小節(“三”為奇數):一是生活上“惟適之安”,二是精神上的“無憂于心”,三是對世事的不聞不問。而這第三小節卻是一、二兩小節的一個小結。其偶中有奇的結構特點更為顯然。
末一段歌詞,從“盤之中”到“如往而復”共六小節,都是兩句一節,比較勻整。但前三節和第五、六兩節都是實寫,獨第四節為虛筆,并不相稱。從“嗟盤之樂兮”至結尾“終吾生以徜徉”,也是六小節。但這后一個六小節與前六節不同。前三節是泛說,每節三句;中二小節是指李愿,每節一句;最后一小節是說自己,卻寫了三句。看似勻整,卻屢有變化。這也屬于“偶中有奇”。
本篇的主題思想也不是一眼就看得出的。歌公正隱者僻居山林之樂,自是題中應有之義。但這是最表面的意思。而譏刺豪門權貴的炙手可熱和嘲諷“伺候”、“奔走”之徒的厚顏無恥,則是比較深入一層的揭露了。至于通過李愿之口,強調窮通“有命”,宣傳明哲保身之道,應屬文章的局限性,然而這仍非作者之意的主旨。作者真正的用心所在卻若隱若顯地體現在李愿所說的三段話的后兩段中。那就是:所謂:“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的“大丈夫”,其當權得勢和荒淫享樂的好運氣實際是不會長久的。冰山易倒,統治階級內部的互相傾軋,達官貴人因胡作非為而招來的飛災橫禍,這正是中唐時期經常出現的社會現實。李愿正是針對這種活生生的現實才發出這樣的感慨:“與其有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以及“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這一類的話。所以韓愈在送李愿的歌詞中提到了“虎豹逐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虎豹”、“蛟龍”顯然是比喻,而“不祥”的實質則是指當時黑暗腐朽、瞬息萬變的動蕩政治局面。
但韓愈的文章是寫得相當巧妙的。在李愿對“人之稱大丈夫者”一段描述中,明明是譏刺,看去卻仿佛歌頌;明明是揭露,看去卻仿佛夸耀。甚至愈寫愈鋪張,看去似艷羨口吻,實際卻是無情鞭撻。而對這種“大丈夫”所即將面臨的危險處境,卻含蓄地停頓不說下去,然后在后面的幾段話中曲折地把真意透露給讀者。所謂“儌幸于萬一,老死而后止”,即是說無論高高在上的達官貴人或依附于權豪之門的無恥之輩,能保全首領活下來的不過是極少數的例外而已。因此我認為,六朝駢文雖辭采富贍,典故很多,但文章內容卻比較直接了當,沒有什么深度;唐宋八家的古文,看似平淡質實,而它們所反映的思想內容卻深微曲折,不是一下子就能從表面上看得出來的。然則蘇軾說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其真正可貴處反而在此不在彼呢。質之讀者,不知以為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