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有光《項(xiàng)脊軒志》抒情散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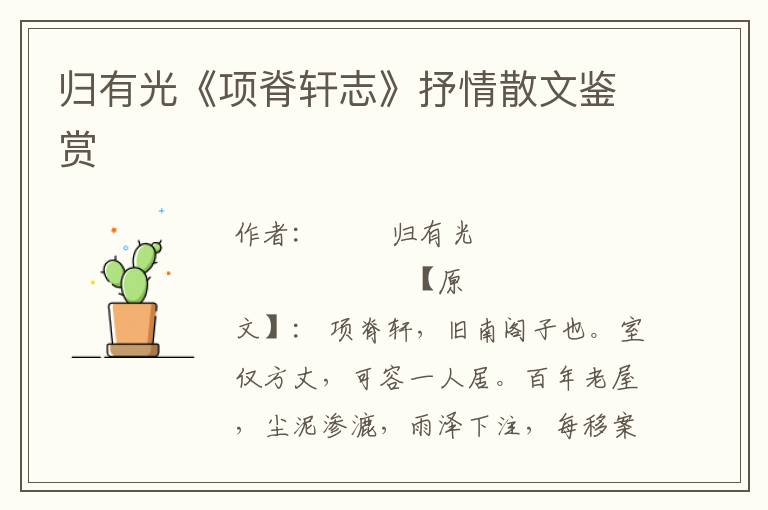
作者: 歸有光
【原文】:
項(xiàng)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墻周庭,以當(dāng)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于庭,舊時欄循(2),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墻,桂影斑駁,風(fēng)移影動,珊珊可愛。
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為一,迨諸父異爨(3),內(nèi)外多置小門墻,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雞棲于廳。庭中始為籬,已為墻,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于此。嫗,先大母婢也(4),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5)。室西連于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余曰:“某所,而母立于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為應(yīng)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發(fā)(6),讀書軒中。一日,先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7),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zhí)此以朝,他日汝當(dāng)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
軒東,故嘗為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8),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hù)者。
項(xiàng)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懷清臺(9)。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昧昧于一隅也(10),世何足以知之?余區(qū)區(qū)處敗屋中,方揚(yáng)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
余既為此志,后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幾學(xué)書。吾妻歸寧(11),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后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fù)葺南閣子,其制稍異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
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12)。
【作者簡介】:
歸有光(1506——1571),字熙甫,號震川,明朝昆山(今江蘇昆山)人。嘉靖十九年中舉,以后屢試不第,遷居安亭江上讀書講學(xué),從學(xué)者常數(shù)百人。六十歲時中進(jìn)士,授長興縣令,后官至南京太仆寺丞。
歸有光是明代優(yōu)秀的散文家,他和唐順之、王慎中、茅坤等人反對前后七子的復(fù)古主義主張,并以散文創(chuàng)作與之對抗,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使當(dāng)時的文風(fēng)有一定的轉(zhuǎn)變,后人稱之為“唐宋派”。歸有光的散文受司馬遷和唐宋諸家的影響,簡潔平淡,直抒胸臆,對清代桐城派影響較大。有《震川文集》。
【鑒賞】:
《項(xiàng)脊軒志》是歸有光抒情散文中的代表作,集中體現(xiàn)了他簡淡平易而又真切感人的風(fēng)格,在藝術(shù)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歷來為人所稱道。
項(xiàng)脊軒是作者年輕時讀書的地方,作者及其家庭的變遷都通過這一間僅“可容一人居”的小屋表現(xiàn)出來。文中記載了很多日常小事,看似瑣碎,無關(guān)宏旨,純屬信手拈來,但卻都與項(xiàng)脊軒有關(guān)。項(xiàng)脊軒實(shí)際上是全文記事抒情的一條線索,它把一件件小事,一個個人物緊緊連系在一起,使得文章形似散漫,神實(shí)聚合,做到了形散神不散。
作者善于選取典型的事件,寥寥幾筆就能逼真地勾畫出一種場景。如寫分居之后的混亂,只用了“東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雞棲于廳”十三個字就形象地表現(xiàn)了出來。寫對祖母、母親和妻子的懷念也分別選取了最能體現(xiàn)人物特點(diǎn)的事例,筆墨雖不多,事情雖不大,卻使人物的音容笑貌躍然紙上,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象姚鼐所說的:“震川之文,每于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fēng)韻疏淡,是于太史公有深會處。”
作者善于描摹人物的言語神情,每以口語入文,卻能收到自然真切,形象生動的效果。如寫母親叩門而問“兒寒乎?欲食乎?”就充分表現(xiàn)出慈母的情懷。又如寫祖母的一段話則既表現(xiàn)了一種關(guān)切責(zé)備,又表現(xiàn)了一種鼓勵期盼。而諸小妹的天真好奇則通過“何謂閣子也?”的問話活靈活現(xiàn)地表露出來。作者能用直白的口語表現(xiàn)出各人不同的個性,可見其運(yùn)用語言的嫻熟技巧。
這篇文章的最大特點(diǎn)是于敘事中飽含著真摯的感情。作者描寫修葺后的項(xiàng)脊軒怡人的環(huán)境,流露出一種自得歡喜的情緒,然而作者著墨最多的卻還是“悲”的抒發(fā)。幾十年來,項(xiàng)脊軒幾經(jīng)變故,先是家族的分裂,后是祖母、母親和妻子的謝世、作者撫今追昔,感慨萬端,形之于文字,也自然有動人之語。而作者對親人的懷念是通過回憶她們的音容笑貌而自然流露出來的,同時用一種淡然的筆調(diào)透露出自己的哀思。如寫對亡妻的懷念,只以“從余問古事,或憑幾學(xué)書”兩句追憶在項(xiàng)脊軒中的活動,但兩人的親密融洽卻不難想見。而這種幸福卻更襯托出失去伴侶后的寂寞凄涼。作者在這里未用寫祖母和母親時的“泣”、“號”等語,僅以“室壞不修”一帶而過,卻更加深切地反映出作者悲哀悼念之情。作者仿佛只是在回憶昔日之瑣事,但由于其中蘊(yùn)含著真切的感情,流之于筆端也就自然能感人肺腑,所謂“無意于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于言表”,“不事雕飾而自有風(fēng)味”。
這篇文章并非一時所作,后面兩段是以后加上去的補(bǔ)記,主要抒發(fā)對亡妻的思念,文章最后忽然提到了庭中的枇杷樹,使感情曲折遷回,含蓄地表達(dá)出了物在人亡的凄愴,作品到此戛然而止,卻因而顯得回味無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