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方芳《指端光陰》散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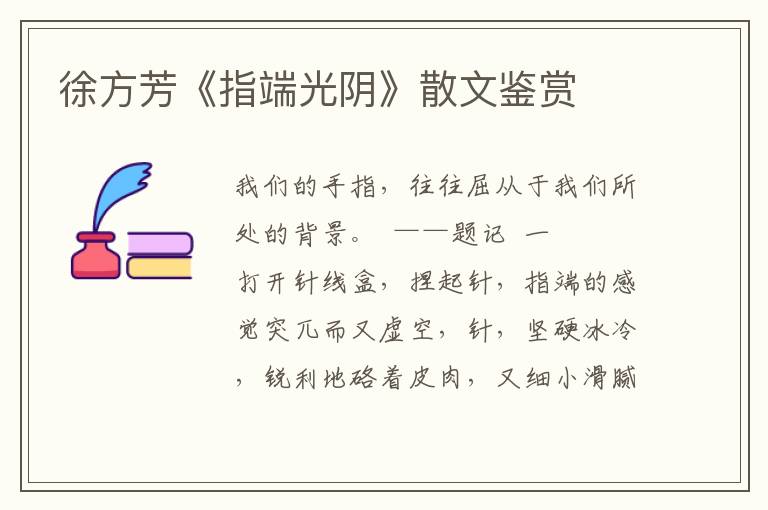
我們的手指,往往屈從于我們所處的背景。
——題記
一
打開針線盒,捏起針,指端的感覺突兀而又虛空,針,堅硬冰冷,銳利地硌著皮肉,又細小滑膩,稍微疏忽就滑落無蹤。穿線也無比生澀,針眼不夠規整,線又不停劈開、發毛,剪來擰去也沒有形成平滑窄細的前端,遠非從前的針線可比,實在與這個講求精密度的時代背道而馳,又盡在情理中——用針線的人越來越少,考究它們的質量反而是一種浪費。
折騰許久總算針線一體,開始縫補孩子長褲膝蓋上的破洞,聽說有種卡通布貼,一粘就好,又快又美觀,我卻樂得自己動手,牽引著針線在布料里往返穿梭,才覺得真正像個女子。偶爾修補衣物、釘釘紐扣,總讓我暗暗得意,因年少時學得的這點小技能,我不必像多數同齡人一樣,衣服有點損壞就要到處尋覓漸漸稀少的裁縫店或只得丟棄。
大學時代,我是宿舍唯一有針線的,室友的媽媽看到我取出針線包,一臉驚喜愛憐:“難得,真是好姑娘,還會這個,不簡單呢!”我成了她眼睛里懂事能干的好孩子。那些晚間,磁帶一圈圈轉動如慢悠悠的老水車,歌聲如水,在床鋪、書桌和年輕的面容之間千轉百回。有人翻書,有人習字,有人刷刷寫信,有人折幸運星、千紙鶴,時光穿過十指,緩慢輕柔,待到準時熄燈,衣物已修好,信封貼了郵票,幸運星在玻璃瓶里閃著童話的光芒……經過指端的分分秒秒已被小心翼翼地貯存起來。彼年,世界那么小,和我們關聯的人就那么幾個,光陰悠然而從容,空氣松弛而清澈。
十幾年過去,曾整日輾轉于我們指端的物品,早在歲月中悄然隱退。大學宿舍比以前安靜得多,新居民的手指更靈活敏捷,輕快地觸碰劃掠著屏幕,(手機或電腦的),游戲、追劇、購物,朋友動態、時事八卦、相關不相關的資訊滾滾而來又滾滾而去,如此輕易地看見、參與這個世界,他們比我們快樂嗎?
不奇怪他們怎么這般沉迷,似乎人們都在沉迷中,多年前勤勉地拈著針線修修補補、翻閱書籍、握筆寫字的我的手指,閑暇時間最熱衷的是屏幕上的舞蹈。不由自主去觸摸,漫無目的地瀏覽、點開,只要手上的事情不那么鄭重緊迫,手指會隨時帶著靈魂從當下溜走,一旦落到屏幕上,就煥發了強悍的活力,輕盈、飛快、不知疲倦,牽引著魂魄上天入地、忘乎所以,時間沒有了約束,甚至沒有概念。
我又是多沉迷呢?頻頻翻看手機,讓修補衣服這幾分鐘就能做好的事遲遲沒有完成,縫好最后一針,竟已夜深,輕輕抹平針腳,天地安靜,一個補丁是我整晚的唯一所得。
二
電視機前,母親在織毛衣,一挑、一繞、一收、一送,手指如翻飛的鳥兒,熒屏上多緊張的情節也不影響她的節奏。一根孤立的毛線一寸寸變成了一件毛衣的肌理,均勻、緊致、美感十足,織成部分漸漸延長,她有時停下來,比畫一下完成部分的長度,決定接下來加針還是減針,綁扎還是留空,結袖子還是收領口,專注又嚴謹,好像正打造著一項重要的工程。
二三十年前,織針和毛線總是糾纏在女性指端,她們稱之為“毛活”,儼然是家務的一部分。家務是做不完的。于是,就看見她們午后在編織,晚間在編織,夏天樹蔭下納涼、冬天曬太陽取暖在編織,煤爐前看飯鍋湯鍋在編織,督促孩子做作業在編織,即使是上班時間,也要抓住一切機會飛針走線。孩子們的作文里,編織毛衣的場景和事件被反復提及,用于贊美母親的心靈手巧和對家人體貼入微的愛。
各種材質的織針,無論是竹子、金屬,還是木質,都一樣平直、光滑、鋒利,帶著反復摩挲之后的瑩潤光澤,那是女性溫柔的武器,在與時間的較量中奪回一件又一件戰利品。有正在進行的“毛活”作道具,女子們便成了出色的外交家,友誼之外,攀比、試探、打聽、隱瞞、挑唆、告密……這些陰暗與爭斗,憑借手上不停歇的編織避免了目光交匯而不動聲色,日子依舊絲絲入扣。
母親輩的主婦們手上整天忙著的,還有做衣服。腳踏縫紉機,像踩風琴,按住布料,迅速一抽,針尖飛快起落,細密的線腳拉出一條條筆直的線,衣衫一步步成型。母親是裁剪高手,好看的衣服打量幾眼,就能仿制出來。她一直想要個縫紉機,無奈屋子里被各種家什擠得滿滿當當,實在放不下。那時城鎮居民住職工宿舍,住房問題上沒有我們這一代人的焦慮,無奈卻一分不少。用一根針一軸線,母親照樣給我做出了時新的荷葉邊、小翻領、泡泡袖,看到的都說這個媽媽真是巧。母親自得之余也流露點小遺憾,可惜不會刺繡,你外婆做得可好了!我就問,怎么不學呢?母親淡淡地回答,哪有時間。農忙地里掙工分,農閑挖野菜、撿柴火,跑幾十里去縣城拾煤渣,化肥廠剛倒出來,閃著火星冒著白煙,大家一窩蜂沖上去撿,燙得滿手都是燎泡。不疼嗎?疼,可你慢一步就沒有了。聽得我心頭一陣刺痛,母親又彎下頭頸,繼續飛針走線,她的手干燥粗糙,布滿時間劃痕。
上了中學,我就不穿母親織的毛衣和手工做的衣服了,嫌土。孩子出生前后,母親又興高采烈地操持起她早年的看家本事,除了毛褲、開衫,線勾的鞋子,還縫制了斜襟的棉襖和背心式連衣棉褲。孩子穿上這樣的衣服,抱起來雙臂間能感到一種溫暖熨帖。帶孩子去游泳,小棉褲招來一陣艷羨,都說寶寶穿著舒服、還保護肚子不受凍。留心看去,幾乎所有的嬰孩都身穿手工織的毛衣毛褲,已經做了奶奶或外婆的主婦們,竟然不約而同地又拿起丟棄許久的織針毛線,或許是只有柔嫩的新生命才配得上這心思細密千絲萬縷的呵護。小小的毛織衣物,舒適、合體,每一件都獨一無二,也是一份獨一無二的疼愛。
待到孩子滿地亂跑,手工的棉衣就不需要穿,孩子活潑好動,衣服太暖太厚了。幾件大的,一次沒穿過。我一直收在衣柜里,我會好好保存,連同那些穿小穿舊的毛衣棉衣。多少愛意且不說,千針萬線的不僅僅是件件衣服,更是凝聚手澤的藝術品、被物化的一段段時光,彌足珍貴。
三
再炎熱的夏天,小南屋里的穿堂風也是那么涼爽。外婆左手的紡錘飛轉,一團瑩白,聲如微雨,右手騰挪,手心的棉花被擠向虎口處,又被食指和拇指快速擰搓成線纏在紡錘上,幾番旋轉拉伸變得柔韌緊實,這過程如云朵化雨一般美麗奇幻。
外婆把巨大蠶繭一樣雪白飽滿的一軸線鄭重地放起來,拍拍衣襟上的棉絮,好像對我們說,又好像自言自語,比買的好多了。而后,又拿起一團棉花重復剛才的勞動。外婆有多少線要紡呢?我問外婆,這么多線用得完么?外婆說,總有用處,不然歇著做什么呢?我看來的勞作不止,在外婆看來是歇息,她的意念里只有田里的耕作收割才是活兒。
外婆的碎布堆了冒尖的一笸籮,大的不到一尺見方,小的也就一角、一條,是裁衣服剩下的,拿起一個布片,她能說出這是哪一年誰做什么衣服剪下的,整理著敘說著,也把過去的日子梳理了一遍。大小不一、形狀各異、質地不同的布片,在外婆這里,是一個家族的記事符號,記著一個人又一個人生命中的大小事件,一筐碎布足以整理出一個家族散逸的生活史。
碎布被用來修補衣物。也常常被外婆做成枕套和布包。剪刀隨手一剪就是規整的三角、圓形、梯形、菱形,拼接與排布也那樣巧妙妥帖。一直很驚異外婆沒上過數學課如何懂得幾何之美,就像她不翻日歷照樣說出哪天什么節氣,這個月是大月還是小月,或許是因為她從不游離時間,諳熟它的步調與結構?
沒看過外婆刺繡,母親說她也沒看過。外婆年輕時,白天耗在田里,下工時饑腸轆轆,發的食物卻一定要帶回家,收割和播種時節,她的口袋、袖子甚至連鞋子里都藏著麥粒、花生、黃豆之類,只因家里有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她本不齒偷竊,太公是位鄉紳,外婆幼年就熟讀“志士不飲盜泉之水”,也讀過女子師范,卻因早年定下的婚約中途輟學。地方志上把太公定位為開明士紳,他確實接受了新思潮的清風吹拂,欣然認同并積極回應,但價值判斷卻依然根植在傳統信義的土壤中,盡管他也知道外公這邊家道中落,女兒可能會為衣食之憂所困。
有一年農歷六月六曬衣,我看見了外婆的刺繡,淺紅絲帕上兩顆深紅的石榴,滾圓飽滿,一顆還露著晶瑩剔透的籽粒,外婆的針竟繡出了一幅工筆畫。我問外婆,您以前帶這個手帕?外婆嘆息一聲,這哪是手帕,這是我新娘裝的衣襟。衣裳呢?賣給人家新娘子做鞋面了,還有夾襖、旗袍……都賣了,一家老小要吃飯,還幸虧那時候布難買,不然誰要人家穿過的衣服……
年老的外婆是地地道道的農婦。針線活之外,總搬著小板凳除草間苗,她干活慢條斯理,說話絮絮叨叨,說著說著就說起少女時代的好友周召南和顧大雅,追悔沒有像她們一樣敢走出去干革命,灶臺泥地里窩囊了一輩子。小時候,覺得這兩個名字難聽透頂,后來讀了書,知道取名法則有“女取詩經”一說,才明白看似又老又土的外婆,少女時代的朋友圈居然是這么有品位。唯一能看出外婆有點文化的,是她終年供奉著上書“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娟秀的小楷是外婆的唯一手跡。曾經寫字繡花的手,如何做到終日熟稔地縫縫補補與田間勞作,外婆的心路秘密,恐怕無人知曉,也無人猜透。
外婆生命最后幾天,反復念叨著她的閨中密友,外婆的敘說里她們還是如花少女,她想知道她們身在何處,是否安好,又無從實現,就這樣帶著不甘閉上了眼睛。少時摯友,分別之后一生沒再重逢,委實為人生悵恨。所幸今天不會如此,再遠的時空也可以通過手指來連接,即便闊別多年,動動指尖,就能獲知此時此刻彼此動向,問候、調侃、談笑,好像從不曾分離。我們這一代注定沒有了外婆那樣的遺憾,可我們的手指又何嘗是自己能真正左右的呢?到了垂暮之年,盤點這一生,又會不會因為那么多光陰在指端被白白拋擲而悔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