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霞《我的父親是木匠》散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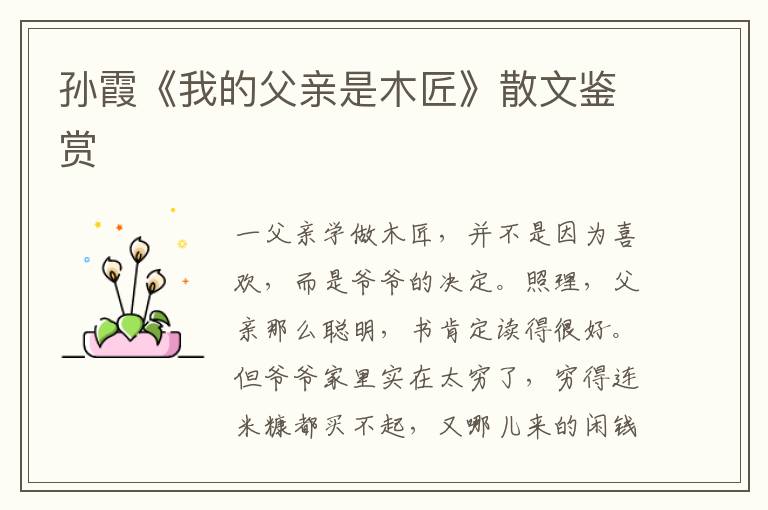
一
父親學做木匠,并不是因為喜歡,而是爺爺的決定。照理,父親那么聰明,書肯定讀得很好。但爺爺家里實在太窮了,窮得連米糠都買不起,又哪兒來的閑錢送子女讀書?于是,父親讀了兩年書后,被迫含淚退學了。
除了讀書,父親原本還有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爺爺的一個妹妹,嫁給城里一個鐵路職工。不知什么原因,夫妻倆一直不見生育。他們選了爺爺的第四個兒子,也就是我父親做養子。爺爺自然高興,一則兒子將來可以頂職做一個拿工資的城里人,二則家里少了一個人挨餓。
姑爺爺在鐵路部門上班,工資還挺高,送父親讀書沒有絲毫問題。父親讀書的機會又來了。沒想到,一向通情達理的姑爺爺,不知道受了誰的唆使,居然跟爺爺提出一個條件:愿意收父親為養子,但必須送三擔稻谷給他家。爺爺原本就舍不得可以抵大半個勞力的父親,心想:養了這么大的兒子白白送給你,你不懂得感恩就算了,還反過來找我要東西。爺爺堅決不干,連夜走了三十多里路去城里喊父親回家。當時,父親已經在姑爺爺家住了兩天,吃了兩天飽飯。就這樣,父親讀書的最后機會也喪失了。
多年后,爺爺跟我們講起這件事,還是有點內疚的。他埋怨自己當年不該那么沖動,哪怕是去借三擔谷,也應該借這個機會改變父親“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命運。可父親一點兒也不后悔,他說,他只要能跟家里人在一起,吃糠也比吃白米飯香。
我覺得最應該追悔的是姑奶奶。若是她當年能勸阻丈夫,也不至于老了后無依無靠。不管如何,父親畢竟是自己的親侄子,不可能輕待了她。
父親的成績那么好,必定是喜歡讀書的。他之所以把當年的遺憾說得云淡風輕,只是不想讓爺爺奶奶難過罷了。上小學高年級的我,突然間變得勤奮起來。那個時候,只有我自己知道,我還有一份責任,替父親完成未完的心愿。
二
爺爺想著父親就這樣天天跟著他在泥巴里混,終究不是個辦法。于是,他決定送父親去學木匠。出發的那個清晨,父親望著掛在墻壁上的書包,一步三回頭。背著那套比書包重得多的“裝備”,父親瘦小的背明顯地駝下去,眼睛里原有的一束光,也在那一刻徹底熄滅。
那個年代,木匠和篾匠都很吃香。父親的一個哥哥——三伯伯,早在父親半年前就開始學了篾匠。當年,一個家庭出現兩個匠人師傅,也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
但我可以打包票,父親其實一萬個不愿意學木匠的。聽師奶奶說,父親跟著師爺爺出去做上門工,路過學堂(學校)門口時,一雙腳就像被繩子拴住了似的,半天都不見動,急得師爺爺直跳腳。師爺爺最怕帶父親去有藏書的人家做工。因為只要師爺爺一不注意,父親就會偷著去翻書柜里的書。中午時分,別的徒弟都是趕緊找地方休息一下。父親卻一個人躲進書房里看書。有時遇上東家仁厚,允許父親帶一本書回去看,父親會歡喜得連晚飯都可以不吃。
畢竟,做木工是個細致活,容不得絲毫的馬虎,必須一心一意才做得好。因為看書分心,出過幾個小差錯,被師爺爺狠狠批評過幾次后,父親的那顆不安分的心才肯漸漸平靜下來。幾年后,三伯伯和父親相繼出師,不但不在家里“白吃”,還能賺點錢。爺爺家的貧苦的生活,也因此得到了很好的改善。那邊的姑爺爺,也通過別人的介紹,過繼了一戶多子人家中的一個兒子當養子。多年以后,年邁的姑奶奶每次一回娘家,就會感嘆一句“當年哦改(為什么)不留著老四哦!”
俗話說“徒弟徒弟,三年奴隸”。雖說父親的處境沒有話里說的那樣不堪,但期間所受的磨難也是可想而知的。不說別的,父親當學徒的那三年里,師爺爺家一連添了兩個女兒,那些尿片什么的,都是父親他們幾個徒弟幫忙洗的,寒冬臘月里,一洗就是一大桶。冰冷的水,把父親的手凍成了“紫牙姜”。
我也曾在下雪的日子去池塘洗過衣服。那種被冰水刺骨的痛苦,我終身不忘。我無法想象,不過十來歲的父親,如何咬著牙,在刺骨的冰水中,洗完一桶又一桶。
三
十五歲那年,父親坐火車去岳陽做零工。父親第一次出遠門,第一次坐火車,一切是那樣的陌生和新奇。出發前的頭天晚上,奶奶幫父親準備行李。連著父親做工用的斧頭、尺子、錘子、刨子之類的都放在一個嶄新的木箱子里。試布鞋的時候,奶奶發現父親的襪子到處都是洞。正好,父親的一個哥哥剛結婚不久,有兩雙新尼龍襪還沒穿過。奶奶跟那個哥哥一說,那個哥哥連忙拿了一雙給父親。
長這么大,父親第一次穿新襪子,并且是當時流行的尼龍襪,心里別提有多開心了。他把新襪子往腳上一套,感覺自己的那雙大腳都好看了很多。父親怕把襪子穿壞了,又趕緊脫下來。睡覺的時候,他特意把襪子壓在枕頭底下。
第二天天剛亮,父親吃了早飯準備出門。他那個新婚的嫂子黑著臉過來,二話不說,逼著父親把襪子脫下來。父親除了妥協,還能怎樣?一直到出門,父親都沒有說什么,也沒有不高興,還大聲地跟奶奶他們打招呼。
坐在火車上,父親再也忍不住了。看著自己的腳,想著自己十幾年來,連穿雙新襪子的權利都沒有,眼淚如決堤般。傷心,難過,悲憤,茫然……以至于下車的時候,失魂落魄的他將工具箱遺忘在火車上了。北方的冬天來得早,雪花和寒風一個勁兒地往父親身上撲……
多年后,我嫁到了父親當年第一次出遠門的城市。在這里,我有了溫馨的家,有了可愛的女兒……我不知道,上蒼如此厚待我,是不是因為對當年父親冷漠的補償。
四
記憶里,老家附近,只要有人家蓋新房子,上梁的時候,一定會請父親去主持。這樣的大事,一般的木匠師傅做不來。父親身體好,講話中氣十足,聲音又好聽。他一開口,數里外的人家都聽得清清楚楚。記憶里,父親每天起床,都會一邊穿衣服一邊唱“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尤其是冬天,父親唱出來的聲音更是洪亮,氣勢更足。父親沒有經過專門的訓練,但那個腔調,一聽就知道不屬于通俗唱法,而是介于民族唱法和美聲唱法之間。
上梁成不成功,全靠請來的師傅主持得好不好。父親聰明,記性好,師爺爺教他幾次,基本就會了。剛開始,師爺爺不放心,站在一旁指導。后來,沒有師爺爺在旁,父親也能做得很好。父親每次主持到最后,總不忘加上一句:恭喜東家福星高照,祖輩多出狀元郎。
回想當年,爺爺若是能忍一忍,系緊腰帶也要堅持送父親讀書,指不定,父親會考個很不錯的大學。父親每次只要一提起他輟學的事,眼神便如暮色般黯淡下去。我不忍心再看父親。轉過頭去,我看到了墻壁上滿滿的獎狀。唉,若是父親能有機會繼續讀書,獎狀保準比我的還要多。
五
父親干活時的精益求精,我們三姐弟都見識過。遇上父親把木料拿回來“量線”,需要一個人當幫手的時候,我們都特別害怕父親叫上自己。因為,父親不允許我們在做事時有一絲一毫的疏忽。量出來的線稍微歪一丁點兒,都會挨上一頓父親的板臉訓斥。這或許是父親的活兒比其他的師兄師弟接得多的原因吧。我覺得,父親除了手藝好,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體諒東家的難處。那時候,做上門工的師傅,東家都是好煙好茶好飯招待。也有家里條件差,只能勉強管飽的。遇到這樣的人家,有的師傅就會裝著很忙的樣子,要么拒絕,要么將日子往后拖。父親從不做這樣的事,還常常將碗里的好菜夾給那戶人家的老人和小孩。這還不算,吃晚飯的時候,還會故意少吃一碗。當然,也有家里條件不錯,故意刻薄的,父親也只是做到心里有數,不說出來。父親的一個師弟林叔叔,也遇上過這樣的人家,他的處理方式就挺好玩的。照理,中餐那一頓,東家應該準備點豬肉之類的葷菜。第一頓,那戶人家的女主人光買了點油豆腐,林叔叔不氣不惱,照樣吃得津津有味,嘴里還夸:“油豆腐好吃,我最喜歡吃油豆腐,油豆腐就是我的命!”女主人樂得合不攏嘴。她心想,既然這個匠人師傅那么喜歡吃油豆腐,那明天再稱點豬肉,一來自己家里的人可以趁機多吃點肉,二來旁人看著顯客氣。誰知,肉一端上桌,林叔叔就光用筷子夾肉吃。那家的女主人實在看不過,干脆說出來:“林師傅,你昨天不是說油豆腐是你的命嗎?”林叔叔嘴里咬著一大塊肥肉,口齒不清地回應:“我有了肉,連命都不要噠!”
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林叔叔是個超級聰明的人。可我想不明白的是,師爺爺為什么只肯將上梁的“主持”位置傳給父親呢。
朦朧間,一米七的個子,濃眉大眼的父親,威風凜凜地高高在上,鞭炮響過,父親手執一炷香,用他那渾厚的男中音振振有詞:
發炮一響
天門開
……
這時候,東家遞給父親一只雄雞,父親接過來,奇怪的是,之前還在極力反抗,“咯咯”叫得歡的那只雄雞忽然不叫不動,老實得不得了。父親將那只雞舉起來,又振振有詞:
手捧一只雞
皇母娘娘賜予弟子一只雞
……
念到這里,東家給他遞上一把菜刀。接過菜刀后的父親,將刀背在一塊事先準備好的大木頭上用力“砍”三下,然后仰頭快速念道:
天煞要歸天主
地煞要歸地藏
……
接著,父親麻利地將雄雞放血。父親的一連貫動作干脆利落。東家又驚又嘆,臉上頓添喜色。又見父親將雞血撒向四方,向前一步,低頭念道:
雄雞血,一濺馬
……
東家眉開眼笑地接過已經落氣的雄雞,示意家人送給我母親,又給父親遞過一個篩米用的大篩盤。父親左手端盤,右手先抓起盤里的米向四周拋灑。站在下面的大人們撐開口袋,希望能裝多一點“黃金”(白米)。小孩子們只盼著父親快點撒糖果餅干。我多么希望父親能多往我們這個方向撒一些呀。可那個時候的父親,像不認識我們似的。弟弟小,不懂事,急得不行,跳起腳來沖著臺上大聲喊“爸爸”,父親也只當沒聽見,引來笑聲一片,只聽父親高呼:
手捧一只盤
黃金白米拋五方
……
父親用手擦了擦額頭的汗,雙手接過東家的一瓶酒。父親那高亢的聲音在云朵里飄蕩:
手執一瓶酒
上有烏篷蓋頂
……
依稀間,那聲音跟教室里讀書的聲音混合在一起。座位上,一個濃眉大眼的小男生,儼然端端正正地坐捧著一本書,鏗鏘有力地讀著:天地玄黃,宇宙洪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