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瀚《東游記(節選)》原文,注釋,譯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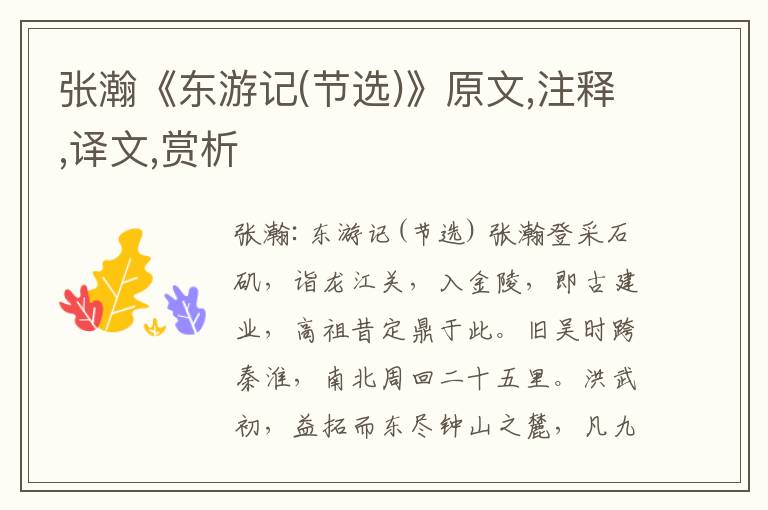
張瀚:東游記(節選)
張瀚
登采石磯,詣龍江關,入金陵,即古建業,高祖昔定鼎于此。舊吳時跨秦淮,南北周回二十五里。洪武初,益拓而東盡鐘山之麓,凡九十六里。立門十三,南曰“正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鐘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鳳”,今塞“鐘阜”,“儀鳳”二門。其外城則因山控江,周回一百八十里,別為十六門。紫金諸山環亙于東北,大江回繞于西南,龍蟠虎踞,古稱雄鎮。迨今唯睹城郭崔巍,而宮闕荒蕪,殿閣只存武英,奉先,猶故物也。然宮逼近城東,而民居處其西。自長安街至大中,三山,抵水西門,路甚整潔,民居兩廊可步,尤便行人。出正陽門數里為南郊壇。出聚寶門一里為報恩寺,有琉璃塔,高二十五丈,永樂年重建,夜每燃燈數十,如星光燦爛,遙見十里之外。寺左為雨花臺,臺在山岡,可西望大江。三山門內為鳳凰臺。
出朝陽門,沿城而南,恭謁孝陵。陵中禁采樵,草深木茂,望之叢蒙,深遠不可測。惟遙望殿宇森嚴,御路傍列石器,長亙數里。前峙御碑,高三丈許,覆以石亭。亭前朱門籞戟,以時啟閉。左有懿文皇子墓,亦朱門深鎖,不能至也。洪武初,置漆園,桐園、棕園于鐘山之陽,種木各萬株,以收油、漆、棕纜,用造海船及防倭戰艦,其省民之供慮周如此。城北為太平門,內曰“太平岡”,外曰“太平堤”。三法司在堤之南,公庭簡肅,殊清閑無事。夏月面后湖,觀夾堤芙蕖,湖光蕩漾,鶴舞松陰,鹿鳴芳砌,可稱吏隱。都察院邸第在太平岡下,壯麗嚴整,傳為劉誠意先生所建。北之西有雞鳴山,登之可以眺遠,故宮遺址,儼然一望中矣。
自采石放舟而下,經燕子磯,上有觀音閣,懸大江之崖,望之危險。再下為黃天蕩,江闊水涌,四望無涯,亦無蘆葦、沙洲。雖值風恬日朗,而江濤震撼,白浪橫空,唯聞澎湃之聲而已。登儀真公署,有后樂樓,樓下四圍皆水,遍植蓮花,鳧鷗蕩漾,對景可以忘機,題后樂者,吾杭吳龍江也。
南京是六朝故都,歷代墨客作詩為文詠嘆金陵山川的不計其數。張瀚《東游記》中所寫的這段金陵游記可謂奇文。全篇僅七八百字,卻遍寫城中諸景,且脈絡分明,詳略有致,余韻徐歇。
這篇游記之所以凝煉而有余韻,首先是因為作家胸有成竹。寫金陵全景,或由明確的觀察點進行靜態描述,或由清晰的游蹤進行動態描繪。動靜結合,景物如在眼前而余味曲包,明朗處情景接人;含蓄處又喚起讀者的想象,幾欲鼓翼而飛。
作者是從浙江開始他的東游之行的:由浙江到安徽,又從安徽采石磯沿長江入龍江關(今南京興中門外),到了他供職所在地——南京,開始了他對古城的總體描述。開篇簡述舊吳以至洪武間南京地域的演變過程。然后俯瞰全貌,靜態描述南京城內城外的總布局。先是十三門,縱向由南至北,“正陽”、“太平”兩分;橫向由東向西,“通濟”、“三山”參差排列,“神策”、“金川”相映交輝。十三門敘述完畢,城郭輪廓即勾勒得十分清晰。再寫外城雖有十六門,卻不再一一道出,而是取了紫金諸山和環城大江,顯現出龍蟠虎踞之勢,再用一句“因山控江,周回一百八十里”輕輕帶住,外城的景色便也一目了然。又述城內,宮闕近東,民宅處西。一個觀察點,四句話,城內城外,城南城北,城東城西即描摹得層次分明,秩序井然。
進入城內,作者又用移步換景的辦法進行動態描寫,儼然一位導游,將可觀之景一一道出:聚寶門外的報恩寺、三山門內的鳳凰臺、朝陽門外的明孝陵、太平堤外的后湖(玄武湖)等,無一闕遺。一路上又有雨花臺、三法司、太平岡、雞鳴山,一步一景,各具特色。娓娓敘來,似漫不經心,然南北東西,風姿秀出。待到故宮遺址,俯首而望,一宮一殿,一山一水,不只是盡收眼底,而且是親切可愛的了。立足雖在城外,目光已達城里。先由城里說到城外,這里仍在城內收筆,是為圓合無隙,首尾相接。如此選景、寫景,便自然是凝煉而有余韻了。
其次,作者在局部審視時選取最有表現力的鏡頭。詳略有序地寫景,這是文章凝煉而有余韻的又一原因。南京古城景色很美,古跡很多,若將幾十處景致一一詳細描述往往會失之平板、呆滯;而要把它濃縮在七八百字之中就更是難乎其難。但作者卻運筆自如,繁簡得當。略寫的景色一筆帶過,不拖泥帶水,所謂“止于所當止”。“出正陽門數里為南郊壇,出聚寶門一里為報恩寺,有琉璃塔,高二十五丈,永樂年重建。”幾句話就交代了五處景:兩門、一壇、一寺、一塔,且寫出里程、高度、年代,堪稱惜墨如金,言簡意賅。同時該放之處還須放開,所謂“行于所當行”。中山門外的孝陵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墓地。作者作為明朝的臣民,他到這里來,就不單純為了觀賞的,而是“恭謁孝陵”,所以也就不惜筆墨加以細致的描繪。在點出“陵中禁采樵”之后,接著寫出的是:“草深木茂,望之叢蒙,深遠不可測。”仍不正面寫陵,而是把它置于青松翠柏之中,顯出它的叢蒙深遠,不可測知的雄美景色。然后才回頭遙望,寫殿宇森嚴,御道綿長,石像森列,墓墓宏敞,不覺令人想象出當年王陵體制的崇閎。那“伐罪吊民,功同湯武,攘夷撫夏,威邁漢唐”的一代英主雖已不在了,而他當年置園種樹,以造防倭戰艦,省民之供的遺澤卻長留人間,使作者感懷不已。這不同于一般的歌功頌德,而是就實景寫實事,稱頌朱元璋建國之初在國防上的深謀遠慮和在政治上的體恤民艱。接下去,寫玄武湖的優美風光。對后湖中的湖光鶴影稍稍放筆點染,燕子磯的放舟、黃天蕩下的驚濤駭浪,一筆緊跟一筆,懸空而落,詳略相間,雖未將每處景色一一端出,但投石擊水,在平靜的湖面激起一兩朵雪白的浪花,反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
再次,嚴謹冼煉而又清美樸實的語言風格,形成了此文凝煉而有余韻的特色。作者曾在他的《自省記》中摘錄了人們對他的評價,稱其有“潔峻之行,宏遠之才”,“執法不激不徐”,“器宇凝整沖曠,才華精敏特達”。這些品行反映在語言風格上就是嚴謹冼煉而又清美樸實。七八百字寫三、四十景,一景一轉,一轉一境,無絲毫緊張急促。城內城外,無論是看“每燃燈數十,如星光燦爛,遙見十里之外”,令人欣喜贊嘆的琉璃塔,還是觀“湖光蕩漾,鶴舞松陰,鹿鳴芳砌”,教人心曠神怡的玄武湖,作者都是輕攏慢捻而又引人心魄。每一景雖寥寥數語,但因把握住了景色特點,景與景之間的關系,形象仍不失生動明朗。同時因把很多短句串在一起,形成流暢的旋律,其聲似潺潺流水。而大量數據,方位名詞的運用又給人以嚴謹、科學的印象,加強了文章的可信度,從而突出南京“風景與文化交融,山川共古跡映輝”的特點。
這篇游記雖只是《東游記》中的一段,但它卻體現了作者描繪浙、蘇、皖一帶地區景色的一種手法,并且也充分發揮出游記散文的藝術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