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泰山記原文,注釋,譯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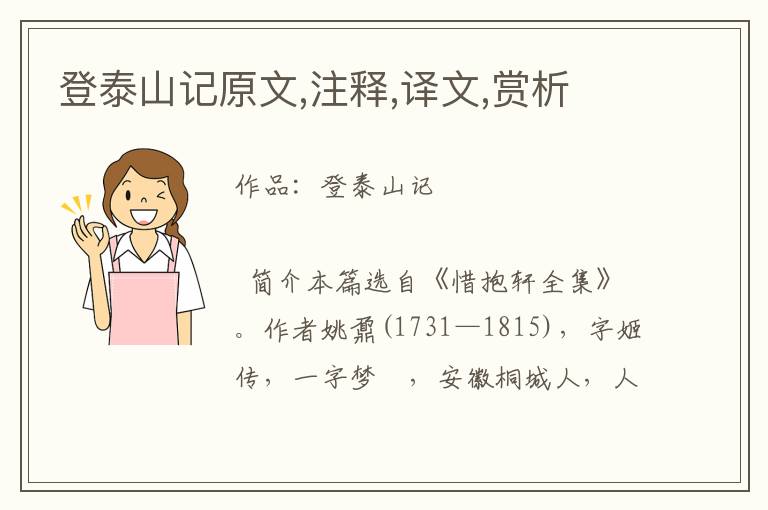
作品:登泰山記
簡介
本篇選自《惜抱軒全集》。作者姚鼐(1731—1815),字姬傳,一字夢穀,安徽桐城人,人稱惜抱先生,清代著名古文家,桐城派的重要作家,曾參加《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其論文主張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并重。《惜抱軒全集》共八十八卷,包括文集、詩集、《法帖題跋》、《左傳補注》、《國語補注》、《公羊傳補注》、《穀梁補注》、《九經說》等。本篇是一篇游泰山后的游記,對深冬時節泰山景物的描寫如詩如畫,寫出了泰山的雄偉壯麗。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①。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峰,在長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于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潁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為磴,其級七千有馀。
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
戊申晦,五鼓,與子潁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云漫,稍見云中白若摴蒱數十立者②,山也。極天云一線異色,須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絳皓駁色,而皆若僂③。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④,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跡。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
桐城姚鼐記。
注釋
①陽、陰:古人稱山南為“陽”,稱山北為“陰”。 ②摴(chū)蒱(pú):同“樗蒲”,古代賭具。 ③絳(jiànɡ):大紅色;皜(hào):同“皓”;駁:雜;僂(lǚ):彎腰曲背。 ④罅(xià):瓦器的裂縫,此處指縫隙。
譯文
泰山的南面,汶水向西流;它的北面,濟水向東流。南面山谷的水都流入汶水,北面山谷的水都流入濟水。成為南北山谷分界的,是古代長城的遺址。泰山最高處的日觀峰,在長城南面十五里的地方。
我在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從京城冒著風雪,經過齊河、長清,穿過泰山的西北谷,越過長城的城墻,到達了泰安。這個月的二十八日,我與知府朱孝純子潁從泰山南麓登山。四十五里的山路,都是用石頭砌成的臺階,總共有七千多級。
泰山正南面有三道山谷,中間山谷的河流繞泰安城而過,這就是酈道元所說的環水。我開始巡著山谷進去,走完了一小半路程之后,再翻越中嶺;又順著西谷上去,就到了山頂。古時人們登山,順著東谷進去,途中有道天門。東谷在古時被稱作天門溪水,是我沒有到達的地方。現今所經過的中嶺和山頂上擋在路上的山崖,世人都稱之為天門。路上迷霧彌漫,冰雪滑溜,石板臺階幾乎沒法攀登。等到了山頂,只見蒼郁的群山積滿了白雪,雪光映照著南面的天空;遠望夕陽映照著城墻,汶水和徂徠山猶如一幅圖畫,而半山腰上停著的云霧就像一條帶子一樣。
戊申這月月底,五更的時候,我與子潁同坐在日觀峰的一個亭子上等待日出。大風刮起積雪撲打在臉上。亭子的東面從我們的腳下起都是云霧彌漫著,隱隱約約看見云霧中數十個白色的像骰子一樣站立的東西,那就是山峰。在極遠的天邊,有一條云線顏色奇特,一會兒就變得五彩繽紛;太陽出來,紅得像朱砂,下面有一片晃動的紅光浮托著它。有人說,這就是東海。回過頭看日觀峰以西的山峰,有的被陽光照著,有的還沒有,紅色與白色錯綜相間,又都像彎著腰曲著背一樣。
日觀峰亭子的西面有岱祠,還有個碧霞元君廟;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廟的東面。這一天,我們沿途觀看了路邊的各種石刻,這些石刻都是唐朝顯慶年間以后的,那些古老的石刻都模糊毀壞了。偏僻不在正路上的,都來不及去看。
山上石頭多,土少;石頭青黑色,方方正正的多,圓形的少。雜樹少,松樹多,長在石頭縫里,都是平頂的。冰雪覆蓋,沒有瀑布,無鳥獸的聲音和足跡。靠近日觀峰的數里內都沒有樹,而積雪與人的膝蓋齊高。
桐城姚鼐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