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羆說》文章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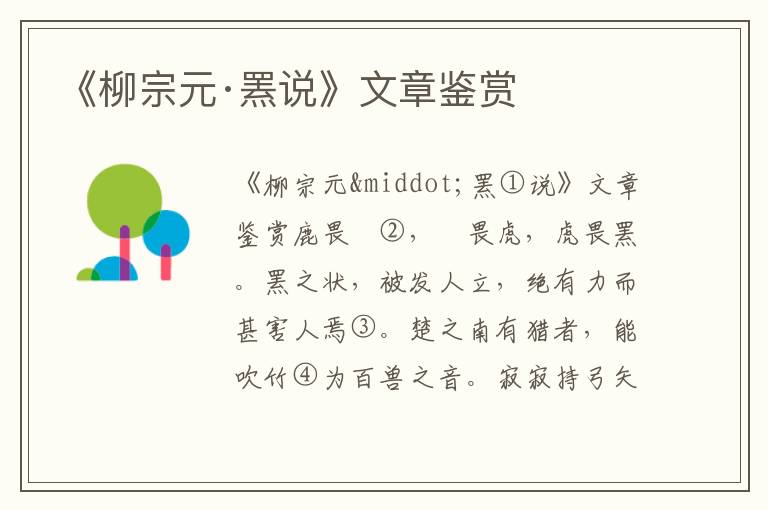
《柳宗元·羆①說》文章鑒賞
鹿畏貙②,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發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③。
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④為百獸之音。寂寂持弓矢罌⑤火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⑥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⑦。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捕⑧挽裂⑨而食之。
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注】
①羆(pí皮):熊的一種,俗稱人熊或馬熊。比一般的熊大,黃白花紋,能直立行走。②貙(chū初):獸名。也稱貙虎,形狀像野貍貓而體大。③被(pī劈):同“披”。絕:最,非常。④竹:指小竹管。⑤罌(yīng英):一種腹大口小的瓦罐。古代用來盛酒水,這里用來裝燈火。⑥發火:亮出燈火,以便照明射擊。⑦亡去:逃跑。⑧捽(zuó)捕:揪住搏擊,扭打。⑨挽裂:撕開,撕裂。
《羆說》是一篇托物喻人、含義深刻的寓言小品,是柳宗元貶官永州(今屬湖南)時所作。這則寓言含義深刻,它描述了一個靠吹管吸引野獸而沒有真實本領的獵人的可悲下場,有力地諷刺了社會上那些不學無術、靠吹噓來欺世盜名的人。這種人雖然能依靠欺騙手段蒙混一時,卻往往在緊要關頭原形畢露,以致害了自己。
開篇處,作者選用連鎖遞進兼排比的句式:“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徑直點出了本文的四個角色,以一物降一物來揭示其中的關系。在鋪墊充分以后,用細致筆墨描繪了一個沒有真本領的可悲獵人,經過激烈爭斗以后喪命熊口。
獵人的悲劇不是出于偶然,一個沒有打敗野獸本領的人,單單憑著出色的擬聲能力,是沒有辦法對付強大的外物的。從而揭示宗旨:那些不善于增強自身的實力,專門依靠外界力量的人,遲早會遭到獵人一樣的下場。
另外,此篇寓言也暗示作者對腐朽無能的封建統治者的諷刺,聯系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安史之亂以后,藩鎮勢力日趨膨脹,朝廷為了牽制那些跋扈的強藩,就有意識地扶植另一些節度使,企圖以藩制藩。結果是東藩未平,西藩更強,對中央的威脅愈加嚴重。柳宗元本不贊成“以藩制藩”的做法,本文末句“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的告誡,就是在譏諷唐統治者不修內政、依賴外力的各種政策的弊害,隱喻朝廷如不加強中央集權,而采“以藩制藩”的錯誤做法,必將招致像獵人一樣的覆滅命運。
總之,本文不足九十字,卻描繪生動,又不乏完整的故事情節和豐滿的角色,完成了一個故事從鋪墊到結束的全部過程,語言堪稱是簡練精辟!
后人評論
林紓在《韓柳文研究法》中批注:“必有一句最有力量,最透辟者鎮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