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聞宇《檢討豪杰》散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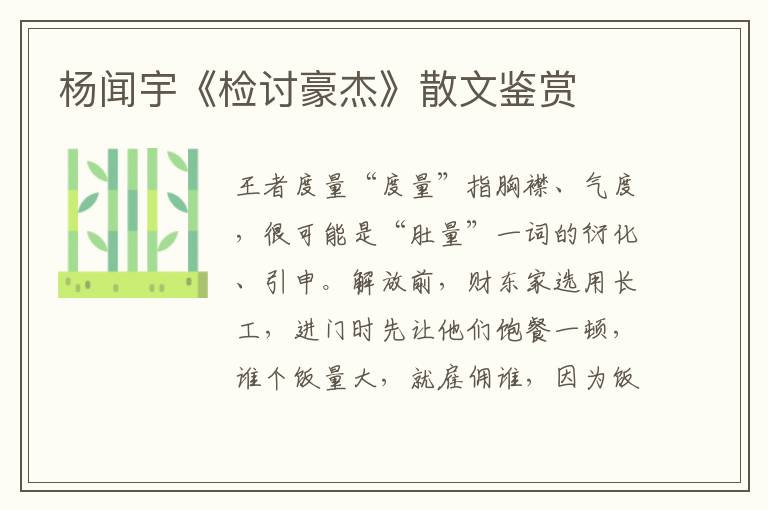
王者度量
“度量”指胸襟、氣度,很可能是“肚量”一詞的衍化、引申。解放前,財東家選用長工,進門時先讓他們飽餐一頓,誰個飯量大,就雇傭誰,因為飯量大者有力氣,有力氣才能多干活。而俗語里的“宰相肚里好撐船”,則指的是政治襟懷,屬于微妙的精神境界,是一種獨具的主觀意識。對于經緯天下的治國者而言,“度量”如何,于事業成敗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公元前494年,吳國敗越于夫椒,越王勾踐表面服輸,暗地里卻“臥薪嘗膽”,19年后,翻回手突襲吳國。越國能反敗為勝,是勾踐善用人才、勵精圖治之外,又特別注重瓦解敵方的君臣關系,將“重寶以獻遺太宰嚭”,讓伯嚭挑撥夫差與伍子胥的關系,逼迫賢能的伍子胥自刎。夫差被越圍困時,寫下一封信用箭射給越國的謀臣文種、范蠡:“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夫差是悔也無及,可信里的話卻是針針見血(范蠡引退而全身,文種戀棧被迫自裁)。這說明夫差臨終時已經悟到:一國之主有無選賢任能的度量襟懷,是事業成敗之關鍵;可對取勝者而言,“度量”二字又會急遽地發生變異。
劉邦拜韓信為大將時,韓信評價項羽:“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意思是:匹夫之勇不足為訓,善用人才則天下無敵。劉邦登上皇位,評價張良、韓信、蕭何時,對此“三杰”接連使用了三個“吾不如”。劉邦的總結非常到位,體現出領導者之度量,集中在選賢任能的襟度、魄力上。
度量的效用如此顯著,說到底只是事物的一個方面,令歷代精英所解不開的是:帝王家這等度量,是以“勢當兩立”為前提的。精英群落里,張良是個罕見的佼佼者。眼見滅楚之后,鯨布、彭越、韓信在同一年(公元前196年)相繼被劉邦除掉,再加上文種、范蠡的不同下場,張良很快就省悟,還是夫差的那封信點中了要害:敵手如在,統治者是解衣推食,盡量利用人才之優長,敵手一旦被扳倒,統治者則立即翻回手遽擊內部人才之短板——這就是帝王們所深深隱藏著的“回馬槍”。于是,他堅決地脫屣繁華,躲進秦嶺深處辟谷去了。
文治與武功,在一個帝王家手底是日月那樣的難于并舉,李世民則是個例外。論武功,與李世民齊肩者不乏其人,若論文治,史冊上則無出李世民之右者。登上龍椅,李世民沒有毀棄功臣,“鸞鳳凌云,必資羽翼”,尤其是對魏徵的任用,非常耐人尋味。
魏徵比李世民年長19歲,公元618年被李建成用為幕僚。眼見李世民功業日隆,嚴重威脅到太子的地位,便多次告誡建成要先發制人,否則,后果不堪。玄武門骨肉相殘的惡斗過去之后,李家多位親人栽倒于血泊之中,李世民召征責之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這是仇人相對時分外眼紅的質問,眾皆為之危懼。而魏徵卻慷慨自若,從容對曰:“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魏徵沒有服軟,只悔怨建成未聽他的話,才致成目前慘局。可誰也料想不到,李世民這時候反而是抽回了架在魏徵脖頸上的鋼刀,轉拜其為諫議大夫。一反常規而重用敵手,李世民是一時的心血來潮嗎?
玄武門政變之前,李世民早就注意到魏徵。他曾經聽魏徵的兩位前上司說起過魏徵其人,李密承認自己沒有聽從魏徵的十策是失敗的原因之一,竇建德認為魏徵是千古奇才,只是運氣總是晦氣。魏徵后來被建成用為幕僚,說服建成掛帥出征,運用攻心之術,沒打什么大仗就收服了山東、河北,樹起了文武全能的高巍形象;而且在征戰山東的過程中結識了羅藝、李援等強手,太子地位益發牢固。嗣后,李世民與建成明爭暗斗,并沒占到多少便宜,身邊的謀士房玄齡、杜如晦反被趕出了秦王府,逼得他不得不鋌而走險,發動武裝政變。自不同的角度,李世民算是全面見識了魏徵的本事與才干。
李世民好學深思,極善于審時度勢。前朝的楊廣是排擠了兄長、扼殺了父皇才上得龍椅的,而自己是殺死兩個兄弟才奪得皇位的,政變僥幸成功,可在法統和道德上卻是輸得精光,下一步倘不能在文治上有所建樹,與楊廣能有什么區別呢?然而,武功迥異于文治,眼前治國理政的棘手難題,憑仗馬背上的那一套是無法奏效的。所以,心里早就暗暗籌劃著,要重用魏徵這個千古難得的人才。
李世民襟懷博大,度量如海,其收效也極其顯著。“由于唐太宗不拘一格,廣開言路,重用賢才,使得他統治的時期,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少有的升平時期,出現了有名的‘貞觀之治’。”(習近平語)魏徵在李世民身邊17個春秋,后人盛贊貞觀之治,首先歸功于李世民,再者就是魏徵。
檢點歷史,可以推知,一個清醒的領導者的襟懷度量,是從實踐中取得的,形成之后也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其變化的流程與軌跡,個人心理素質固然是決定性的因素,但也不能輕忽不斷發展變化著的外部環境。
襟懷磊落一丈夫
袁枚、蔣士銓、趙翼并稱乾隆三大家,蔣、趙推重袁枚,其詩集皆請袁枚為序。袁枚的文章里,我尤其喜愛《記魯亮儕》。
魯亮儕在河南總督田文鏡門下供職。田公位高權重,以嚴厲苛刻著稱。有一天好事來了,田公命令魯亮儕去摘取中牟縣李令的官印,并就此代理縣令。魯亮儕去了中牟,很快又折了回來,起因是深入了解之后,他認定李令是個賢能的官員,別人的彈劾雖非誣告,可內中的情由卻值得體憫。魯亮儕違背田公之令,決心放棄這個誘人的官位。
田公麾下的提、鎮、司、道各級官員,對田公都服帖、敬畏。魯亮儕回省之后,先去拜見布政司、按察司,詳細稟報了事情的內情、原委。兩司皆曰:“魯亮儕呀,你難道犯喪心病了嗎?哪有你這樣辦事的?這種事在別處尚且不許,何況田公!”
文章緊要處,是魯亮儕翌日一早面見田公。眼見田公就要發火,斡旋其間的兩司趕忙拜伏請罪:“是我們平時教誡不力,才有魯亮儕這樣狂妄悖理的官員。這事交給我們,我們嚴厲審訊他在中牟縣拉派作弊的罪行。”魯亮儕脫下官帽,當即向前叩頭,大聲說道:對呀,應當這樣。可我請求把話說完(下面是魯亮儕的原話)——
裕(亮儕名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圣上以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為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
他簡要表明自己赴任經過兼及改變初衷的原因。接著,話鋒直指田公:我說的這些情況,大人如果事前了然于胸,我這樣復命,那就是我的罪了;如果大人不了解內中情由,我今天回來申明原委,或許可以不辜負大人的愛才之心(李令有才能),同時也不辜負圣上以孝治理天下的意旨(李令是借俸盡孝才虧損帑庫的)。大人這次差遣,是額外地抬舉我、器重我,我非常感激,在你的厚愛之下,我如果輕義重利,順水推舟,只顧惜自己榮耀晉升,這能對得起你對我的苦心栽培嗎?
百余字的辯解委婉、懇切,實則是勁氣如龍,綿里藏針:一,你沒有調查研究,撤換李令的決策是個失誤。二,如果將李令與我一并治罪,既不符合圣意,也只能證實你的愛才之心是個虛偽的幌子(隱喻你的人品有問題)。三,你假如要維護尊嚴,一言九鼎,將錯就錯,那就另外派員去吧。
魯亮儕心里清楚,二司昨天已將這件事向田公稟報過了,田公沒有表態,顯然也沒有收回成命的意思(因為摘印事宜非同兒戲,已經寫成給皇帝的奏章送出去了)。在大庭廣眾之中面對怒氣滿腔、亟欲發作的田公,魯亮儕這是站在懸崖上的孤注一擲,也是鷹擊長空的最后一搏。
這里刻畫田公,僅用“面鐵色、乾笑、默然、變色、下階”之類扼要平實的字眼,簡潔利落,便將其復雜、劇烈的心理活動揭示得淋漓盡致。至于兩司的法內含情、恭謹慎微,著意袒護又暗中示意魯亮儕“趕快退下”的微妙眼神,更將大堂上劍拔弩張的森嚴氣氛推至極致——此時此際,端的是石欲破而天欲裂。全文在繁簡搭配與細節運籌上精裁慎減,步入了爐火純青的境地。圍繞魯亮儕,以中牟縣的所見所聞遠相映照,回省之后,以兩司及轅門之上下層層設襯,這些都是簡而又簡,點到即止;可在閻羅殿似的決斷場合,魯亮儕的剖腹辯白則是緊矢密鏃,不惜占用全文五分之一的篇幅。文勢如海外天風,開闔倏忽,充分顯示出“文心雕龍”者卓越的駕馭能力。
魯亮儕“騎驢”進入中牟,面對著陳述內情而潸然泣下的李令時,面對摘印大事,當如何措手呢?文中這樣描述:
魯曰:“吾暍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丈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
漢字的運作是相當神奇的。“丈夫”,本指成年男子或女子配偶,可在前邊加一個“大”字,立馬就跨界升華而成為懷大志、有氣節、敢作敢為的巍然形象了。魯亮儕反復斟酌時脫口而出的“丈夫”二字,當屬“大丈夫”也。大千世界,男兒如沙,這里的“丈夫”只可能是沙里淘金的結果。
在這里,假如沒有“且浴且思”而“擊盆水誓”的細節鋪墊,嗣后的“擲印鏗然”、“怒馬馳去”,會顯得突兀、生硬。“怒馬馳去”,一如云際閃電,又與文之收尾遙相對應,照拂著魯亮儕“武藝尤絕”的巋然身影。騎驢換成騎馬,緩行化為馳去——這類簡單的行色置換,袁枚筆底是一絲不茍的。此文不單使魯亮儕智勇過人的大丈夫形象須眉畢現,田文鏡威嚴的心理素質也悄悄然負重提升,令人敬服。簡約的文字在袁枚筆底化作了勁弩強弓,平射則裂石殺虎,仰射則穿喉墜雕,足見散文細節之巧妙運籌是何等神奇。
讀者或許要問,袁枚與魯亮儕的關系,非尋常吧?袁是杭州人,魯是麻城人,袁枚23歲那年,只是在保定的一間廂房里,從側面窺視過向上峰稟報工作的年已七旬的魯亮儕。動意寫這篇文章,則是“魯公卒已久”(2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緣起是在南京偶然聽到“葛聞橋”其人提說到“摘印”之事,袁枚才決心要寫寫這位“奇男子”的。
全文不過千字,為什么能將仕途波瀾描繪得這樣顯豁、逼真呢?袁枚曾先后在溧水、江浦、沭陽、江寧諸縣當過6年縣令,對于官場上下有著超乎尋常的認識。正因為袁枚與魯亮儕的閱歷、精神暗相契合,既致成寫作的靈感源頭,更是此文得以成功的根柢所系,自然,也寓有作者自抒性情、自度抱負的深長用意。至于后來,有論家認為袁枚的作品致力于閑情逸致,缺少社會內容,恐怕是有些誤讀罷。
袁枚距今,二百年往矣。當今社會,見利疾趨,見害必躲,官癮愈來愈重者大有人在(簡直難以救藥),仕途傾軋排擠的惡習,也未能盡然掃蕩。既然生活中罕有正氣入骨、光明磊落的魯亮儕式的人物,像袁枚這樣的文學巨擘,失卻了植根的土壤,能不銷聲匿跡嗎?
泉臺聚首
日月運行不息,仿佛在暗示著人的靈魂不滅。靈魂不滅,相類似的某些靈魂,總會有個邂逅的時候。有一天,項羽、韓信、岳飛、楊虎城幾位恰巧遇到了一起。披露襟懷的機會著實難得,便各自敘說了在世時無法提及、處于九泉又窩得難熬的一番心里話。
項羽是不謙讓、不客氣的,率先開口:
楚與漢較量時,我是很瞧不起劉邦那小子的,覺得他怎么也不如我。直接與我過招的,主要是韓信、彭越、英布、陳平。
陳平,在魏王咎那里遭受讒言,投奔于我,曾隨我入關破秦,此人品質低劣,轉投劉邦之后,在關鍵時刻離間了我和范增的關系;失去亞父,我也就坐上了沒底的船。英布,土匪出身,因受秦律被鯨,又稱鯨布,后來又叛投劉邦。韓信嘛,早年是個乞食的叫花子,在我這里為治粟都尉,嫌官小,就轉投劉邦。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些人在我手底,沒一個能被我擱在眼里。可他們一伙摸準了我的脾性,我又被“力拔山兮氣蓋世”迷住了眼睛,一時痰迷心竅,硬是被這伙沒名堂的小人活活地捺進了泥坑。烏江邊上,我大呼“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直到今天,我也想不出來我的話有什么破綻。
韓信見項羽提說到自己,擺手制止:
項王呀,事實證明你才是真正的英雄。我因為挫敗了你的“力拔山兮氣蓋世”,自己也就背上了你曾經背過的那個“包袱”。我說過你的弱點是婦人之仁。究竟什么是婦人之仁呢?不就是頭發長見識短,認不準人嘛。而我自己,就沒有跳出婦人之仁的圈子。劉邦與我閑聊,咨詢他能指揮多少兵士作戰,我說不過10萬。他說,你呢?我說,“臣多多益善耳。”他笑了:“你這么大的本事,怎么讓我給擒拿了?”我說:“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君臣之間,推心置腹,開誠布公,彼此把話能說到這么個地步,我韓信還能信不過他嗎?可誰能想到,我最后仍然是栽在他老兄的手底。呂后嘛,我本來是有戒心的,可怎么也沒有想到,我的大恩人蕭何竟與這個女人合謀,騙我進宮。他倆所設的騙局,實際上正是在按照劉邦的意圖暗中行事。你想想,假如劉邦沒有除去我的意思,呂后、蕭何,敢對我下毒手嗎?唉!世人稱我是一代名將,可最后卻翻在這樣一條陰溝里,這叫不叫“婦人之仁”?與其在鐘室被一伙女人長矛戳死,遠不如你老兄那樣縱橫馳騁,有美人、駿馬陪著,揮劍如龍,長歌當哭,戰死于烏江,來得痛快淋漓。
沉穩的岳飛冷靜地看了看項羽、韓信,說道:
二位說的都屬于內斗。我是在對異族作戰不斷取勝的形勢下被召回臨安的。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陷我于死地。難道他就是真正的兇手?十二道金牌催我從前線返回,金牌是高宗下的,我如果違旨,就是不忠。回到臨安,高宗命秦檜處置我,秦檜也的確是兇狠、殘酷。“臣子恨,何時滅?”在世時,我恨的是蹂躪我們國家的胡虜,現在冤沉九泉,你們說我該恨誰呢?
不管怎么說,在這個世界上,看起來事君能致其身的“忠”字是人生的底線。我岳飛倘是不忠,后人還會在山水絕勝的西湖邊修建“岳王廟”以香火供奉嗎?或許含有仰慕忠臣的意思。西湖邊上的名人墓日益增多。1954年,毛澤東在杭州,覺得西湖周圍墳墓太多,是讓活人與鬼為鄰,便對當時的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發話:“除了岳王墓等少數幾個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墳墓外,其他的應該統統遷到別處去。”清明節前一天的下午,在我墓前的花圈叢中,就有毛澤東敬挽的花圈。“忠奸”二字,形同冰炭,從來是不可混淆的。
至于800年后,汪精衛誣蔑我是個不能節制的軍閥,周作人提出秦檜的案應該翻一下。只要中華民族不滅亡,漢奸的這個念頭,永遠是黃粱美夢。
聽“精忠報國”的岳飛說到當代,慣于緘默的楊虎城開口了:
我比毛澤東恰好年長一個月。西安事變前夕,我收到過毛澤東寫的信。蔣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韙,執意要“攘外必先安內”,眼睜睜地要葬送中華民族。西安兵諫時抓了他,本不該放他走,可我聽了周恩來的規勸,還是依從張學良的意愿,釋放了他。一到南京,蔣介石翻回手腕扣押了好意送他的張學良,將我放洋,調離部隊,也就是調虎離山。國民黨軍隊里,我是首倡抗日的將領;抗戰爆發,我一心想回國抗日;返回到香港時,周恩來派張云逸趕來規勸我,千萬不能到南昌去見蔣介石。我思量,大敵當前,全面抗戰,國家正急于用人,全國上下都呼吁蔣介石釋放張學良,無論如何,他蔣介石總不至于不讓我上前線抗日吧。事實證明,我的想法非常幼稚——蔣介石將我關押了12年,逃往臺灣之前夕,殺了我全家四口,連妻子、兒子、小女兒一塊殺害。而蔣介石呢?是因為西安兵諫,他才轉向于抗日;由于抗日,他蔣介石才被譽之為民族英雄。我家四口人的鮮血,倒是為蔣介石染成了一頂“民族英雄”的紅帽子!
我在世時,斯世列強,無不認為中國是一塊肥肉。今天在座的各位和我一樣,僅僅是肉里的幾塊堅硬的骨頭而已。我的意思,一個人忠于民族、國家,這是天經地義的,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如果將他的個人利益、私家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整個國家只是為他提供服務的工具,我們這些人,還要不要忠于這樣的統治者呢?“忠”字固然崇高,難道“愚忠”也屬于崇高的范疇?
項羽一直昂著傲氣的頭顱,好像沒聽到楊虎城在說些什么,韓信、岳飛,神情專注,聽罷,陷入了沉思……
“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羅貫中語)常人以為,凡被譽為英雄者,個個都是死得其所,死而無憾。實際情況呢?恰恰是:塵世知音少,幽泉暗恨多。
生命不可能逆轉,然而,造物主如果轉變思路,拆除陰陽之藩籬,人不管生前死后,言論無礙,有話盡可以和盤托出;倘真是那樣,眾多的英雄人物里,有些則很可能要脫下“英雄”的外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