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立秋《肉粽子》散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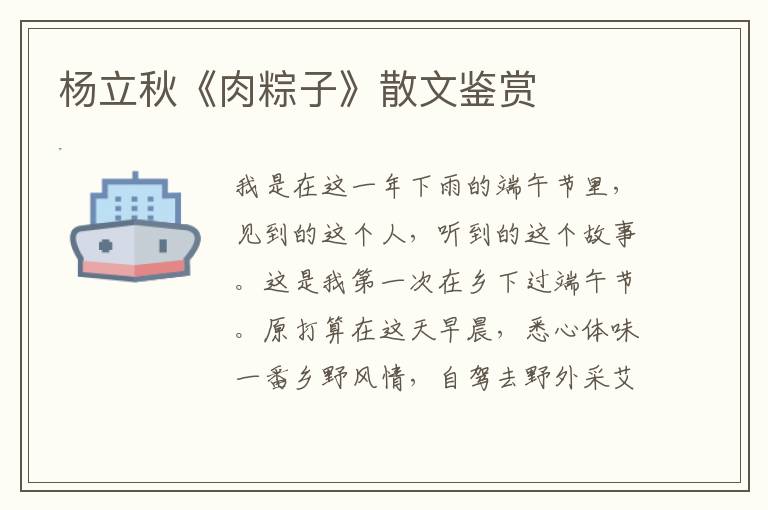
我是在這一年下雨的端午節里,見到的這個人,聽到的這個故事。這是我第一次在鄉下過端午節。原打算在這天早晨,悉心體味一番鄉野風情,自駕去野外采艾蒿和吃野餐的,可是,綿綿細雨,像絮絮叨叨沒完沒了傾訴的怨婦,絲毫沒有停息的意思。
我看著頭一天晚上在鎮上買的那堆吃喝的東西,再望望灰蒙蒙的天際,只好打消了自駕野游的計劃。心中不免有些失落。
不能出行,但習俗照舊。我隨同二姨一家和居住在前院也趕來一同過節的表哥,房前屋后掛完了彩紙葫蘆,相互間戴上了五彩線,就擺好桌子,準備端午節的早餐。
當我們把粽子和煮熟的雞鴨鵝蛋滿滿地擺上桌子之后,院門外忽然響起一陣摩托聲,然后,在摩托聲的戛然而止中,一個人閃進院中。只見他把一個透著粽子影的方便兜遞到表哥手中,沒說幾句話就匆匆離去了。我還頭一次看見這樣送東西的,就像是在雨中他特意趕著一份使命而來似的。
表哥告訴我,那人曾是他的戰友。因為是南方風味的肉餡粽子,所以,特意送來讓我們嘗嘗。
因為是葷性,二姨給加了溫,當我剝開綠色的粽葉,才發現它并不像大棗和葡萄干粽子那樣含蓄地露出“頭臉兒”,而是,藏而不露。我試探性地順著棕角咬一口,就露出了肉粉色的肉團兒,不是甜的,而是咸味的。只見一絲油亮的湯,緩緩的,浸潤似的閃現出來。只是閃現,而不是流淌。細細品嘗中,我感到香而不膩、咸淡適中。這香,遠遠超過包子和餃子餡的香。因為北方人很少包肉餡粽子。所以,我還是第一次吃。
也正是通過這粽子,我才從表哥娓娓的講述中,得知了一些關于他這位戰友的故事。
表哥的戰友叫高發,村人們都叫他發子。他當兵四年就退伍回農村了。在部隊時,他很憨厚,憨厚得似乎有些木訥,但實質卻很機靈。在部隊的各項演練中,成績都排前位。他還冒生命危險救過一個戰友。那是在一次實彈演習中,那個戰友不知怎么搞的,手榴彈拉了弦之后,竟沒有及時甩出去,而是落在了腳下。望著呲呲冒煙的手榴彈,那個戰友傻了似的不知所措。這時,發子忽地沖上前去,幾乎在手榴彈爆炸時,把它扔了出去。戰友得救了,可是,他卻失去了兩根手指。他得了嘉獎,立了功,也落下了殘疾。
四年后,他退伍回農村了。那時家里很窮,哥四個都在農村務農,他在家排行老三。那時,只有大哥草草成了家,二哥、弟弟和妹妹都窩在家中,過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父親青光眼,母親后來患上了中風,口眼歪斜,步履蹣跚,貧困的家里,更是捉襟見肘。面對貧困的家,他是這個被稱作窩棚的小村子里,第一個遠離故土奔赴南方打工的男人。他一走,就是十六年——這十六年里,他都經歷了怎樣的艱辛和不易,又都經歷了怎樣的生活磨難和辛酸,無人知曉。村里人只是知道從他走后,家里就像干涸的河床,漸漸有了濕潤的樣子。過了幾年,家里翻蓋了房子,再后來,二哥、弟弟和妹妹也都相繼結婚成家。他是在他父親去世那年奔喪趕回來的,并且還帶著一個女人。趕回來后,就再也沒有離開過這村子。起初,村人們以為一向孝順的發子,是在為父守孝在家,可是,一年兩年過去了,他還是未走。并且,帶回來的那個女人,也一直沒走。兩個人在他父親后院的那處房子里出出進進共同生活。可是,既沒看到他們結婚,也沒看到他們的孩子,樣子平淡而又親切,儼然就是一對夫妻。然而,這樣的夫妻模式,著實讓村里人猜疑,一個大謎團在村人們的心頭凝聚著,并且被一些長舌婦們編成好多的版本,成為村人們飯后拉呱、納涼時的談資。
發子回來一年多后,除了種地,還不張不揚地干起兩個營生。一個是在鎮上組織起一個包工隊,專門承攬大大小小的建筑施工。另外,還在距離窩棚村十二里路的叫黑魚汀的地方,承包一個小型魚塘。他把哥哥弟弟都給拉巴進來,使他們的日子也日漸一日地好轉起來。他讓妹妹專門伺候已經半癱在炕的老母,每月,由他付給妹妹相當于城里保姆工資的報酬。而他帶回來的女人,則待在家中料理家務、整花弄草。他覺得她能隨他到農村來,已經夠委屈她了,所以,絕不能讓自己的女人風吹雨淋、成為村婦。
這個女人很少走出院門,忙完家務,時常會默默地坐在寬敞、充滿田園韻味的院落里,望著悠遠的天空凝神,好像在思念遙遠的南方故鄉。有一次,當發子看到她偷偷抹淚時,心疼了,也心軟了,就違心地勸她回故鄉,回不回來,隨她心愿。可是,這女人卻使勁地搖著頭,說了一句讓發子能感動一輩子的話:你在哪,我就在哪,你在哪,哪就是家!這回該發子流淚了。沒過幾天,發子就買了當時村里僅他才有的電腦,讓他的女人在這方窗口里,看外面的世界,看自己的故鄉。
在發子從南方回村的第二年里,表哥退役返鄉的。因為表哥是軍官退役,所以,在村人們眼中,就絕不是發子的境遇了,多少帶了點“榮歸故里”的味道。在農村,每月有四千多塊的退役金領著,出行有轎車開著,那是很讓村人們艷羨的事情。
因為發子曾與表哥是戰友,是他手下的兵,在整個窩棚村里,他們倆又是不同于村人的同村人,所以,兩個人就成了一個階層。在發小、戰友、同類的基礎上,就成了常來常往的好朋友。盡管在表哥面前,發子也時而現出自卑的樣子,但他畢竟也是到大城市打拼、生活了那么多年的人,也多少混出個樣來,從見過世面的角度看,又絕對在表哥之上,所以這樣一想,發子也就平衡了些,也就覺得在這個村子里,他們倆是唯一可以平起平坐的人。
聽表哥說,發子帶回的女人小巧玲瓏,長相俊俏。并且有文化有素養,干凈利落。家里被她營造打理得很有情調與品位。而發子,也勤勞能干,外面被他弄得也田園味十足。兩個人和諧默契,把二人世界過得有聲有色,把城鄉生活結合得妙趣橫生。表哥說,發子和那女人,是領了證的合法夫妻,但發子寧愿讓人們去瞎猜瞎想,也不向誰出示,好像他一點也不介意誰,但他介意表哥,他只讓表哥看了結婚證。那女人年長發子幾歲,但外觀看,絕對看不出,倒像是比發子小。女人叫郎琳,一個很好聽的名字,這倒與她的嬌小和漂亮挺吻合。
關于發子背井離鄉的十六年,他從未向表哥陳述過,只是在一次與表哥喝酒時,沉沉地說了一句:十六年里,我在外受的苦、遭的罪,是有的人兩輩子都不曾受過的——談及到他的女人時,他紅著眼圈,也只是說了一句:她是在我最困頓最低谷時走近我的,我們有太多太多的故事,我到任何時候,都不能辜負了她——然后,一口酒,就把什么都壓下去了。
在表哥退役之前的發子的許多事情,都是發子后來幽幽地向表哥傾吐的。表哥只是傾聽,絕不多問,發子說到哪,他就聽到哪。
發子的女人,不僅乖巧,還會做一手好飯菜。她不僅能做些具有南方口味的飯菜,北方的飯菜也做得很好吃。發子時常約表哥到他們家去喝喝酒,聊聊天,表哥過意不去,時常也拎些熟食或啤酒什么的。發子也唯恐表哥如此這般,于是,經常找些幫著做點什么事的借口,讓表哥過去。
在發子的院落里,有一個誰家都沒有的吊床,吊床掛于兩棵楊樹之間。沒事的時候,發子的女人就悠悠地坐在吊床上,要么看書,要么寫點什么東西,要么就微閉著眼睛,似睡非睡。大多的時候,吊床是空著的,風中,輕輕地搖蕩著、擺動著,像在水中飄動的小船。
在這個窩棚村子里,每家的院門,整日都是大敞著的,所以,這個吊床,就成了吸引孩子們的磁場,每天,都有好多孩子無所顧忌地走進來,大大方方地坐上去。他們能夠這樣坦然,是因為發子的女人從來沒有冷臉拒絕過,更沒有攆過,倒是笑容可掬地招呼著,并幫著扶上去。她雖然不與村人們怎么聯系,但她卻愿意聯絡這些孩子,她經常給前來的孩子講安徒生和格林的童話故事,教他們認字,讓他們做成語接龍。孩子們也都愿意聽,樂于學,更因為,有吊床可以打悠悠。久而久之,村人們對發子的女人有了點好感,雖然覺得不可接近,但又覺得和藹可親。不知是誰推薦的,還是消息不脛而走,此事竟傳到了窩棚小學校長那里。有一天,這個只有六十名學生的小學校長,竟親自登門拜訪,聘請發子的女人去當語文老師。發子的女人先是拒絕了。后來,一些男男女女的村人再加上嘰嘰喳喳的孩子登門助陣協聘,發子的女人才答應了下來,從此,她就成了窩棚村建功小學的語文老師。直到現在——
其實,關于發子和發子的女人的故事,我很有興趣能知道得更多一些。可是,就像包在粽子里的肉餡,畢竟有限,畢竟不可多得。我想,一個南方的城里女人,能夠愛上一個農村的且又廢掉兩根手指的打工男人,并且能隨他來到農村,嫁他為妻,這其中,一定有著非凡的經歷和情結,一定有著太多的不易和曲折,同時,也一定有著太多的不被人理解與認同的觀念。但無論怎樣,我覺得,感情與愛是最重要的。當感情與愛同在的時候,一切,也就都不在話下了!
發子的女人包的肉餡粽子很好吃。我在慢慢品味的同時,也在悉心地品味著她和發子的故事。
當我們決定第二天駕車野游時,我不假思索地建議道:請發子和發子的女人一同去吧。
表哥眨眨眼睛,微笑道:就是因為肉餡粽子?
我說,是的,因為肉餡的粽子很好吃,肉粽包裹的故事,更耐人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