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羅曼·羅蘭《鼠籠》抒情散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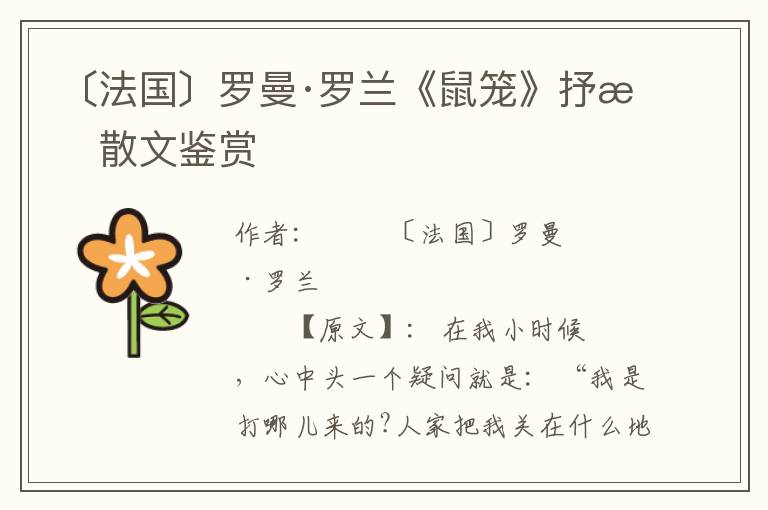
作者: 〔法國〕羅曼·羅蘭
【原文】:
在我小時候,心中頭一個疑問就是:
“我是打哪兒來的?人家把我關在什么地方了?……”
我出生在一個小康的中產家庭里,周圍有愛我的親人,這個家庭處在一個景物宜人的地方,到后來我對那地方也曾回味過,也曾借著我考拉(1)的聲音贊頌過那種喜洋洋的土風。
我怎么會在剛踏進人生的小小年紀,頭一個最強烈最持久的感觸就是——又暖昧,又煩亂,有時候頑強,有時候忍受的:
“我是一個囚犯!”
佛郎素瓦一世(2),一走進我們克拉美西(3)圣·馬丹古寺那個不大穩固的教堂的時候,說過這樣的話:“這可真是個漂亮的鼠籠!”——(這是根據傳說)——我當時就是在鼠籠里的。
最先是眼底的印象:我小孩子目光所及的頭一個境界。一所院子,相當的寬廣,鋪砌著石頭,當中有一塊花畦,房子的三堵墻圍繞著三面,墻對我顯得非常的高。第四面是街道和對街的屋宇,這些都和我們隔著一道運河。雖然這方方的院子是坐落在臨水的平臺之上,可是從幽禁在底層屋子里的孩子看來,它就象是動物園圍墻腳下的一個深坑。
一個最切身的印象是童年的疾病和嬌弱的體質。雖然我有健康的父母,富于抵抗力的血統——(姓羅蘭和姓古洛的都是高大,骨骼外露,沒有生理的缺陷,天生耗不完的精力,使得他們一輩子硬朗、勤快、都能夠活到高年。我的外祖父母滿不在乎地活到八十以上,我寫文章的時候,我八十八歲的老父正在那里興致勃勃地澆他的花園)。他們的身子骨在什么情形下都經得住疲乏和勞碌生活的考驗,我的身子骨也和他們沒什么兩樣,可是,在我襁褓時期卻出了件意外的事,一直影響了我的一生,給我帶來痛苦的后果。那是因為在我未滿周歲的時候,一個年輕女仆一時粗心,把我丟在冬天的寒氣里忘了管我,這件事險些送了我的性命,而且給我種下支氣管衰弱和氣喘的毛病,使得我受累終身,人家從我的作品里,常常可以看到那些“呼吸方面的”詞藻:“窒悶”,——“敞開的窗戶”,——“戶外的自由空氣”,——“英雄的氣息”,——這些都是無心的,進發出來的,好象是飛翔受了挫折時的掙扎。這只鳥在撲著翅膀,要不就是胸脯受了傷,困在那里,滿腹焦躁地縮作了一團。
最后是精神方面的印象,強烈而又深入心脾。我在十歲以前,一直是被死的念頭包圍著的。——死神到過我的家,在我身旁擊倒了我一個年紀很小的妹妹(我下文還要說到她)。她的影子常駐在我們家里沒有消散。摯情的母親,對這件傷心事總是不能淡忘,如醉如癡地追想著那個夭殤的孩子。而我呢,我眼看著她沒有兩天就消失了,又老看著我母親那么一心一意地牽記著她,死的念頭始終在圍著我打轉,盡管在我那個年紀是多么心不在焉,只想著溜掉,可是恰恰因為我十歲或十二歲以前一直是多災多病的,所以就更加暴露了弱點,使得那個念頭容易乘虛而入了。接二連三的傷風、支氣管炎、喉病、難止的鼻血,把我對生活的熱勁斷送得一干二凈。我在小床上反復叫著:
“我不要死啊!”
而我母親淚汪汪地抱緊了我,回答說:
“不會的。我的孩子,善心的上帝不會連你也從我手里奪去的。”
我對這話只是半信半疑:因為要說到上帝的話,我只知道從我人生第一步起他就濫用過他的威力,別的我還知道什么呢?當時我還不懂,我對于上帝的最清楚的見解,也就是園丁對他主人的見解:
老實人說:這都是君王的把戲。
…………
向那些為王的求助,你就成了大大的傻子。
你永遠也別讓他們走進你的園地。
古老的房屋,呼吸困難的胸膛,死亡兇兆的包圍,在這三重監獄之中,我幼年時期初步的自覺,仰仗著母親惴惴不安的愛護而萌動起來。脆弱的植物,和庭前墻角抽華吐萼的紫藤與茄花正象是同科的姊妹。朝榮夕萎的唇瓣上所發出的濃香,混合著呆滯的運河里的膩人氣息。這兩種花在土地里植根,朝著光明舒展,小小的囚徒也象她們一樣,帶著盲目的可是半眠半醒的本能,在空中暗自摸素,要找一條無形的出路來使自己脫逃。
最近的出路是那道暗沉沉的運河,它沿著平臺的矮墻,我憑在墻頭。河水渾膩而青綠,沒有波紋,河上載著深凹的重船。瘦弱的纖夫幾乎要傾著全身的重量來撲到地上。船欄桿上纜繩的磨擦隱約可聞。一座轉橋扎鑠作聲,緩緩地旋動開來。船艙的小天窗上擺著一盆石榴紅,從船艙里,一縷青煙在冉冉上升。艙口坐著一個女人,默默無語,縫補著活計,這時徐徐抬起頭來,朝著我漠然看了一眼,船過去了……而我呢,我居在墻頭,看見墻和我一同過去。我們把那只船撇在后頭了,我們漂開了。越漂越遠,到了無垠的廣漠。沒有一絲振蕩,沒有一絲簸動,悠悠蕩蕩的,仿佛我們也象黑夜的天空一樣,老是這么著,在永恒里自在滑翔。隨后我們又發覺了,墻和我,還是在原來的地方做著夢。船卻走了。它到得了目的地嗎?另一只船接著又過來了。仿佛還是先前的那一只……
另外一條出路,更加自由而沒有障礙:就是太空。——小孩子常常仰起臉來,望著飄忽的云,聽著呢喃的燕語。一大片一大片的白云,在孩子的心目中都幻成光怪陸離的建筑物(那是他初次著手的雕塑,小小的創作是把空氣當黏土來塑造的)。至于那些兇險的密云,法蘭西中部夾著霹雷的傾盆暴雨,那就更不用說了!風云起處,來了害人的對頭,造物主雙眉緊皺,向荏弱的小囚徒重新關起天上的窗板……可是救星來了,就象是女巫的手指為我打開那曠野上的天窗……聽!鐘聲響了,這正是圣·馬丹寺的鐘聲!在《約翰·克利斯朵夫》的開頭幾頁,也有這鐘聲在歌唱著。我未覺醒的心靈里,早就銘記住它的音樂了。在我的屋頂上面,這些鐘聲從古老大教堂透雕的鐘樓里面裊裊而出,但這些教堂的歌鳥卻沒有使我想到教堂。以后我再說說我和教堂中神的關系。我們的關系是冷淡的,客氣的,疏遠的。盡管我認真努力,我也沒法和神祗接近。神懂得我怎樣地找過他啊!可是懂得我心事的神決不是那個神。這是向我傾聽的神——為了要這個神向我傾聽,我才特意把他創造出來,在我的一生中,我始終不斷地向他皈依,這個神是在翱翔著的歌鳥身上的,也就是鐘聲,而且是在太空里的。不是圣·馬丹寺高據在雕飾的拱門之上,踡縮在他鼠籠之內的那個上帝,而是“自由之神”。——自然,在那個時期,我對他翅膀的大小是毫無所知的。我只聽見那兩個翅膀在寥廓的高空中鼓動。可是我卻不斷定它們是否比那些白云更為真實。它們是我一個懷鄉夢,這個懷鄉夢為我打開一線天光,轉瞬就匆匆飛逝,讓籠門又在我生命的暗窟上關閉了……很久很久以后,(這情形留待將來再說吧!)我爬,我推,我用前額來頂開那個籠門;在空闊的海面上,我又找到了那鐘聲的余韻。但是直到青春期為止,我始終是在那個緊閉的暗窟里摸索著——我指的是勃艮涅(4)那個又大又美的暗窟,那暗窟就象是一所地窖,酒桶排列成行,桶里裝著美酒,桶上結著蛛網。在那里面,除了一個女人,別的人都是逍遙自在的,我聽到他們的笑聲,正如我們本鄉人那么會笑一樣。我并不是瞧不起這種歡笑和豪飲……可是,窟外有的是陽光啊!……那真的是陽光嗎?(但愿我能夠知道就好了!)要不就是夜景吧?……既然那些身強力壯的人沒有一個想要離開,我知道自己軟弱,也就失掉了勇氣,留守在我的一隅。
我十六七歲讀到《哈姆菜特》的時候,那些親切的詞句在我那暗窟的拱頂下引起了怎樣的共鳴啊!
“我的好朋友,你們什么事得罪了命運,她才把你們送進這監獄里來了?”
“監獄里!”
“丹麥就是一所監獄。”
“那么整個世界也是一所監獄。”
“一所大的監獄,里面有許多監房,暗室,地牢……”
當真的,再往下讀,一句話,一句神咒般的話打開了我
無窮的希望:
“上帝啊!就是把我關在一個桃胡殼里,我也會把自己當作奄有無限空間的君王。”
這就是我一生的歷史。
我一回顧那遙遠的年代,最使我驚異的就是“自我”的龐大。從剛離開混沌狀態的那一刻起,它就勃然滋長,象是一朵大大的漫過池面的蓮花。小孩子是不能象我現在這樣的來估計它大小的,因為只有在人生的壁壘上碰過之后,對自我的大小才會有些數目;高舉在天水之間的蓮花,本來是鋪展的,不可限量的,這座壁壘卻逼得它把紅衣掩閉起來。隨著身體的生長,在許多歲月中受盡了反復的考驗,這樣一來,身體是越來越大了,自我卻越來越小了。只有在青年期快完的時候,自我才完全控制住它的軀殼。可是這種生命初期充塞于天地之間的豐富飽滿,以后就一去而不可再得了。一個嬰兒的精神生命和他細小的身材是不相稱的。但是難得有幾道電光,射進我遠在天邊的朦朧的記憶,還使我看到巨大的自我,據在小小的生命里南面稱王。
以下是這些光芒中的一道,——不是離我最遠的,(還有別的光芒照到我三歲的時候,甚至更旱,)而是最深入我心的。
我年方五歲。我有個妹妹,是第一個叫瑪德璘的,她比我小兩歲。那時是一八七一年,六月底,我們隨著母親在阿爾卡旬海濱。幾天以來,這孩子一直是懶洋洋的,她的精神已經萎頓下去。一個庸醫不曉得去診斷出她潛伏的病根,我們也沒想到過不上幾天她就會離開我們了。有一次,她來到了海邊:那天刮著風,有太陽,我和別的孩子在那里玩著;可是她沒有參加,她坐在沙土上面的一把小柳件椅上,一言不發,看著男孩子們在爭爭吵吵,鬧鬧嚷嚷。我沒有別的孩子那么強壯,被人家把我排擠出來,撅著嘴,抽抽咽咽的,自然而然走到這女孩子的腳邊,——那雙懸著的小腳還夠不著地;——我把臉靠著她裙子,一面哼哼唧唧,一面撥弄著沙地。于是她用小手輕輕地撫弄著我的頭發,向我說:
“我可憐的小曼曼……”
我的眼淚收住了,我也不知是受了什么打動。我朝她抬起眼來;我看見她又憐愛又悽愴的臉。當時的情形不過如此。過了一會兒,我對這些就再也不想看了。——可是,我要想它一輩子哪……
這個三歲的小姑娘,她那略微大了些的臉龐,她淡藍的眼珠,她又長又美的金發,那是我母親引以自豪的,——她藍白兩色交織的斜方裙子,上部敞著露出雪白的襯衫,她懸宕著的小腿,腿上穿著粗白襪子和圓頭羔皮鞋……她充滿了憐憫的聲音,她放在我頭上的柔軟的手,她惆悵的眼光……這些都直透進我的心坎。剎那間我仿佛受到了某一種啟示,那是從比她更遠的地方來的,是什么呢?我也說不上來。小動物什么都不擺在心上,受了別的吸引,就把這些忘得一干二凈了。
我們回到了住所。太陽在海面上落了下去。那一天正是小瑪德璘在世的最后一天。咽喉炎當夜就把她帶走了。在旅館的那間窒悶的屋子里,她臨死掙扎了六個鐘頭。人家把我和她隔開了。我所看到的只是蓋緊的棺材,和我母親從她頭上剪下來的一綹金發。母親瘋了似的,連哭帶喊,不許別人把她抬走……
過了幾天,也許就是第二天,我們回家去了。現在是眼前還看得見那個載著我們的火車廂;那些人,那些風景,那些使我惶恐不安的隧道,整個占滿了我的心思。根本就沒什么悲哀。離開那個我所不喜歡的海,我心里沒有一點遺憾;我也離開了在那個海邊發生的不愉快的事;我把一切都撇在腦后,一切似乎都煙消云散了……
但是那個坐在海邊的小姑娘,她的手,她的聲音,她的眼光,——從來也沒離開過我。好象這些都鏤刻進我的肌骨似的!那時她不到四歲,我也還不到五歲,不知不覺的,兩顆心在這次永訣中融合在一起了。我們兩個是超出時間之外的。我們從那時起,緊靠著成長起來,彼此真是寸步不離。因為,差不多每天晚上臨睡之前,我總要向她吐訴出一段還不成熟的思想。而且我還從她身上認出了“啟示”,她就是傳達了啟示的脆弱的使者,——這啟示就是:在她從塵世過境中的那個通靈的一剎那間,純凈的結合使我倆融為一體,這個結合在我心里引起的神圣的感覺:——也就是人類的“同情”。
在我所著的《女朋友們》的卷尾,當葛拉齊亞在客廳大鏡子里出現的時候,可以看到我對這道光芒的淡薄的追憶。
(陳西禾 譯)
【作者簡介】:
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1866——1944) 法國作家,音樂學家、社會活動家,廣泛從事小說、傳記、戲劇、評論等創作,是一位具有世界性影響的藝術家。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母與子》,傳記《米開朗琪羅傳》、《貝多芬傳》等。《鼠籠》選自他的回憶文集《內心旅程》。
【鑒賞】:
一提到童年,總會使人想起明媚的陽光,絢麗的鮮花,母親的笑臉以及月光下的搖籃,童年總是人生最美好的年華。然而《鼠籠》展示給我們的卻是作者度過的另外一種截然不同于我們的記憶的童年景象:高墻、深院鎖住他那活潑敏感的童心,疾病、死亡纏繞在他尚不該知曉殘酷的年齡。筆觸哀婉細膩,氣氛沉郁滯重。
讀后給人印象是深的,首先是籠罩在文中的一種深沉哀婉的情調。他的童年是“在鼠籠里的”,這使他有種作“囚犯”的感覺;生活在三面是高墻一面是運河的封閉空間內,幼小的心靈感覺到了被“幽禁”,而那“脆弱的植物”、“渾膩而青綠”的運河水,“深凹的重船”、“瘦弱的纖夫”、“默默無語”的冷漠女人以及時時包圍著他的對于死亡的敏感和恐懼,無不給文章的總體畫面增加著沉重凝暗的色彩。
但是作者并不消極悲觀也不憤世嫉俗,而是表現出以一種天生的不可抑制的人性力量擺脫精神桎梏、證實人道精神的不可禁錮的寬闊胸懷。把幼小的心靈因為一艘船、一片云、一陣燕語或鐘聲而激蕩,從而產生了對于自由的向往和追求,這是作者一生精神生活的開始,他在令人窒息的生存環境中依然充滿了叛逆的精神,這首先表現在他對于上帝的諷刺挖苦:“我只知道從我人生第一步起他就濫用過他的威力”,否定了上帝的神秘力量,張揚了人的人格力量,用莎劇中的一句臺詞概括了他一生的精神追求:“上帝啊!就是把我關在一個胡桃殼里,我也會把自己當作奄有無限空間的君王。”其次還表現在尋找人道主義思想感情的萌發契機上。妹妹的死一方面使他過早地體驗到了死亡的可怕,另一方面也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死亡,獲得了更高層次的人生體驗:他得以明白了蘊藏在自己內心深處的一種深厚的神圣感情——人道主義的感情。
“鼠籠”在藝術上體現了典型的大家手法。遣詞造句、抒情寫景、創造意境無不深含寓意,寓有哲理,感情真摯自然,緊緊圍繞主題結構布局卻又毫無雕琢之痕跡,非功力深厚不足以至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