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延梅《斯人已去,江河長流》散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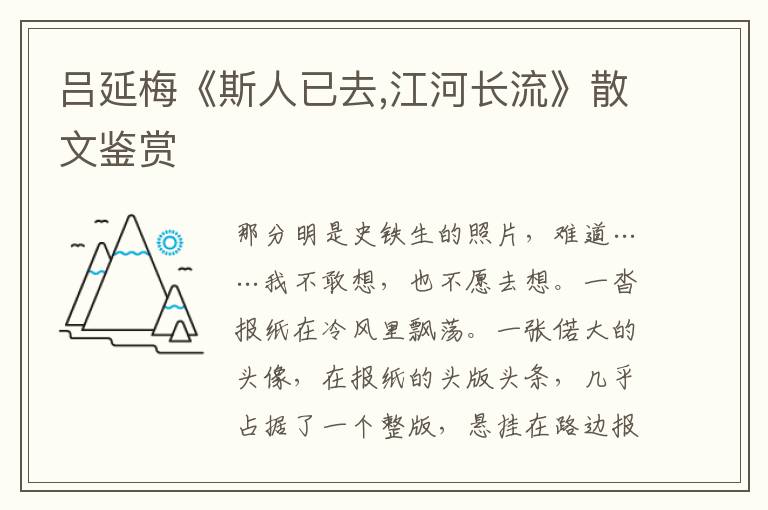
那分明是史鐵生的照片,難道……我不敢想,也不愿去想。一沓報紙在冷風里飄蕩。一張偌大的頭像,在報紙的頭版頭條,幾乎占據了一個整版,懸掛在路邊報亭的正中間,一絲溫和憨厚的笑容,掛在那張看著令人踏實的方正的臉上,他的視線向著斜前方,仿佛憧憬著寒冬里明朝升起的暖陽。熟悉的東西總能夠觸動我,隔著一條街,我瞄了一眼,一種不祥的預感莫名其妙地籠罩著我。我迫不及待地躲閃著車輛,三兩步橫跨馬路,在報亭前,呆呆地站了半天,這分明是史鐵生!在他60歲生日的前一天凌晨,突發腦溢血逝世。我默默地離開那里,不小心在馬路牙子上踩翻了一腳,我打了個趔趄,肚腹里開始翻江倒海,我的腦袋開始轟響,腳下有點軟綿綿的。
史鐵生是我最鐘愛的作家。鐘愛一個作家的作品和鐘愛一個人的感覺是一樣的。即使沒謀過面,只要看到他的文字,體味著字里行間的溫度,身外的一切就遠了,整個世界是安靜的,心里熨帖著,沉浸在一種飽滿又莫名的情緒里,久久不愿出來。
《我與地壇》是我讀到的史鐵生先生的第一篇文章。那天夜里,我又一次失眠。我的清醒在深夜里恣意,在別人的酣眠里,睜著痛苦的眼。害怕影響家人休息,一個人坐在角落里看書。翻閱一本雜志,不起眼的一篇文章攫住了我的眼球。我瀏覽了一遍,又迫切地仔細讀了一遍。四周的黑夜,只有局促著我的墻壁是光亮的,心里驅不走的黑暗,曾令我窒息,眼前的這些普通的字符,為我勾畫了一個異常明亮的世界,它漸漸驅散氤氳于心的塵霾,引領我走出那片茫茫的黑暗之澤。
我突然感覺到,在這個無情的世界上,有一顆苦難的靈魂離我很近很近,似乎伸出手就能觸摸到他。我掃了一眼作者的名字,并不熟悉,當時也就沒記住他的名字。英雄不問出身,我認為好文章也不問出處。
緣分是上天安排的,你不用刻意去等它,它就在你生命的某一天與你不期而遇。幾個月之后,我在語文教科書上發現了這一篇。我要用一星期的時間去研究它,之后給高一的學生上一堂欣賞課。這時候它的名字——《我與地壇》已深深地烙在我心里,史鐵生這個名字與我也親近起來。因為備課,了解了他的人生際遇。北京知青下鄉,二十歲突然雙腿殘疾,后來在街道的工廠里做工,業余創作小說。他曾經搖著輪椅在地壇里呆了十五年,也曾幾次自殺未遂。地壇里的白晝和黑夜,建筑與行人,一草一木,一葉一蟲,以及疼愛他又不知所措而耗盡心力的母親,這一切在他眼里,也在他心里,陪伴著他,久而久之,給了他神性的啟示:“一個人,出生了,這就不再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而只是上帝交給他的一個事實;上帝在交給我們這件事實的時候,已經順便保證了它的結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
一個星期的時間,我在這篇文字里徜徉,與史鐵生在地壇的角角落落里輾轉,看古殿檐頭浮夸的琉璃,凝視淡褪了朱紅的門壁,走過那一段段坍圮了的高墻和散落的玉砌雕欄,在愈見蒼幽的老柏樹下,陪伴茂盛得自在坦蕩的野草荒藤。正如史鐵生在文中所說:“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這樣一個寧靜的去處,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我總覺得,在我人生最落魄的時候,這些文字走進我的生命里,不正是上帝對我的救贖嗎?
一周之后,這些文字仿佛是流淌在我骨子里的血液。課堂上,在少年人澄澈的目光里,我帶領他們在史鐵生的筆下,在地壇里,享受著生命的精彩:蜂兒舞成了一朵小霧停在半空;搖頭晃腦的螞蟻捋著觸須猛然想透了什么;瓢蟲爬來爬去,忽而又飛走了;蟬蛻寂寞成空屋子;草葉上滾動的露珠,轟然墜地摔開萬道金光。滿園子的繁華充滿生機,所有卑微的生命都自由自在地自我存在。荒蕪的園子并不荒敗,這給了作者生命的啟迪:再卑微的生命也有活著的權利和自由,再不堪的處境也得坦然面對。他的文字是暗夜里的一道強光,讓我清楚:我遇到的挫折是微不足道的,這個世界上比我不幸的大有人在,關鍵是如何面對無常的命運,災難面前,怎樣昂起不屈的頭顱。
后來又學習了史鐵生的小說《命若琴弦》:蒼茫的深山之中,兩個瞎子,一老一少,他們穿梭于各個村落之間,以拉三弦說書為生。老瞎子的師傅曾經告訴他琴槽里有一張治療失明的藥方,只有彈斷一千根琴弦才能把藥方取出來。于是,老瞎子盡心盡力地彈斷一根又一根……終于有一天大功告成了,他欣喜激動地打開琴槽,結果那里面竟是一張無字的白紙……老瞎子告訴小瞎子,彈斷一千二百根才能取出藥方,他希望小瞎子永遠扯緊歡跳的琴弦,不必去看那張無字的白紙。老瞎子的一輩子都被那虛設的目標拉緊,于是,生活才有了生氣,重要的是他在繃緊的過程中得到了快樂。
海明威說:“世界是美好的,值得我們為它奮斗。”我們就像那個在黑暗里憧憬著光明的瞎子,苦難是豐富而寬廣的,有了這個虛設的目標,享受充實的過程就足夠了。史鐵生曾說:“左右蒼茫時,總也得有條路走,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筆去找。”史鐵生直面殘疾與病痛,徹悟了生命,對宿命沒有抱怨。他的作品里透露出殘缺的完美,更給人悲劇的震撼力量。
一向健康的母親早早地去世了,而殘疾的兒子卻勇敢地活了下來。史鐵生在《合歡樹》中寫到:“母親那時已不年輕,為了我的腿,她頭上開始有了白發。” 為了給兒子治病,母親顯示出不屈不撓的精神與信念。“到處找大夫,打聽偏方,花很多錢。她倒總能找來些稀奇古怪的藥,讓我吃,讓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最后母親終于意識到無法通過各種努力治愈兒子的雙腿,她平靜地接受了這一殘酷而無情的現實。為了激勵兒子在生活中重新站立起來,“她到處去給我借書,頂著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電影,像過去給我找大夫,打聽偏方那樣,抱了希望”。母親的無私無怨、堅強執著、寬厚仁慈鼓舞著史鐵生在文學的路上走下去。他小說獲獎之后,面對眾多登門訪問的記者,準備的套話說來說去覺得心煩,就搖著輪椅,坐在地壇安靜的樹林里,想:上帝為什么早早地召母親回去呢?迷迷糊糊的,聽見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作者的心得到一點安慰,默默地看見風正在樹林里吹過。母親親手栽在窗下的合歡樹,就是母親活在人世的見證,兒子的綿綿情思,將永遠與之“合歡”。
史鐵生在散文《宿命的寫作》里提到他寫作的原因,首先是謀生,其次是為價值實現,然后還有更多的什么,一是不僵死在現實里,因此二要維護和壯大人的夢想,尤其是夢想的能力。他把寫作當成職業,以它為光榮,以它為信仰,更相信寫作是一種命運。在《“忘了”與“別忘了”》中談到他的殘疾時,他說殘疾人假如有陰云的話,也是他敏感的產物。試想這敏感若多起來,誰跟他說話能不提心吊膽般戒備呢?這樣下去哪還有平等可言呢?他認為人道主義不僅意味著殘疾人該有人的權利,還意味著他們必須理直氣壯地去爭取,倘自己先膽怯了,則天上掉餡餅的機會微乎其微。他主張:讓我們的肉體不妨繼續帶著殘疾,但要讓我們的精神像健康人一樣與世界相處。
后來,斷斷續續讀了一些史鐵生的作品。又了解到他的身體狀況,患尿毒癥,需要一周三次去醫院做腎透析。他調侃自己:職業是生病,業余是寫作。肉身的史鐵生,要承受外人無法想象的生存之痛、生命之痛。
讀他的文章,每一篇我都能感覺到文字背后的沉重——生命難以承受之重。于是,又害怕讀他的文章。
史鐵生去世后,耿耿于懷的痛惜之情又促使我讀了陳希米(史鐵生的妻子)懷念他的書——《讓死活下去》。她說:“好像心和身體,所有的地方都懸著,絕望得找不到絕望。”郁結其中的空寂令我不忍卒讀。這是失去伴侶的孤雁在寒風中的哀鳴。書中引用哲人唐望的話:“一旦你開始憂慮,你就會因為絕望而抓住任何東西;一旦你抓住不放,就會為之耗盡你的力量,或耗盡你所抓住的人或東西。”孤獨的她開始通過閱讀、行走和書寫,不斷地和史鐵生的靈魂對話,與思想史上的哲人交談,向虛空發問。“史鐵生看書慢,看到前頁把自己的體悟寫出來,等到翻到后頁和作者寫的一樣。那些經過自己豐富體悟過的,會融在血液里,不光更豐富更有力,而且還會生長,成為生命經久的滋養。”經過深沉闊達的思考,她慢慢走出失去愛人的絕境,重新尋獲生命的意義,她要用她的生命讓史鐵生以另一種方式繼續活下去。
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天:2011年1月1日。新的一年的陽光灑滿魯西南這個小城的西門大街,正午我剛從親戚家吃完飯出來,突然瞥見,路邊報亭里懸掛著的報紙上那一幅偌大的黑白照片,史鐵生坦然的微笑正對著我。我突然明白,史鐵生先生永遠離開我們了。我心里空落落的。想著,一個堅強的戰士,在與厄運斗爭了四十年之后,就這樣靜靜地走了。這個世上少這一個人,仿佛整個世界都空曠了,一縷寒風就把一條大街掃蕩了。讀了不少書,沒有哪一個作者能像他一樣深深地走進我的內心。他用殘缺的身體,留給我們最健全的思想。他的樂觀,他的生命哲思,會照亮我們日益幽暗的內心,陪伴我們一直走下去。
深冬的大街上,路人躲躲閃閃地回避著冷風。我直著脖子,沿著街道朝著背離家的方向,機械地走下去。走著走著,淚水像斷了線的珠子,在冷風中噗噗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