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張中丞傳后敘》文章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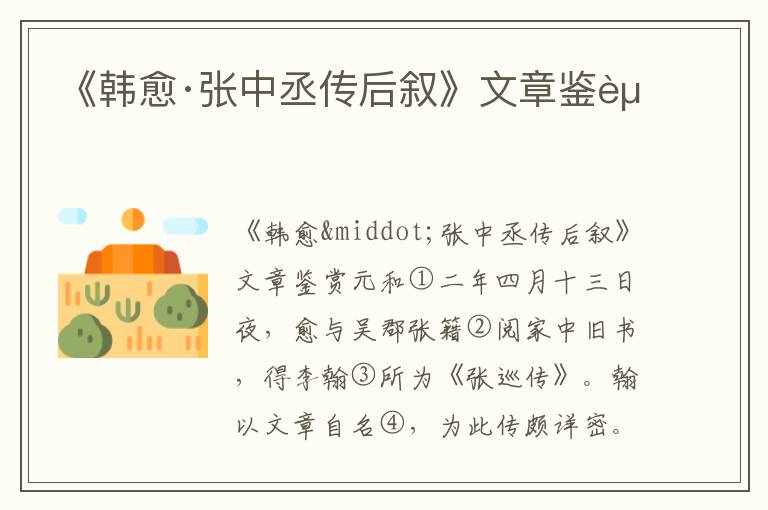
《韓愈·張中丞傳后敘》文章鑒賞
元和①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②閱家中舊書,得李翰③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④,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⑤立傳,又不載雷萬春⑥事首尾。
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⑦,位本在巡上。授之柄⑧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后異⑨耳。兩家子弟⑩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11}于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12},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13}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14}。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15}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
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16}。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于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
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茍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17}之余,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18}!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19}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20}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于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愈嘗從事于汴徐二府,屢道{21}于兩府間,親祭于其所謂雙廟{22}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云之乞救于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云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云坐。霽云慷慨語曰:“云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云泣下。云知賀蘭終無為云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磚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云,云未應。巡呼云曰:“南八{23},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云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
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24}在圍中{25}。籍大歷中于和州烏江縣見嵩{26},嵩時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27},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余,須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28},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29},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后無不識者。巡怒,須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于亳{30}、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注】
①元和:唐憲宗李純的年號(806—820)。②張籍(約767—約830):字文昌,是韓愈的學生,吳郡(治所在今江蘇省蘇州市)人,唐代著名詩人。③李翰:字子羽,趙州贊皇(今河北省元氏縣)人,官至翰林學士。④自名:自許。⑤許遠(709—757):字令威,杭州鹽官(今浙江省海寧縣)人。安史之亂時,他任睢陽太守,后與張巡合守孤城,城陷被擄往洛陽,至偃師被害。⑥雷萬春:與南霽云同為張巡手下的勇將。⑦開門納巡:唐肅宗至德二載(757)正月,叛軍安慶緒部將尹子奇帶兵13萬圍睢陽,許遠向張巡告急,張巡率軍從寧陵入睢陽城。⑧柄:權柄。⑨死先后異:死去的時間先后不同。⑩兩家子弟:指張去疾、許峴。{11}辭服:請降,投降。{12}“食其”句:尹子奇圍睢陽時,城中糧盡,軍民以雀鼠為食,最后只得以婦女與老弱男子充饑。當時,張巡曾殺愛妾、許遠曾殺奴仆以充軍糧。{13}蚍蜉(pífú皮伏):黑色大蟻。蟻子:幼蟻。{14}“而賊”句:安史之亂時,長安、洛陽陷落,玄宗逃往西蜀,唐室岌岌可危。{15}外無待:睢陽被圍后,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等皆擁兵觀望,不來相救。{16}說者句:張巡和許遠分兵守城,張守東北,許守西南。城破時叛軍先從西南處攻入,故有此說。{17}羸(léi雷):瘦弱。{18}“二公”二句:謂二公功績前人已有精當的評價。{19}沮(jǔ舉)遏:阻止,制止。{20}擅:專有。{21}屢道:多次往來。{22}雙廟:張巡、許遠死后,后人在睢陽立廟祭祀,稱為雙廟。{23}南八:南霽云,其在家中排行老八。安史之亂后,被張巡所收留。{24}常:通“嘗”,曾經。{25}圍中:圍城之中。{26}和州烏江縣:在今安徽省和縣東北。{27}臨渙:故城在今安徽省宿縣西南。{28}帙(zhì至):書套,也指書本。{29}僅:幾乎。{30}亳(bó薄):亳州,治所在今安徽省亳縣。
《張中丞傳后敘》是一篇評論,記述唐代官吏張巡和許遠堅守睢陽英勇抗擊安史之亂軍的佳作,也可以說是為英雄人物譜寫了一曲慷慨悲壯的頌歌。
唐朝發生安史之亂后,張巡(709—757)在雍丘一帶起兵抗擊,后與許遠同守睢陽(今河南省商丘市),以微薄之力支撐到了最后,城破被俘后,與部將36人同時不屈而義。亂平以后,朝廷小人竭力散布張許降賊有罪的流言,為割據勢力張目。而李翰曾經親自見到張巡守城的事跡,韓愈感憤于此,就寫《張巡傳》為其澄清事實。
此文創作于唐元和二年(807),繼李翰撰《張巡傳》(今佚)之后,全文感情激蕩,褒貶分明,議論敘事互為表里,不分賓主,其“截然五段,不用鉤連,而神氣流注,章法渾成”。文中關于南霽云拒食斷指、抽矢射塔,張巡誦讀《漢書》、起旋眾泣等細節描寫細膩生動,傳神寫意,形象栩栩如生,光采照人。
本文是議論性較強的記敘文,全文議論和敘事并重,是韓愈對“敘”這種文體的一個創造。全文的最大特色是議論與敘事并重。前半部分側重議論,駁斥了污蔑許遠的錯誤論調,并補敘和贊揚了張巡、許遠“守城、捍衛天下”的事跡;后半部分側重敘事,著重記敘了南霽云去乞師于賀蘭進明的英勇事跡,然后補敘張巡、許遠的軼事。前后兩部分雖各有側重,但又有內在的聯系,前者議論是后者補敘的“綱”,后者是前者的事實佐證,兩部分相輔相成,緊扣贊美英雄、斥責小人的主題。
本文多用事實作論據。如:駁斥傳言許遠畏死降賊的錯誤論調時,用了許遠讓位受權,并在外援不至、人相食且盡的情況下,仍堅持死守的事實;駁斥責備張巡、許遠死守的錯誤議論時,聯系當時敵我雙方力量懸殊“外援不至”,張巡、許遠死守睢陽以捍衛天下的功績,論證守城是正確的。由于都用事實作論證,所以對謬論的批判顯得義正辭嚴,具有不容辯駁的力量。
“駁斥城之陷,自遠所分始”的謬論,運用了類比法。作者用了兩個比喻,即“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以此論證睢陽城的陷落事在必然。將許遠所守的城池先被攻陷,說成是許遠叛變投降,這不過是兒童之見,是完全站不住腳的。通過駁斥誣蔑許遠的錯誤論調以及補充記敘南霽云的事跡,張巡、許遠的其他軼事,贊美他們在安史之亂中抗擊叛軍的英雄事跡,斥責安史叛軍以及那些貪生怕死的將領和誣蔑英雄的小人。
后人評論
黃震在《黃氏日抄》卷上十九中說:“閱‘李翰所為《張巡傳》’而作也。補記載之遺落,暴赤子之英烈。千載之下,癝癝生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