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節(jié)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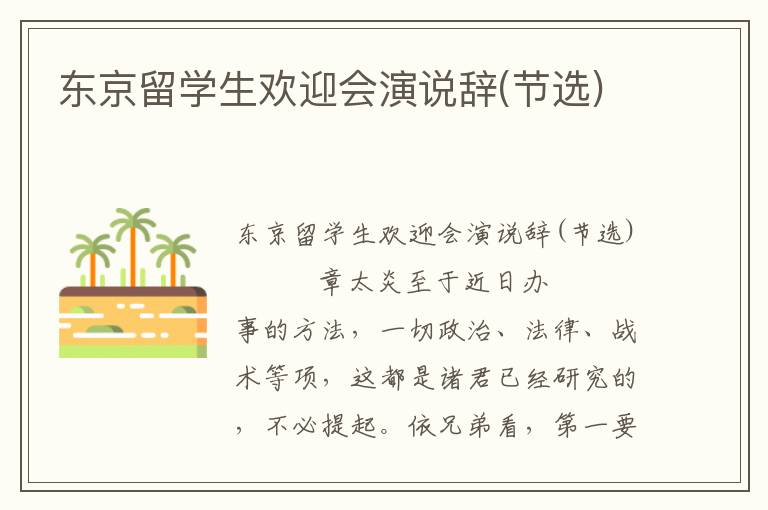
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節(jié)選)
章太炎
至于近日辦事的方法,一切政治、法律、戰(zhàn)術等項,這都是諸君已經研究的,不必提起。依兄弟看,第一要在感情,沒有感情,憑你有百千萬億的拿破侖、華盛頓,總是人各一心,不能團結。當初柏拉圖說:“人的感情,原是一種醉病”,這仍是歸于神經的了。要成就這感情,有兩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發(fā)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次說國粹。為甚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個歷史,是就廣義說的,其中可以分為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跡。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總說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所以自甘暴棄,說中國必定滅亡,黃種必定剿絕。因為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見得別無可愛,就把愛國愛種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曉得,我想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愛國愛種的心,必定風發(fā)泉涌,不可遏抑的。兄弟這話,并不象做《格致古微》的人①,將中國同歐洲的事,牽強附會起來;又不象公羊學派的人②,說甚么三世就是進化③,九旨就是進夷狄為中國,去仰攀歐洲最淺最陋的學說,只是就我中國特別的長處,略提一二。先說語言文字。因為中國文字,與地球各國絕異,每一個字,有他的本義,又有引申之義。若在他國,引申之義,必有語尾變化,不得同是一字,含有數義。中國文字,卻是不然。且如一個天字,本是蒼蒼的天,引申為最尊的稱呼,再引申為自然的稱呼。三義不同,總只一個天字。所以有《說文》④、《爾雅》⑤、《釋名》⑥等書,說那轉注、假借的道理。又因中國的話,處處不同,也有同是一字,彼此聲音不同的;也有同是一物,彼此名號不同的。所以《爾雅》以外,更有《方言》⑦,說那同義異文的道理。這一種學問,中國稱為“小學”,與那歐洲“比較語言”的學,范圍不同,性質也有數分相近。但是更有一事,是從來小學家所未說的,因為造字時代先后不同,有古文大篆沒有的字,獨是小篆有的;有小篆沒有的字,獨是隸書有的;有漢時隸書沒有的字,獨是《玉篇》⑧、《廣韻》⑨有的;有《玉篇》、《廣韻》沒有的字,獨是《集韻》⑩、《類篇》[[!B11]]有的。因造字的先后,就可以推見建置事物的先后。且如《說文》兄、弟兩字,都是轉注,并非本義,就可見古人造字的時代,還沒有兄弟的名稱。又如君字,古人只作尹字,與那父字,都是從手執(zhí)杖,就可見古人造字的時代,專是家族政體,父權君權,并無差別。其余此類,一時不能盡說。發(fā)明這種學問,也是社會學的一部。若不是略知小學,史書所記,斷斷不能盡的。近來學者,常說新事新物,逐漸增多,必須增造新字,才得應用,這自然是最要,但非略通小學,造出字來,必定不合六書規(guī)則。至于和合兩字,造成一個名詞,若非深通小學的人,總是不能妥當。又且文辭的本根,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學,所以文章優(yōu)美,能動感情。兩宋以后,小學漸衰,一切名詞術語,都是亂攪亂用,也沒有絲毫可以動人之處。究竟甚么國土的人,必看甚么國土的文,方覺有趣。象他們希臘、梨俱[[!B12]]的詩,不知較我家的屈原、杜工部優(yōu)劣如何·但由我們看去,自然本種的文辭,方為優(yōu)美。可惜小學日衰,文辭也不成個樣子。若是提倡小學,能夠達到文學復古的時候,這愛國保種的力量,不由你不偉大的。第二要說典章制度。我個〔們〕中國政治,總是君權專制,本沒有甚么可貴,但是官制為甚么要這樣建置·州郡為甚么要這樣分劃·軍隊為甚么要這樣編制·賦稅為甚么要這樣征調·都有一定的理由,不好將專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殺。就是將來建設政府,那項須要改良·那項須要復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見諸施行。至于中國特別優(yōu)長的事,歐、美各國所萬不能及的,就是均田一事,合于社會主義。不說三代井田,便從魏、晉至唐,都是行這均田制度。所以貧富不甚懸絕,地方政治容易施行。請看唐代以前的政治,兩宋至今,那能仿佛萬一。這還是最大最繁的事,其余中國一切典章制度,總是近于社會主義,就是極不好的事,也還近于社會主義。兄弟今天,略舉兩項,一項是刑名法律。中國法律,雖然近于酷烈,但是東漢定律,直到如今,沒有罰錢贖罪的事,惟有職官婦女,偶犯笞杖等刑,可以收贖。除那樣人之外,憑你有陶朱[[!B13]]、猗頓[[!B14]]的家財,到得受刑,總與貧人一樣。一項是科場選舉。這科舉原是最惡劣的,不消說了,但為甚隋、唐以后,只用科舉,不用學校·因為隋、唐以后,書籍漸多,必不能象兩漢的簡單。若要入學購置書籍,必得要無數金錢。又且功課繁多,那做工營農的事,只可閣〔擱〕起一邊,不能象兩漢的人,可以帶經而鋤的。惟有律賦詩文,只要花費一二兩的紋銀,就把程墨[[!B15]]可以統統買到,隨口咿唔,就象唱曲一般,這做工營農的事,也還可以并行不悖,必得如此,貧人才有做官的希望。若不如此,求學入官,不能不專讓富人,貧民是沈淪海底,永無參預政權的日了。這兩件事,本是極不好的,尚且?guī)追稚鐣髁x的性質,況且那好的么·我們今日崇拜中國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的社會主義。那不好的,雖要改良;那好的,必定應該頂禮膜拜,這又是感情上所必要的。第三要說人物事跡。中國人物,那建功立業(yè)的,各有功罪,自不必說。但那俊偉剛嚴的氣魄,我們不可不追步后塵。與其學步歐、美,總是不能象的;何如學步中國舊人,還是本來面目。其中最可崇拜的,有兩個人:一是晉末受禪的劉裕[[!B16]],一是南宋伐金的岳飛,都是用南方兵士,打勝胡人,可使我們壯氣。至于學問上的人物,這就多了。中國科學不興,惟有哲學,就不能甘居人下。但是程、朱、陸、王的哲學,卻也無甚關系。最有學問的人,就是周秦諸子,比那歐洲、印度,或者難有定論;比那日本的物茂卿[[!B17]]、太宰純輩,就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了。日本今日維新,那物茂卿、太宰純輩,還是稱頌弗衰,何況我們莊周、荀卿的思想,豈可置之腦后·近代還有一人,這便是徽州休寧縣人,姓戴名震[[!B18]],稱為東原先生,他雖專講儒教,卻是不服宋儒,常說“法律殺人,還是可救;理學殺人,便無可救。”因這位東原先生,生在滿洲雍正之末,那滿洲雍正所作朱批上諭,責備臣下,并不用法律上的說話,總說“你的天良何在·你自己問心可以無愧的么·”只這幾句宋儒理學的話,就可以任意殺人。世人總說雍正待人最為酷虐,卻不曉是理學助成的。因此那個東原先生,痛哭流涕,做了一本小小冊子,他的書上,并沒有明罵滿洲,但看見他這本書,沒有不深恨滿洲。這一件事,恐怕諸君不甚明了,特為提出。照前所說,若要增進愛國的熱腸,一切功業(yè)學問上的人物,須選擇幾個出來,時常放在心里,這是最緊要的。就是沒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跡,都可以動人愛國的心思。當初顧亭林[[!B19]]要想排斥滿洲,卻無兵力,就到各處去訪那古碑古碣傳示后人,也是此意。原載1906年7月25日《民報》第六號
〔注釋〕 ①做《格致古微》的人:指王仁俊。王仁俊是晚清西學中源說的代表人物,著《格致古微》六卷,從先秦諸子、儒家經典與二十四史中輯出材料,說明西學源出中國。西學中源說以為,西方的某些科學技術、某些事物,是中國流傳出去的。中國學習這些東西,是恢復自己的舊物。最早提出該觀點的是黃宗羲,廣泛流行則在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 ②公羊學派的人:指康有為。 ③三世就是進化:三世說是儒家公羊學派關于歷史演變的思想。由董仲舒首倡,以為《春秋》分十二世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康有為把三世說融進了西方的進化論,并和《禮運》相結合,以為從據亂世到升平世(小康)再到太平世(大同),是社會進化的共同規(guī)律。 ④《說文》: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的簡稱,收字9353個。按文字形體及偏旁構造,首創(chuàng)部首排檢法,分列540部。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分析字形和考察字源的字書,對后世文字學的研究影響極大。 ⑤《爾雅》:最早解釋詞義的專著,由漢初學者綴輯周、漢書舊文,遞相增益而成。 ⑥《釋名》:訓詁書,東漢劉熙著。體例仿《爾雅》,以音同、音近的字解釋意義,推究事物所以命名的由來。 ⑦《方言》:語言和訓詁書。西漢揚雄撰。體例仿《爾雅》,類集古今各地同義詞語,大部分注明通行范圍。 ⑧《玉篇》:字書,三十卷。南朝陳梁間顧野王撰。體例仿《說文解字》,收字16918個。今只存殘卷。 ⑨《廣韻》:韻書,五卷。宋代陳彭年等奉詔重修。后世研究中古語音大都以此為重要依據,為漢語音韻學的一部重要著作。 ⑩《集韻》:十卷。宋代丁度等奉詔重修。字數為53525個,比《廣韻》增一倍余。為研究文字訓詁和宋代語音的重要資料。 [[!B11]]《類篇》:字書,四十卷。宋代王洙、司馬光等奉詔纂修,體例仿《說文解字》,收字31000余。 [[!B12]]梨俱:指《梨懼吠陀》,古印度詩集,收1028首詩。 [[!B13]]陶朱:越國大夫范蠡的別號。后世用以稱富商。 [[!B14]]猗頓:戰(zhàn)國時巨商。以經營河東鹽池致巨富,又經營珠寶,以能識別寶玉著稱。 [[!B15]]程墨:科舉時代,刊行官撰或士人中式試卷以為范例的文章。 [[!B16]]劉裕(363—422):南朝宋的建立者。元熙二年(公元420年)代晉稱帝,為宋武帝。 [[!B17]]物茂卿(1666—1728):日本德川時代哲學家,在儒學研究上頗有造詣。先信朱熹學說,后轉向批判朱學。其學說在當時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對后世產生較大影響。 [[!B18]]戴震(1724—1777):字東原,安徽休寧人。清思想家。學識廣博,參與編纂《四庫全書》。激烈批判程朱理學的禁欲主義,認為理學倡導的“存理滅欲”的“天理”,“以理殺人”比酷吏以法殺人更為殘酷。 [[!B19]]顧亭林(1613—1682):江蘇昆山亭林鎮(zhèn)人。明清之際思想家。明亡后參與抗清起義,失敗后游華北,聯絡同道,以圖復明。于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金石文字均有精深的研究。學主經世致用,提出后世廣泛認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理念。〔鑒賞〕 這是1906年章太炎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會上的演講。章太炎認為,要實現革命的目標,“第一、是用宗教發(fā)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這里選擇了第二條的內容作詮釋。章太炎在《蘇報》上撰文推薦鄒容《革命軍》并發(fā)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清廷極為惱火,遂勾結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于1903年逮捕章太炎與鄒容。是為近代史上著名的“蘇報案”。1906年章太炎刑滿出獄后,孫中山派人到上海把他接往日本東京。在同盟會總部主持下,中國留日學生在東京神田舉行集會,聽章太炎講演。章太炎明確指出,他提倡的“國粹”,是要求人們尊重本民族的歷史,熟悉國情,了解中國自身的優(yōu)點,決不是信奉那斷不可用的孔教,也不是要人們去忠君尊孔,信奉綱常名教,死抱住歷史糟粕的東西不放。他要人們拋掉民族虛無主義,增強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他提倡的“國粹”,包括三項內容:一是民族的語言文字,二是古代典章制度中的好東西,三是中國歷史上許多建功立業(yè)、有學問的優(yōu)秀人物的事跡。章太炎認為,中國的文字有它獨特性,“與地球各國絕異,每一個字,有它的本義,又有引申之義”。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學,所以文章優(yōu)美,能動感情”。宋以后,小學日漸衰落。“若是提倡小學,能夠達到文學復古的時候,這愛國保種的力量,不由你不偉大的”。在典章制度中,顯得特別優(yōu)長的,為“歐、美各國所萬不能及的,就是均田一事,合于社會主義”。中國科舉制的實行,“貧人才有做官的希望”,有參與政權的機會。“我們今日崇拜中國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的社會主義”。把均田制與科舉制說成“合于社會主義”,學術上有點牽強附會,不過章太炎說自己的目標,是針對“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他們說“中國必定滅亡,黃種必定剿絕”。考慮到這樣的因素,如此比附可以說是章太炎別有一番心思了。歷史上建功立業(yè)的人物,章太炎推崇晉末的劉裕與南宋的岳飛。他們“都是用南方兵士,打勝胡人”。講到學術,章太炎以為,“最有學問的人,就是周秦諸子”。章太炎對宋明理學家反感得很,以為清代戴震講的“法律殺人,還是可救;理學殺人,便無可救”的話,“沒有明罵滿洲,但看見他這本書,沒有不深恨滿洲。”章太炎認定的優(yōu)秀人物,是以排斥異族為準則的,尤以排滿為主要目的的。他在演講中指明,要用“國粹”來培養(yǎng)人們“愛國愛種的心”,以達到“風發(fā)泉涌,不可遏抑”的地步。章太炎以為,要達到排滿的目的,就得提倡和培養(yǎng)民族主義的情感:“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為之灌溉,則蔚然以興矣。”(《答鐵錚》)民族主義的培養(yǎng),就像莊稼要灌溉一樣,一定得用中國民族文化上的優(yōu)秀傳統,用歷史上記載的優(yōu)秀人物,以及制度、地理、風俗來教育民眾。這樣的民族主義,是屬于愛國主義范疇的。章太炎的排滿思想,從小就萌生于心中,這源自于明清之際啟蒙思想家。在他十一、二歲時,外祖父朱有虔給他講了雍正年間曾靜、呂留良的文字獄案,向他灌輸了“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義”的道理,告訴他,這些道理在王船山、顧亭林的書中都已講了,尤以王船山的言論更為激烈。王船山看一姓的興亡輕,而視民族的盛衰重;以為可以禪讓,也可以改朝換代,但不能失國于異族。這種極端的民族主義,內中有著強烈的反清意識。1933年辛亥革命22周年之際,章太炎作講演時說:“余成童時,嘗聞外祖父朱左卿先生言:‘清初王船山嘗云,國之變革不足患,而胡人之入主中夏則可恥。’排滿之思想,遂醞釀于胸中。”(《民國光復》)百余年前,章太炎是被當作一個英雄而受到隆重歡迎的。據當時人記載,聽講演的留日學生“是日至者二千人,方時雨,款門者眾,不得遽入,咸植立雨中,無惰容。”(《章太炎年譜長編》第211頁)沒有入會場的,站在雨中聽講,且無絲毫倦意。原因只有一條,即清廷的腐敗與賣國日益為人們所認清:1903年春的拒俄愛國運動,遭到清廷的無情鎮(zhèn)壓;同年夏天上海發(fā)生的“蘇報案”,借洋人迫害革命志士的嘴臉暴露無遺。排滿主義是當時革命派中政見不同者唯一能共同認可的觀點。章太炎“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的排滿主張,適應了當時的時代思潮,是符合要求推翻清廷的志士們的革命要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