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明代兵法·兵經百篇》原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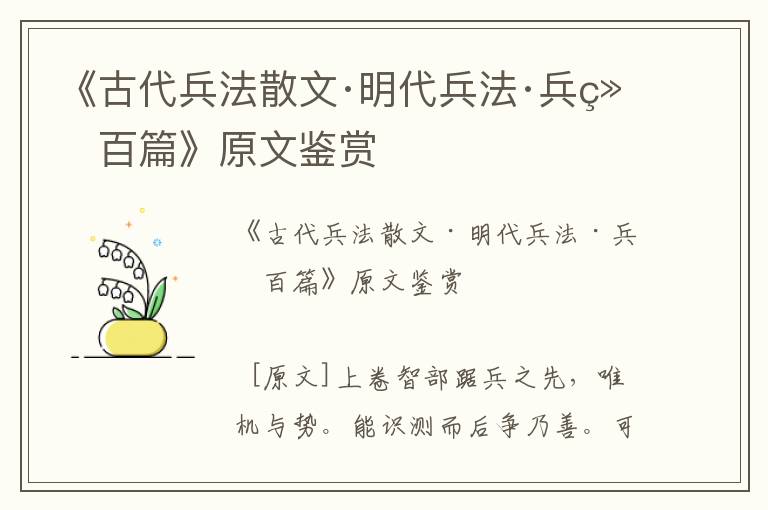
《古代兵法散文·明代兵法·兵經百篇》原文鑒賞
[原文]
上卷智部
踞兵之先,唯機與勢。能識測而后爭乃善。可不精讀兵言以造于巧乎?至于立謀設計,則始而生,繼而變,再而累,自是為轉為活,為疑為誤,無非克敵之法,不得已,乃用拙。總之,預布疊籌,以底乎周謹,而運之行間(指反間),乃能合之以秘也。
先
兵有先天,有先機,有先手,有先聲。師之所動而使敵謀沮抑,能先聲也;居人已之所并爭,而每早占一籌,能先手也;為倚薄擊決利,而預布其勝謀,能先機也;于無爭止爭,以不戰阻戰,當未然而浸消之,是云先天。先為最,先天之用尤為最,能用先者,能運全經矣。
機
勢之維系處為機,事之轉變處為機,物之緊切處為機,時之湊合處為機。有目前即是機,轉瞬即非機者;有乘之即為機,失之即無機者。謀之宜深,藏之宜密。定于識,利于決。
勢
猛虎不據卑址,勍鷹豈立柔枝?故用兵者務度勢。處乎一隅,而天下搖搖莫有定居者,制其上也。以少邀眾,而堅銳沮避莫敢與爭者,扼其重也。破一營而眾營皆解,克一處而諸處悉靡者,撤其恃也。陣不竣交合,馬不及鞭弭,望旌旗而踉蹌奔北者,摧其氣也。能相地勢,能立軍勢,善之以技,戰無不利。
識
聽金鼓,觀行列而識才; 以北誘,以利餌而識情,撼而驚之,擾而拂之而識度,察于事也。彼之所起,我悉覺之;計之所紿,我悉洞之;智而能掩,巧而能伏,我悉燭之,灼于意也。若夫意所未起而預擬盡變,先心敵心以知敵,敵后我意而意我,則謀而必投。一世之智,昭察無遺,后代之能逆觀于前。識至此,綦渺矣。
測
兩將初遇,必有所試;兩將相持,必有所測。測于敵者,避實而擊疏;測于敵之測我者,現短以致長。測蹈于虛,反為敵詭。必一測而兩備之,虞乎不虞,全術也,勝道也。
爭
戰者爭事也,兵爭交,將爭謀,將將爭機。夫人而知之,不爭力而爭心,不爭人而爭己。夫人而知之,不爭事而爭道,不爭功而爭無功。無功之功,乃為至功;不爭之爭,乃為善爭。
讀
論事古不如今,事多則法數,時移則理遷。故讀千古兵言(千古兵言可能為千家兵言之誤),有不宜知拘,妄言知謬,未備識缺,膚俚須深,幻杳索實,浮張心斥,成套務脫。忌而或行,誠而或出,審疏致密,由偏達全,反出見奇,化執為活,人泥法而我鑄法,人法法而我著法。善用兵者,神明其法。
言
言為劍鋒上事(古有三鋒之說,舌鋒在劍鋒之上),所用之法多離奇:或虛楊以濟謀,或權托以備變;或誣構以疏敵;或謙遜以玩敵。至預發摘奸,詭譎造惑,故洩取信,反說餂意,款劇(疑款)導情,壯烈激眾,愴痛感軍,高危悚聽,震厲破膽。假癡,偽認,佯怒,詐喜,逆排,順導,飛、流、紿、狂、吃、譫、附、瞪、形、指、躡、嘿,皆言也,皆運言而制機宜者也。故善言者,勝驅精騎。
造
勘性命以通兵玄,探古史以核兵跡,窮象數以徹(徹:通意)兵徽,涉時務以達兵政,考器物以測兵物,靜則設無形事而作謀,出則探索所懷而經天下。
巧
事不可以徑成者必以巧,況行師乎。善破敵之所長,使敵攻守失恃,逃散不能,是謂因制之巧;示弱使忽,交納使慢,習處使安,屢常使玩,時出使耗,虛警使防,挑罵使怒,是謂愚侮之巧;所設法,非古有法,可一不可再,獨造而獨智,是謂臆空之巧;一徑一折,忽深忽淺,使敵迷而受制,是謂曲入之巧; 以活行危而不危,翻安為危而復安,舍生趨死,向死得生以成事,是謂反出之巧。
謀
兵無謀不戰,謀當底于善。事各具善機也,時各載善局也。隨事因時,謀及其善而止。古畫三策,上為善。有用其中而善者;有用其下而善者;有兩從之而善者;并有處敗而得善者。智不備于一人,謀必參諸群士。善為事極,謀附于善為謀極。深事深謀,無難而易;淺事淺謀,無過而失也。
計
計有可制愚不可制智,有可制智不可制愚。一以計為計,一以不計為計也。惟計之周,智愚并制。假智者而愚,即以愚施;愚者而智,即以智投;每遇乎敵所見,反乎敵所疑,則計蔑不成矣。故計必因人而設。
生
生者孽 也,玄蒂也。故善計者因敵而生,因己而生,因古而生,因書而生,因天時地利事物而生,對法而生,反勘而生。陡設者無也。象情者有也,皆生也。
變
事幻于不定,亦幻于有定。以常行者而變之,復以常變者而變之,變乃無窮。可行則再,再即窮,以其擬變不變也。不可行則變,變即再,以其識變而復變也。萬云一氣,千波一浪,是此也,非此也。
累
我可以此制人,即思人亦可以此制我,而設一防;我可以此防人之制,人即可以此防我之制,而增設一破人之防;我破彼防,彼破我防,又應增設一破彼之破;彼既能破,復設一破乎其所破之破,所破之破既破,而又能固我所破,以塞彼破,而申我破,完不為其所破。遞法以生,踵事而進,深乎深乎。
轉
守者一,足敵攻之十,此恒論也。能行轉法,則其勢倍百。如我以十攻一,茍能轉之,則彼仍其一,而我十其十,是以百而擊一。我以十攻十,茍能轉之,則我仍其十,而彼縮其九,是以十而擊一。我以一攻十,茍能轉之,則敵止當一,而我可敵十,是以一而擊一。故善用兵者,能變主客之形,移多寡之數,翻勞逸之機,遷利害之勢,挽順逆之狀,反驕厲之情。轉乎形并轉乎心,以艱者危者予乎人,易者善者歸諸已,轉之至者也。
活
活有數端:可以久,可以暫者,活于時也;可以進,可以退者,活于地也;可以來,可以往,則活于路;可以磔,可以轉,則活于機。兵必活而后動,計必活而后行。第活中務緊,緊處尋活。無留接是為孤軍,無后著是云窮策。
疑
兵詭必疑,虛疑必敗。
誤
克敵之要,非徒以力制,乃以術誤之也。或用我誤法以誤之,或因其自誤而誤之,誤其恃,誤其利,誤其拙,誤其智,亦誤其變。虛挑實取,彼悟而我使誤,彼誤而我能悟。故善用兵者,誤人不為人誤。
左
兵之變者無如左。左者以逆為順,以害為利;反行所謀左其事,以具資人左其形,越取迂遠左其徑。易而不攻,得而不守,利而不進,侮而不遏,縱而不留;難有所先,險有所蹈,死有所趨;患有不恤,兵眾不用,敵益而喜,皆左也。適可而左,則適左而得,若左其所左則失矣。
拙
遇強敵而堅壁,或退守時宜拙也。敵有勝名,于我無損,則侮言可納,兵加可避,計來可受,凡此皆可拙而拙也。甚至敵無奇謀,我有外患;敵本雌伏,我以勁待,凡此皆不必拙而拙,無失也。寧使我有虛防,無使彼得實著。歷觀古事,竟有以一拙敗名將而成全功者。故曰: 為將當有怯時。
預
凡事以未意而及者,則心必駭,心駭則倉卒不能謀,敗徽也。兵法千門,死傷萬數,必敵襲如何應,敵沖如何擋,兩截何以分,四來何以戰。凡屬艱險危難之事,必須籌而分布之,務有一定之法,并計不定之法,而后心安氣定,適值不驚,累中無虞。古人行師,經險出難,安行無慮,非必有奇異之智,預而己。
疊
大凡用計者,非一計之可孤行,必有數計以儴之也。以數計儴一計,由千百計煉數計,數計熟則法法生。若間中者偶也,適勝者遇也。故善用兵者,行計務實施,運巧必防損,立謀慮中變,命將杜違制。此策阻而彼策生,一端致而數端起,前未行而后復具,百計疊出,算無遺策,雖智將強敵,可立制也。
周
處軍之事煩多,為法亦瑣。大而營伍行陣,小而衣食寢居,總不可開隙迎扈(疑誤)。故攄思于不慮,作法于無防,敵大勿畏,敵小勿欺,計周靡恃,為周之至。
謹
用兵如行螭宮蛟窟,有風波之險。螭宮蛟窟,渡則安也。若大將則無時非危,當無時不謹。入軍如有偵,出境儼臨交,獲取驗無害,遇山林險阻必索奸,敵來慮有謀,我出必裕計。慎以行師,至道也。
知
微乎微乎!惟兵之知。以意測,以識悟,不如四知之廉得其實也。一曰通,二曰謀,三曰偵,四曰鄉。通,知敵之計;諜,知敵之虛實;偵,知敵之動靜出沒; 鄉,知山川蓊翳、里道迂回、地勢險易。知計謀則知所破,知虛實則知所擊,知動靜出沒則知所乘,知山川里道形勢則知所行。
間
間者祛敵心腹,殺敵愛將,而亂敵計謀者也。其法則有生、有死、有書、有文、有言、有謠、用歌,用賂、用物、用爵、用敵、用鄉、用友、用女、用恩、用威。
秘
謀成于密,敗于泄。三軍之事,莫重于秘。一人之事,不泄于二人;明日所行,不泄于今日。細而推之,慎不間發。秘于事會,恐泄于語言;秘于語言,恐泄于容貌;秘于容貌,恐泄于神情;秘于神情,恐泄于夢寐。有形而隱其端,有用而絕其口。然可言者,亦不妨先露以示信,推誠有素,不秘所以為秘地也。
中卷法部
軍之興也,唯上善任,唯將輯兵。于材能鋒穎之士,結而馭之,練而勵之,勤而恤之。較閱能否,兵銳糧足,而后可以啟行。迨相移住,必得所趨,稔于地利而后可以立陣;能肅、能野、能張、能斂,順而發,拒而撼,而后可以逆戰。及搏則必善于分、更,明于延:速,運乎牽; 勾,以迨委;鎮,而后可以制勝。然必深圖一全人隱己之術也。
興
凡興師必分大勢之先后緩急以定事,酌彼己之情形利害以施法,總期于守己而制人。或嚴外以衛內,或固本以擴基,或剪羽以孤勢,或擒首以散余或攻強以震弱,或拒或交,或剿或撫,或圍或守,或遠或近,或兩者兼行,或專力一法。條而審之,參而酌之,決而定之,而又能委曲推行,游移待變,則展戰而前,可大勝也。
任
上御則掣,下抗則輕。故將以專制而成,分制而異,三之則委,四之五之,則擾而拂。毋有監,監必相左也;毋或觀,觀必妄聞也;毋聽讒,讒非忌即間也。故大將在外,有不俟奏請,贈賞誅討,相機以為進止。將制其將,不以上制將。善將將者,專厥任而已矣。
將
有儒將,有勇將,有敢將,有巧將,有藝將。儒將智,勇將戰,敢將膽,巧將制,藝將能。兼無不神,備無不利。
輯
輯睦者,治安之大較。睦于國,兵鮮作;睦于境,燧無驚。不得已而治軍,則尤貴睦。君臣睦而后任專,將相睦而后功就,將士睦而后功賞相推,危難相援。是輯睦者治國行軍不易之善道也。
材
王有股肱耳目,大將比羽翼贊儴。故師之用材,等于朝庭。有智士,若參謀,亦贊國,亦諜呈,任帷幄而決軍機,動必咨詢。有勇士,若驍將,亦健將,亦猛將,亦梟將,主決戰而備沖突,率眾當先。有親士,若私將,若手將,若幄將,若牙將,主左右宿衛、宣令握機。有識士,曉陣宜,知變化,望景氣,測云物,驗風雨,悉地域,灼敵情,知微察隱,司一軍進止。有文士,窮今古,緯理原,秉儀節,哆請求,構箋檄,露疏典,辭亮章。有術士,精時日,相陰幽,探策卜,操回避,煉鴆餌,使權宜可否,利己損敵。有數士,審國運,逆利厄,射襲伏,籌餉筊,紀物用,錄勛酬,籍卒伍,丈徑率,能籌算多寡,略無差脫。有技士,劍客刺,死士輕,盜動襲,通說辨,間諜譎,俾得出入敵壘,相機設巧。有藝士,度材器,規溝塹,葺損窳,創神異,顛小大,促遠近,更上下,翻重輕,仿古標新,專簡飭兵物以全攻守。此九者之內,有兼才,如智能役勇,勇能行智,及智勇備者。有通才,若智謀,若勇戰,若文、藝、技、術,無有不達者,誠奇杰國士也。外此則有別材,若戲,若舞,若笑,若罵,若歌,若鳴,若魃,若擲,若躍,若飛,若圖畫,若烹飲,若染涂,若假物形,若急足善行,總不可悉名。然屬技能足給務理紛者,皆必精選厚別,俾得善其所司,而后事無不宜之人,軍無不理之事。至于獻謀陳策,則罔擇人,偶然之見,一得之長,雖以卒徒,必亟上擢。言有進而無拒,不善不加罰,則英雄悉致,此羽林列曜之象也。
能
天之生人,氣聚中虛則智,氣散四肢則樸。樸者多力,智者多弱,智勇兼備者,世不可數。故能過百人者,長百人;能過千人者,長千人;越千則成軍矣。能應一面之機,能當一面之鋒,乃足以長軍。軍有時而孤,遣將必求可獨往。故善用才者,偏裨皆大將也。
1
鋒
自天、地、風、云、龍、虎、鳥、蛇而外,更立九軍。所以厚別分值,為軍之鋒。一曰親軍,乃里壯家丁,護衛大將者也; 一曰憤軍,乃復仇贖法,愿驅前列者也; 一曰水軍,能出沒波濤,覆舟蕩楫; 一曰火軍,能飛鏢滾雷,遠致敵陣; 一曰弓弩軍,能伏窩挽強,萬羽齊發,制敵百步之外;一曰沖軍,力撼山岳,氣叱旌旗,于以攖大敵,冒強寇; 一曰騎軍,驍勇異倫,飛馳兩陣之間,追擊遠絕之地; 一曰車軍,材力敏捷,進犯矢石,退遏奔騎,列之使敵不得進;一曰游軍,巡視機警,便宜護應合(疑是全字)軍,舉動皆擊之。而中有猱升,狼下,蛇行,鼠伏,縋險,通遠,逾城,穿幕之屬。九者親游附于中軍,余每分列八隅。隅則各御,合則兼出,可伸可縮,使一陣之間,血脈聯絡,惟籍此為貫通也。
結
三軍眾矣,能使一之于吾者,非徒威令之行,有以結之也。而結必協其好:智者展之,勇者任之,有欲者遂之,不屈者植之,淺其憤惋,復其仇仇,見瘡痍如身受,行罪戮如不忍,有功者雖小必錄,得力者賜于非常,所獲則均,從役厚恤,撫眾推誠,克敵寡殺。誠若是豈惟三軍之事,應麾而轉,將天下皆望羽至矣。敵其空哉!
馭
人以拂氣生,才以怒氣結。茍行兵必求不變者而后用,天下有幾?兵非善事,所利之才即為害之才。勇者必狠,武者必殺,智者必詐,謀者必忍。兵不能遣勇武智謀之人,即不能遣狠殺詐忍之人;不用狠殺詐忍之人,則又無勇武智謀之人。故善馭者,使其能而去其兇,收其益而杜其損,則天下無非其才也。仇可招也。寇可撫也,盜賊可舉,而果輕法,而夷狄遠人,皆可使也。
練
意起而力委謝者,氣衰也; 力余而心畏沮者,膽喪也。氣衰膽喪,智勇竭而不可用。故貴立勢以練氣,經勝以練膽,布心以練情,教以練陣藝。三軍練,彼此互乘,前后疊麗,動則具動,靜則具靜。
勵
勵士原不一法,而余謂名加則剛勇者奮,利誘則忍毅者奮,迫之以勢,陷之以危,詭之以術,則柔弱者亦奮。將能恩威脅,所策皆獲,則三軍之士,彪飛龍蹲,遇敵可克。而又立勢佐威,盈節護氣,雖北不損其銳,雖危不震其心,則又無人無時而不可奮也。
勒
勒馬者必以羈勒,勒兵者必以法令。故勝天下者不弛法。然恩重乃可施罰,罰行而后威濟,是以善用兵者準得失為功罪,詳斗奔以恤傷。戮一人而人皆威,殺數眾而眾感服,誅怯斬敗,而士益奮,號令嚴肅,犯法不貸,止如岳,動如崩,故所戰必克。決不以濡忍為恩,使士輕其法,致貽喪敗也。
恤
嘗有絕代英雄,方露端倪,輒為行間混陷,亦有雜于卒伍,勛業未建,或為刑辟所加,可勝浩嘆。天之生才甚難,茍負其質而不見用,則將投敵而為我抗,此為大將者在所必恤。恤者:平日虛懷咨訪,毋使不偶。至于陣中軍兵,披霜宿野,帶甲懸刀,饑搏風戰,傷于體而不言苦,經于難不敢告勞,茍輕棄其命,非惟不利于軍,亦且不利于將。故善用兵者,不使陷于敵,與擅肆戮也。
較
較器不如較藝,較藝不如較數,較數不如較形與勢,較形與勢不如較將之智能。智能勝而勢不勝者,智能勝; 勢勝而形不勝者,勢勝;形勝而數不勝者,形勝,形與數勝則藝疏器窳者,形數勝。我勝乎至勝,彼勝乎小勝。敵雖有幾長,無難克也。
銳
養威貴素,觀變貴謀。兩軍相薄,大呼陷陣而破其膽者,惟銳而已矣。眾不敢發而發之者,銳也;敵眾蜂親,以寡赴之者,銳也;出沒敵中,往來沖擊者,銳也;為驍為健。為勇鷙猛烈者,將銳也;如風如雨,如山崩岳搖者,軍銳也;將突而進,軍涌而沖者,軍將皆銳也。徒銳者蹶,不銳者衰。智而能周,發而能收,則銳不窮。
糧
籌糧之法,大約歲計者宜屯,月計者宜運,日計者宜流給,行千里則運流兼,轉徙無常則運流兼,迫急不及鐺煮則用干糇。若夫因糧于敵,與無而示有,虛而示盈,及運道阻截,困守圍中,索百物為飼,間可救一時,非可長恃者。民之天,兵之命,必謀之者不竭,運之者必繼,護之者維周,用之者常節。
住
住軍必后高前下,向陽背陰,養生處實水火無慮,運接不阻,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有草澤流泉,通達樵牧者則住。然物散不全,方域各異。故暫止惟擇軍宜,久拒必任地勢。
行
軍行非易事也。行險有伏可慮,濟川惟決是憂,晝起恐其暴來,夜止虞彼虛擾,易斷絕者貫聯,難疾速者卷進。一節不防,則失在疏。必先繪其地形以觀大勢,復尋土著之人,以為前導,一山一水,必盡知之,而后可以行軍。
移
軍無定居,亦無定去,但相機宜而行。春宜草木,枯燥則移;夏宜泉澤,雨濡則移;伏于林翳,風甚則移;有便則投,可虞則移;有利則止,無獲則移;敵脆則止,敵堅則移;此強彼弱則移,此緩彼急則移,此難彼易則移。
趨
師貴徐行,以養力也。惟乘人不備,及利于急擊,當倍道以趨。晝趨則偃旗息鼓,夜趨則卷甲銜枚。趨一日者力疲,經晝夜者神憊。一日以趨,兼百數十里; 晝夜以趨,兼二三百里。兼近者絕不成行陣難畢至; 兼遠者棄大軍而進。故眾師遠乎其后也。人不及食,馬不及息,勞而寡及,非恃我之精堅,敵之摧喪,與地形山川之洞悉,敢出于此乎?故非全利而遠害,慎勿以趨為幸也。
地
凡進師克敵,必先相敵地之形勢。十里有十里之形勢,百里有百里之形勢,千里有千里之形勢。即數里之間,一營一陣,亦有形勢。一形勢,必有吭、有背、有左夾右夾、有根基要害。而所恃者必恃山、恃水、恃城、恃壁、恃關隘險阻,草木蓊翳,道路雜錯,克敵者,必審其何路可進,何處可攻,何地可戰,何處可襲,何山可伏,何徑可誘,何險可據。利騎利步,利短利長,利縱利橫。業有成算,而后或扼吭,或撫背,或穿夾,或制根基要害。恃山則索逾山之法,恃水則索渡水之法。恃城壁關隘,草木道路,則索拔城破壘,越關過隘,焚木除草,稽察道路,正歧通合之法。勢在外,慎毋輕入,入如魚之游釜,難以遺脫;勢在內,毋徒繞,繞如虎斗圈羊,不可食也。故城非伏難攻,兵非導不進。山川以人為固,茍無人能拒,山川曷足險哉。
利
兵之動也,必度益國家,濟蒼生,重威能。茍得不償失即非善利者矣。行遠保無虞乎?出險保無害乎?疾趨保無蹶乎?沖陣保無陷乎?戰勝保無損乎?退而不失地,則退也;避而有所全,則避也。北有所誘,降有所謀,委有所取,棄有所收,則北也,降也,委棄也。行兵用智,須相其利。
陣
言陣者數十家,余盡掃而盡括之。形象人字,名曰人陣。順之為人,逆之為人,進之為人,退之為人。聚則共一人,散則各為一人,一人為一陣,千萬人生乎一陣,千萬陣合于一陣,千萬人動乎一人。銳在前而重在后;鋒為觸而游于周,其中分陰陽虛實,當受卸沖。為翼伏吐納,動靜合張。斗不可亂,進必相依,不依則危,人自不亂,亂亦隨整,人能自依。人必依人,又何可亂?高下下隨乎勢,長短廣狹變于形,人陣神然哉。
肅
號令一發三軍威懾,鼓進金止,炮起鈴食,颯奮麾馳。雨不避舍,熱不釋甲,勞不棄械,見難不退,遇利不取,陷城不妄殺,有功不驕伐,趨行不聞聲,沖之不動,震之不驚,掩之不奔,截之不分,是肅。
野
整者兵法也。礙于法則有機不投。兵法之精,無如野戰: 或前或卻,或疏或密,其陣如浮云在空,舒卷自如;其行如風中柳絮,隨其飄泊。迨其簿,如沙汀磊石,高下任勢;及其搏,如萬馬驟風,盡力奔騰。敵以法度之,法之所不及備;以奇測之,奇之所不及應;以亂揆之,亂而不失;馳而非奔,旌旗紛動而不踉蹌,人自為克,師自立威。見利而乘,任意為戰,此知兵之將所深練而神用者也。抑亦難哉。
張
耀能以震敵,恒法也。惟無有者故稱,未然者故托,不足者故盈,或設偽以疑之。張我威,奪彼氣,出奇以勝,是虛聲而致實用也。處弱之善道也。
斂
卑其禮者,頹敵之高也;靡其旌者,亂敵之整也;掩其精能者,萎敵之盛銳也;惟斂可以克剛強,惟斂難以剛強克。故將擊不揚以養鷙,欲搏弭耳以伸威,小事隱忍以圖大,我處其縮以盡彼盈。既舒吾盈,還乘彼縮。
順
大凡逆之逾堅者,不如順以導瑕。敵欲進,贏心柔示弱以致之進;敵欲退,解散開生以縱之退;敵倚強,遠鋒固守以觀其驕;敵仗威,虛恭圖實以俟其惰。致而掩之,縱而擒之,驕而乘之,情而收之。
發
制人于危難,扼人于深絕,誘人于伏內,張機設阱,必度其不可脫而后發。蓋早發敵逸,猶遲發失時。故善兵者,制人于無可逸。
拒
戰而難勝則拒,戰而欲靜則拒。憑城以拒,以恃者非城;堅壁以拒,所恃者非壁;披山以拒,阻水以拒,所恃者非山與水。必思夫能安能危,可暫可久,靜則謀焉,動則利焉。
撼
凡軍之可撼者,非傷天時,即陷地難,或疏于人謀。無是數者而欲撼之,非惟無益,亦且致損。故大將臨敵,犯可撼,戒不可撼,若故為可撼以致人之撼己,而因以展其撼,則又善于撼敵者也。
戰
逆戰數百端:眾、寡、分、合、進、退、搏、乘、迭、翼、緩、速、大、小、久、暫、迎、拒、綴、遇、諧于法。騎、步、駐、隊、營、陣、壘、行、鋒、隨、專、散、嚴、制、禁、令,都、試、嘗、比、水、火、舟、車、筏、梁、協于正。晝、夜、寒、暑,風、雨、云、霧、晨、暮、星、月、黑、雷、冰、雪、因于時。山、谷、川、澤、原、狹、遠、近、險、仰、深、林、叢、泥、坎、邃、巷、衢、逾、沙、石、洞、砦、塞、宜于地。
至展計則謀:心、揚、應、餌、誘、虛、偽、聲、約、襲、伏、挑、搦、抄、掠、關、構、嫁、左、截、邀、躡、踵、驅、卸。
握奇則自:牽、變、避、隱、層、裝、物、神、邪、鉆、返、魃、混、野、當、塵、煙、炬、耀、蔽、裸、空、飛、甚則不。無、沖、涌、擠、排、貫、刺、掩、蹂、夾、繞、圍、裹、蹙,厭、狠、暴,連、毗、懾、摧、戀、酣、并、陷、而施勇。再甚則饑,疲、創、困、孤、逼、降、破、欺、擒、憤、怒,苦、激、強、血、死、鏖、猝、驚、奔、殿、接、救、以經危。精器善使,展戰華夷,亶為名將。
搏
百法皆先著,惟戰則相薄,當思搏法,此臨時著也。敵強宜用抽卸;敵均宜用沖蹂;蒙首介騎,步勇挨之,往還擊殺,使敵無完隊則蹂也。以我之強當其弱,以我之弱當其強,而令強者先發,左右分抄,是謂制弱取勝。預立斷截開分,使敵突則納,敵沖則裂,卸彼勢而全我力,伏鋒以裹之,所謂強駑之末也。要皆相敵以用,然未戰必備其猝來;戰退以虞其掩至,而且北必緊旌,使敵不敢遽迫;勝必嚴追,使伏不得突乘。能如是,而后進可不敗,退可不死,與三軍周旋,風馳電薄間,無不得勝著也。銳而暇,靜而整,慎旃。
分
兵重則滯而不神,兵輕則便而多利。重而能分,其利自倍。營而分之,以防襲也; 陣而分之,以備沖也; 行而分之,恐有斷截;戰而分之,恐有抄擊。倍則可分以乘虛,均則可分以出奇,寡則可分以生變。兵不重交,勇不遠攫,器不隔施。合兵以壯威,分兵以制勝。統數十萬之師而無壅潰者,分法得也。
更
武不可黷。連師境上,屢戰不息,能使師不疲者,惟有更法。我一戰而人數應,誤逸為勞;人數戰而我數休,反勞為逸。逸則可作,勞則可敗。不竭一國之力以供軍,不竭一軍之力以供戰。敗可無虞,勝亦不擾。
延
勢有不可即戰者,在能用延。敵鋒甚銳,少俟其怠;敵來甚眾,少俟其解;征調未至,必待其集;新附未洽,必待其孚; 計謀未就,必待其確;時未可戰,姑勿與戰,亦善計也。故為將者,務觀乎彼己之勢,豈可以貪逞摧激而莽然一戰哉!
速
勢已成,機已至,人已集,而又遷延遲緩者,此隳軍也。士將怠,時將失,國將困,而擁兵境上,不即決戰者,此迷策也。有智而遲,人將先計; 見而不決,人將先發;發而不敏,人將先收。難得者時,易失者機,迅而行之,速哉!
牽
敵之不能猝勝者,惟或用牽法也。牽其前則不能越,牽其后則莫敢出。敵強而孤,則牽其首尾,使之疲于奔趨;敵狽而倚,則牽其中交,使之不能相應。大而廣,眾而散,則時此時彼,使之合則艱于聚,分則薄于守,我乃并軍一向,可克也。
勾
勾敵之信以為通,勾敵之勇以為應。與國勾之為聲援,四裔勾之助攻擊。勝天下者用天下,未聞己力之獨恃也。抑勾者乃險策,用則必防其中變。恩足以結之,力足以制之,乃可以勾。
委
委物以亂之,委人以動之,委壘塞土地以驕之。有宜用委者,多戀無成,不忍無功。
鎮
夫將志也,三軍氣也。氣易動而難制,在制于將之鎮。鎮矣,驚駭可定也,反側可安也,百萬眾可卻滅也。志正而謀一,氣發而勇倍,動罔不臧。
勝
凡勝者,有以勇勝,有以智勝,有以德勝,有以屢勝,有以一勝。勝勇必以智,勝智必以德,勝道務祈修。善勝不務數勝而務全勝,務為保勝。若覬小利,徒挑敵之怒,堅敵之心,驕我軍之氣而輕進,墮我軍之志而解紐,是為不勝。
全
天德務生,兵事務殺。頎體天德者,知殺以安民,非害民;兵以除殘,非為殘。于事作不攻自拔以全城,致妄戮之戒以全民,奮不殺之武以全軍。毋徽功,毋歆利,毋逞欲,毋藉立威。城陷不驚,郊市若故。無之而非全,則無之而非生矣。
隱
大將行軍,須多慎著,固已言周謹矣。然對壘克敵,率軍馭將,事多不測。擊一軍進止者,當表異以為士卒先;擊舉陣存危者,當計安以為三軍恃,且行不知所起,止不知所伏,顯象示人而稠眾莫識,刀劍森列之中,享藏舟之固者,大將有隱道也。
下卷衍部
善用兵者,明天數,辟妄說,廣推其役女(此處疑有誤),通文借傳不惜(費解)。對敵則蹙,眼、聲、挨、混、回。有用,至半,一,影響之中;致機于空,無,陰,靜,化于閑。忘,不示威能,斯為操縱由己,而底于自如之地也。兵至是乃極。
天
星浮四游,原無實應,帷當所居之地,氣沖于天,蒸為風雨云霧。及暈芝蕩搖諸氣,可相機行變。正應者惟陰陽寒暑,晦明之數而已。疾風颯颯,謹防風角;(疑為羊角)眾星皆動,當有雨濕;云霧四合,恐有伏襲;疾風大雨,隆雷交至,急備強弩。善因者,無事而不乘;善防者,無變而不應,至人合天哉。
數
用兵貴謀,曷可言數?而數亦本無。風揚雨濡,在天只任自然;凍堅潮停,亦是氣候偶合。況勝而旋敗,敗而復勝?勝而君王,敗而撲滅。舉爭將相之能,即未圖于人而人倏助;未傾于敵而敵忽誤;事所未意而機或符,皆以造數,而非以數域人。數系人為,天著何處。茍擁節專麾,止盡其在我者而已。若管郭袁李之學,可神而不可恃也。
辟
兵家不可妄有所忌,妄則有利不乘;不可妄有所憑,憑則軍氣不利。必玄女力士之陣不搜,活曜遁甲之說不事,孤虛風角日者靈臺之學不究。迅風疾雨,驚雷赫電,幡折馬跑,適而不惑。以人事準進退,以時務決軍機。人定有不勝天,志一有不動氣哉。
妄
讀《易》曰大過,曰無妄。圣賢以無妄而免過,兵法以能妄而有功。故善兵者,詭行反施,逆發詐取,天行時干,俗禁時犯,鬼神時假,夢占時 ,奇物時致,謠讖時倡,舉措時異,語言時舛,鼓軍心,沮敵氣,使人莫測。妄固不可為,茍有利于軍機,雖妄以行妄,直致無疑可也。
女
男秉剛,女秉柔。古之大將,間有藉于女柔者,文用以愚敵玩寇,武用則作戰驅軍,濟艱解危,運機應變,皆有利也。男不足,女乃行。
文
武固論勇,而大將征討,時用羽檄飛文,恒有因一辭而國降軍服者。士卒稍知字句,馬上詩歌,行間俚語,條約禁令,暇則使之服習,或轉相耳傳,自聞詔解義,不害上為君子師,儒者兵也。
借
古之言借者,外援四裔,內約與國,乞師以求耳。惟對壘設謀,彼此互角,而有借法乃巧。艱于力則借敵之力,難于誅則借敵之刃,乏于財則借敵之財,缺于物則借敵之物,鮮軍將則借故之軍將,不可智謀則借敵之智謀。何以言之?吾欲為者誘敵役,則敵力借矣;吾欲斃者詭敵殲,則敵刃借矣;撫其所有,則為借敵財劫其所儲,則為借敵物; 令彼自斗,則為借敵之軍將;翻彼著為我著,因彼計成吾計,則為借敵之智謀。己所難措,假手于人,不必親行,坐享其利; 甚且以敵借敵,借敵之借,使敵不知而終為借,使敵既知而不得不為我借,則借法巧也。
傳
軍行無通法,則分者不能合,遠者不能應。彼此莫相喻,敗道也。然通而不密,反為敵算。故自金、旌、炮、馬、令箭、起火、烽煙報警急外; 兩軍相遇,當詰暗號; 千里而遙,宜用素書,為不成字,無形文,非紙筒。傳者不知,獲者無跡,神乎神乎。或其隔敵絕行,遠而莫及,則又相機以為之也。
對
義必有兩,每相對而出。有正即有奇,可取亦可舍,對。古今智能人,已籌略時宜可否戰陣利害中,機法生焉,變化神焉,有無窮之用矣。
蹙
謀于心曰計,力可為曰能。從心運者虛,見諸為者實。有能則能,雖半計而亦可生計。無能則無從計,而善計皆空,籌空非計也。計必計所能,不惟攻擊能,戰守能,即走、降、死亦必要之能。故善兵者,審國勢己力,師武財賦,較于敵以立計。英雄善計者而有束手之時,無用武之地,勢不足而能不在耳。蹙之者,于勢能未展之日,則俯首受制。無計之計,止有一避; 無智之智,止有一拙; 無能之能,暫庸一屈。角而利,爪而距,不可蹙矣。
眼
敵必有所恃而動者,眼也。如人有眼,手足舉動斯便利。是以名將必先觀敵眼所在,用抉剔之法。敵以謀人為眼,則務祛之; 以驍將為眼,則務除之; 以親信為眼,則能疏之; 以名義為眼,則能壞之。或拔其基根,或中其要害,或敗其密謀,或離其恃交,或撤其憑藉,或破其慣利,此兵家點眼法也。點之法,有陰、有陽;有急、有緩。人有眼則明,弈有眼則生。絕其生而喪其明,豈非制敵之要法哉?
聲
師以義動者,名兵也。驚使數動者,虛喝也。敵夜營,遙誘以火鼓,實迫以金炮,制敵前后,伏兵兩路,使敵逃竄而殲之者,啄木畫也。轟轟隱,隱萬人咤自云端,名曰天唳。潺潺泡泡,千軍噪營于內,名曰鬼彗。為潮迥,如寉清,震敵上下不知所由,使敵自相擊撞,而滅絕之者,落物朔也。
挨
天道后起者勝,兵法攖易不攖難。威急者,索也;銳犀者,挫也。敵動我能靜,我起乘敵疲。敵挾眾而來,勢不能久,則挨之;其形窘迫急欲決戰,則挨之;彼戰為利,我戰不利,則挨之;時宜守靜,先動者危,則挨之;二敵相搏,必有傷敗,則挨之;有眾而猜,必至自圖,則挨之;敵雖智能,中有摯者,則挨之;……天時將傷,地難將陷,銳氣將墮,則挨之。挨之乃起而收之,則力全勢遂,事簡功多。古之所為寧觀,為徐俟,為令彼自發,皆是也。可急則乘,利緩則挨,故兵經有后義。
混
混于虛,則敵不知所擊;混于實,則敵不知所避;混于奇正,則敵不知變化; 混于軍、混于將,則敵不知所識。而且混敵之將以賺軍,混敵之軍以賺將,混敵之軍將以賺城營。同彼旌旗,一彼衣甲,飾彼裝束相貌,乘機竄入,發于腹,攻于內,殲彼不殲我,自辨而彼不能辨者,精于混也。
回
凡機用于智者一則間,用于愚者二而間,數受欺而不悟者三而間。間三而迫奇莫測,間二而迫人所度,間一而迫顛于法。一出二,二出三,隨勢變還,隨形變遷;三迫二,二迫一,隨勢歸復,隨形歸復。
半
凡設謀建事,計有十,行之僅可得五,其半在敵與湊合之間;行有十,而計止任其五,其半在敵與湊合之間,故善策者多惕。曰:我能謀人則思敵能謀我者,至視天下皆善謀,則可制天下之謀生。是精謀勇戰操其一,敵之抵應操其一,地天機宜操其一,必諦審。夫彼多而此少,或此多而彼少,能合于三,其勢乃全。故當以半而進乎全也。
一
行一事而立一法,寓一意而設一機,非情之至也。故用智必沈其一,用法必增其一,用變必轉其一,用偏必照其一,任局必出其一,行之必留其一,盡之必翻其一。蓋以用為動,以一為靜;以用為正,以一為奇。上于一,余一不可。一不可一余,一不可一盡。二余一則三之,四余一而五之,京秭嘴(溝的誤寫)澗而極正之,此阿祗那由之,不可無量也。余一也,精之致也。
無
大凡著于有者,神不能受也。不能受,則遇事不自持,其不血衄者希矣。故善用兵者,師行如無,計設若否,創奇敵大陣而不動,非強制也。略裕于學,膽經于陣,形見于端,謀圖于朔。
影
古善用兵者,意欲如此,故為不如此以行其意,此破軍擒將降城服邑之微法。今則當意欲不如此,故為不如此,使彼反疑為意欲如此,以行其意欲不如此,此破軍擒將降服城邑之微法。故為者,影也; 故為而示意者,影中現影也。兩鑒懸透三千丈哉。
空
敵之謀計利,而我能空之,則彼智失可擒。虛幕空其襲,虛地空其伐,虛伐空其力,虛誘空其物。或用虛以空之,或用實以空之,虛不能則實詭,幻不赴功; 實不能則虛就,其寡奇變。運行于無有之地,轉掉于不形之初,杳杳冥冥,敵本智而無所著其慮,敵未謀而無所生其心。洵空虛之變化神也。
陰
陰者,幻而不測之道。有用陽而人不則其陽,則陽而陰也;有用陰而人不測其陰,則陰而陰也。善兵者,或假陽以行陰,或運陰以濟陽,總不外于出奇握機,用襲用伏,而人卒受其制,詎謂陰謀之不可以奪陽神哉。
靜
我無定謀,彼無敗著,則不可動;事雖利而勢難行,近稍遂而終必失,則不可動。識未究底,謀未盡節,決不可為隨數任機之說。當激而不起,誘有不進,必度可動而后動,雖小有挫,不足憂也。妄動躁動,兵家極戒。
閑
紛糾中,沒掂之設一步,人不解其所謂; 寬緩處,不吃緊立一局,似覺屬于元庸,厥后湊乎事機收此著之用,則所關惟急。是知兵有閑著,兵無閑著。
威
強弱任于形,勇怯生于勢,此就行間之變化言也。若夫善用兵者,運夫天下之所不及覺,制夫天下之所不敢動,戰夫天下之所不能守,扼夫天下之所不得沖,奔夫天下之所不可支,離夫天下之所不復聚。威之所懾,未事革兵而先已懼,既事兵革而莫能敵。一時畏其人,千秋服其神。
忘
利害安危,置之度外,固必忘身以致君矣。而不使士心與之俱忘,亦非善就功之將也。然而得其心者,亦自有術:與士卒同衣服,而后忘夫邊塞之風霜;與士卒同飲食,而后忘夫馬上之饑渴;與士卒同登履,而后忘夫關隘之險阻; 與士卒同起息,而后忘夫征戰之勞苦;憂士卒之憂,傷士卒之傷,而后忘夫刀劍鏃戟之瘢痍。事皆習而情與周,故以戰斗為安,以死傷為分,以冒刃爭先為本務,而不知其蹈危也。兩忘者,處險如夷,茹毒如飴也。
由
進止戰守由于我,斯有勝道。由我則我制敵,由敵則為敵制。制敵者,非惟我所不欲,敵不能強之使動,即敵所不欲,我能致之不得不然也,甚至敵以挑激之術,起我憤慍,能遏而不應,斯真能由我者。
如
以智服天下,而天下服于智,智固不勝; 以法制天下,而天下制于法,法亦匪神。法神者,非善之善者也。圣武持世,克無城,攻無壘,戰無陣,刃游于空,依稀乎釀于無爭之世,則已矣。淵淵涓涓,錚錚鏗鏗。
自
性無所不含,狃于一事而出,久則因任自然。故善兵者,所見無非兵,所談無非略,所治無非行間之變化。是以事變之來,不得安排計較,無非協暢于全經。天自然,故運行; 地自然,故未凝; 兵自然,故無有不勝。是以善用兵者。欲其自然而得之于心也。詩曰:左之右之,無不宜之; 右之左之,無不有之。
[鑒賞]
《兵經百篇》,亦名《兵經》。因為以一百字條的形式結構全書,所以又稱《兵經百字》、《兵法百家》、《兵法百言》。作者揭暄,字子宜,生卒年不詳,明末廣昌(今江西廣昌)人。少年時便才志過人,“深明西術”,精通天文,喜歡與人談論軍事,“其言多古今所未發”。著成《兵經》皆古所未有。學者吳炳讀后驚呼:“此異人異書也!”清兵攻陷南京,揭暄曾舉兵奮起抗擊,聲名一時響震江蘇、福建。最后,終因大局難以挽回,無法施展自己的雄才奇略,他便隱居山林郁郁而死。
《兵經百篇》現存本系清末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清末人候榮對幾種手抄本校勘、釋義、引證而刊行于世的。全書分為上、中、下3卷: 上卷智部,28個字條,主要論述以謀致勝的方法原則; 中卷法部,44個字條,主要闡明組織指揮和治軍的方法原則;下卷衍部,28個字條,主要指出作戰中應注意的一些問題。為了鑒賞的方便,考慮到字條間的相互關系,我們在輯錄原文時,將個別字條的先后順序作了少許調整。
一百個字條,宛若一百顆小小的珠子。初看各自獨立互不相關,待仔細研讀之后,似又可將其系成幾串。筆者就此作一嘗試,大膽地打破原來各卷的體例安排,歸納為五個方面的問題。這樣,閱讀起來,或許能減少全書“結構松散”的感覺,便于理解和掌握其中的主要內容。未知讀者諸君以為然否?
一、決策與奇謀方略
“興”者,興師、舉兵之謂也。善戰者先勝而后求戰,不善戰者先戰而后求勝。兵動非同一般,興兵作戰務必慎重決策。決策分為宏觀決策和微觀決策兩種。“如”字條即是從宏觀著眼,就戰略決策而言,力求運用威懾力量,盡可能制止和避免直接的軍事沖突;“自”字條則是指在兩軍角逐的戰場上,要求指揮員把握軍事斗爭的客觀規律,做到戰術上運用自如,使用兵力得心應手。“半”字條告訴軍事決策者,凡事要想到多種可能,多準備幾手,以“多惕”來追求全策全勝。那么,怎樣才能從戰略全局上奪取勝利呢?“勝”字條講述了一般的原則,提出了“勝勇必以智,勝智必以德”的思想,把政治作為取勝的首要條件,并且闡明了“善勝不務數勝而務全勝”的觀點。“眼”字條,則更加明確地指出,應當抓住對戰爭勝負起關鍵作用的主要矛盾。接著,“全”字條又從戰爭目的的高度,展示了“全勝”的意義和內容。戰爭的軍事目的與政治目的的一致性,要求作戰指導堅持“上兵伐謀,其次伐交”的方針。“不攻自拔以全城,致妄戮之戒以全民,奮不殺之武以全軍”,奪取全勝也是軍事謀略所追求的最高目標。正如“利”字條所強調的,“必度益國家,濟蒼生,重軍威”,軍隊的作戰行動,一定要考慮到對國家是否有利,對百姓有無好處,能否顯示國家和軍隊的威力。因此,“蹙”字條說,善于用兵的人,要察知本國的力量,經濟和軍事戰備狀況,在與敵國進行認真切實的比較之后,再制定相應的對策。如果整個形勢不宜于立即決戰的,就要耐心等待時機。“延”、“挨”兩字條講的就是拖延時間,以俟有利時機后發制人。不過,“延”字條主要是從戰略上審時度勢,先勝而后求戰;“挨”字條則是從戰術范圍內,從交戰的具體時節上,針對敵方現實的或者潛在的矛盾,把握好火候,做到“可急則乘,利緩則挨”。在進攻作戰中,與“延”、“挨”相反,要求的是“速”,即速戰速決,無論是戰略行動,還是戰役戰術行動,一概如此。而控制戰爭的機運,依靠的是充分發揮指揮員的主觀能動性,所以“辟”、“數”兩字條,提出了反對戰爭觀上的天命論,進而在用兵指導上排除奇門遁甲之類的邪說。軍隊一旦掌握了行動的自由,就標志著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這便是“由”字條講述的內容。要取得主動權,必須善于創造和捕捉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敵的戰機。“機”字條說,態勢上安危所系的地方是戰機,戰局的轉折點是戰機,事情的緊要關頭是戰機,時間恰到好處是戰機。有眼前還是戰機,轉眼之間就不是戰機的。有抓住被利用了是戰機,稍一放松就不成其為戰機的。俗話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戰場上的機遇,隨時間變化而變化,隨條件變化而變化。恰到好處地把握時機,適時地運用兵力,才能乘虛入隙,殲敵奪地。“發”字條集中地講了時間、時機,進一步強調了把握戰機的重要性。戰爭是爭奪最激烈的一個領域,兵爭與敵拚殺,將爭謀高一籌,指揮戰爭的統帥力爭決定戰局轉換的戰機。“爭”、“先”字條反映出積極的競爭意識,強烈的競爭觀念。爭機、爭利、爭主動權,都要依靠英勇頑強地去爭奪。就作戰形式而言,雖然有攻有守,但是作為軍人,時時刻刻所想的,事事處處所做的,都應當是著著爭先,為著力爭主動。“先”字條講了“四先”:不用爭奪而制止了爭奪,不用戰爭而制止了戰爭,在戰爭還未爆發時,就先勝于無形,這是“先天”;不依靠短兵相接的戰斗取勝,而靠預先設置的計謀取勝,這是“先機”;搶先占領敵我雙方必爭之地,這是“先手”;軍隊剛一行動,就挫折抑制了敵人的計謀,這是“先聲”。“猛虎不據卑址,勍鷹豈立柔枝?”“勢”字條以十分形象的比喻開頭,指出善于用兵的人,都很重視觀察研究和利用作戰所處的態勢。因為同樣的兵力,在有利的態勢下,便如猛虎添翼;在不利的態勢下,則似鷹折雙翅,欲飛而不能飛。
決策已定而沒有計謀,軍隊也不可能作戰。在軍事謀略學中,“計”與“謀”常常同用或者連用。計有千條,法有萬端,《兵經百篇》談計謀,抓住了運用計謀的一個關節點,即研究敵將,因人設謀,因情施計,謀活而不謀死。在籌劃謀略時,要根據情況的發展變化和時間的不斷推移,把計劃盡可能地做到完善。所謂計謀,實際上就是詭道。一個“妄”字,反映了軍事斗爭最突出的特點,兵不厭詐。又一個“斂”,指出了作戰雙方都在竭力隱蔽自己的真實企圖。因而,或虛張聲勢(“張”字條),長自己威風,滅敵人志氣,出奇兵制勝敵人;或示聲于敵(“聲”字條),使敵人聞其聲而不見其形,調虎離山,聲東擊西;或大智若愚(“拙”字條),隱藏自己的才智而故意顯示愚笨,讓敵人看不起自己,疏忽懈怠,而我運籌帷幄,伺機行動;或進行戰術的偽裝(“混”字條),以假亂真,混水摸魚;或隱真(“無”字條)示假(“影”字條),布設計謀象是若無其事,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虛而實之,實而虛之,使敵人捉摸不定。“空”字條說,施計用謀,就其目的來說,就是引導己方的行動步步接近既定目標,直至達到最終目的,同時用盡各種方法造成敵人失誤。“誤”字條提出了九種誤敵之法:“或用我誤法以誤之,或因其自誤以誤之。誤其恃,誤其利,誤其拙,誤其智,亦誤其變。虛挑實取,彼悟而我使誤,彼誤而我能悟。”“順”字條則提出順敵心理,因勢利導,順以導瑕,誘敵致誤。當然,許多奇謀方略的成功運用,不僅借助于戰場上的示形布勢,還常伴之以“唇槍舌劍”、“口誅筆伐”的巧妙配合。《兵經百篇》中的“言”、“文”兩字條認為,一個聰明的指揮員,克敵制勝的功力,不只是表現在劍鋒上,還潛藏于筆鋒、舌鋒之上。這一切,誠如“撼”字條講述的,就是為了創造條件,使自己不被敵所戰勝,然后等待和尋求敵人可能被我戰勝的時機。
二、應變與預先準備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世間萬事萬物,無時無處不在變化;兵書千章萬法,突出一個“變”字。《兵經百篇》,無不包含著“變”的思想,并且專列“變”字一篇。戰場情況瞬息萬變,作戰方法亦應隨機應變,靈活多變。當變不變,無異于刻舟求劍。因此,“回”字條說,制勝術,能否重復使用,重復的次數多少,都必須根據敵情的變化而變化。自古以來,兵家認為有成法而無定法。靈活機動,臨機應變,這是軍事指揮上的基本特點。“一”字條講,要力求比敵手智高一籌,法多一種。那些“行一事而立一法,寓一意而設一機”的指揮員,是造詣不深的表現。“生”就是指善于創造、創新戰法,反對照搬照套,提倡靈活用兵。“野”字條主要講超常用兵,變化無常,以力求做到“制人而不制于人”。我變敵亦變,敵變我再變。“累”字條指出,針對敵手策略的變化,及時改變自己的策略,再從自己的新策略,推斷敵人可能重新改換的策略。于是,事先于暗中準備“破彼之破”的一手。如果說,這是就縱向而言的話,那么“疊”字條則是從橫向來說的,即同時使用幾個連環相扣的計謀,全方位多角度的用智,達到一次作戰行動的成功。而“活”字條則進一步指出,沒有多種方案的策略,是將要陷人貧困的策略。它談到了靈活運用戰術的幾個方面:掌握時間方面的靈活、控制空間上的靈活、選擇道路方面的靈活、兵力機動方面的靈活,同時,又強調了靈活要有一定的范圍。“對”字條說,任何事理都有兩方面,它們往往是相對地存在著。有正即有奇,有攻就有守,有可取的就有可舍的,這就是對立統一。“拒”字條說,拒是攻中之守,所以防守時一定要考慮既能應付一般情況,又能應付復雜危急的情況,既可暫拒又可久守,敵人不來進攻時認真籌劃作戰方案,敵人來攻時就能確保處于有利的地位。對于不能迅速打敗的敵人,“牽”字條指出用牽制的辦法對付。古往今來,聰明能干的人在運籌用兵方略時,從相宜與不相適宜,從布陣的有利與有害兩方面中分析情況,就能確定出正確的戰法,變化莫測,就有無窮無盡的運用之妙。制勝之道,是在對立中求統一,從相反中求相成;計謀韜略,無非是活用軍事辯證法。“巧”字條中包含著更加生動的辯證法思想,它提出了“巧”的五個方面:一為用巧的基本思想是因敵制變;二為用巧的基本法術是欺騙敵人,造成敵人犯錯誤;三是用巧貴在創新,用謀施術勝在新奇;四是用巧要善于隱蔽自己的企圖;五是用巧要大膽而靈活,敢于反常用兵。“左”字條專門講反常用兵,要學會從相反中求相成,以患為利,以迂為直,以逆為順,以難為易,從不可能中找可能,逆著敵人的心理行動,背著敵人的判斷決事。因此,“讀”字條提出,在學習和運用古代兵法時,“人泥法而我鑄法,人法法而我著法,善用兵者,神明其法。”
所謂“善于應變”,從現象上講,似乎是“隨機”產生的,然而就本質而言,這種“應變”,不僅來自事先對戰爭發展變化的準確預見(“預”字條),來自預先處置情況的經驗積累,而且是因為事先有了必要的精神準備和物質準備。“天”字條,指善于利用有利的政治形勢和軍事時機,提早做好準備,應付任何突然來臨的事件。正如“閑”字條所說,“兵家寧可有閑著,不可無備著。”“周”字條也講到,指揮員制定計劃,進行準備一定要周密細致,防止紕漏。對每一個關系到影響戰斗力的各種因素都要一一注意,大到行軍作戰(“行動”)、駐防轉移(“移”)、安營扎寨(“住”)、通信聯絡(“傳”)、后勤補給(“糧”),小到穿衣、吃飯、睡覺,都不能給敵以可乘之隙,不存任何疏忽。亦如“謹”字條所說,身處沙場,必須時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和不懈的戰斗意志,隨時隨地都得謹慎。“隱”字條講,指揮員統兵打仗,多數情況下都能謹慎持重從事,但在兩軍對壘中去進攻敵人,會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情況。作為將領,在刀光劍影中,要能沉著冷靜,隨機應變以穩操勝券。作戰雙方在進行力量競賽中,指揮員的職責是,既要施計消滅敵人,又要設法保存自己,既要努力識破敵人的詭計,又要盡可能如“陰”字條所講的那樣隱蔽自己的行動企圖。隱蔽自己的行動企圖,目的是為了達到出敵不意,攻其不備。“秘”字條說,總括用謀之大事,在于隱機藏略,不暴露企圖。“謀成于密,敗于泄。三軍之事,莫重于秘”,要做到“一人之事,不泄于二人; 明日所行,不泄于今日”,要求不“泄于語”、不“泄于容貌”、不“泄于神情”,不“泄于夢寐”。
三、了解和判斷敵情
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指揮員的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是建立在對敵我力量分析對比的基礎之上。“較”字條提出的力量比較,是從軍隊的武器裝備、戰術技術、兵員的數質量、布勢的利弊、指揮員智能的高低等多種因素綜合的分析對比,并且從對戰爭勝負影響的大小,將這些因素進行了先后排列。排在最前面的是指揮員的戰略水平、智能高低;其次是部隊所處的態勢、兵員的數質量、戰術技術和武器裝備。在冷兵器時代,武器裝備的差別不是太懸殊,所以它被排到了最后。正因為武器裝備的優劣不十分明顯,相對地說來,士兵掌握武器裝備的技術也比較簡單。與之相適應,將帥的謀略智能對戰爭勝負的影響顯得特別突出、特別重要。“識”字條就專指識敵將,即識敵將之才、識敵將之謀、識敵將之能等。在古代戰場上,交戰雙方的智力角逐,基本上表現為雙方指揮員的斗謀斗法,因此可以說,識敵將是知彼的主要內容。識敵將的方法,除了歷史地考察他們的性格、品德、用兵習慣和才識等等,還要靠雙方的交戰來加深了解。例如,偵察敵軍的部署,就可以了解敵軍將領的才能;用假裝敗退來欺騙敵人,用小利引誘敵人(“委”字條),就可以了解敵軍將領的性格和品德;用佯攻來驚動敵人,用襲擾來攪亂敵人,就可以了解敵軍將領的指揮調度能力,這些都是為了察明敵人的作戰能力,對敵情進行正確的分析。此外,偵察敵人所處的地形情況,是了解敵情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地”字條論述的思想,是作者揭暄在深入研究《孫子兵法》的基礎上,總結戰國以后的戰爭經驗,給指揮員提出的需要細心思索的具體問題,其中“山川以人為固”的觀點,正確地評估了人與地的關系。地無兵不險,兵無地不強;地利可以為敵我雙方爭奪和利用;地利只有在軍事家正確運用時,才會變得堅不可摧。了解和分析敵情,是為著對敵情作出判斷。“測”字條說,判斷敵情是為了避實就虛地進攻敵人。要判斷敵人是怎樣判斷我方的,就要故意顯示弱點來欺騙它,以便發揮我方的長處。判斷錯誤,就會中敵人的詭計。敵我雙方互用詐術,都在互相欺騙,使戰場情況忽真忽假、時虛時實,善于用心計的將軍,對情況一定要細心分析認真思考,這就包含著“疑”,從疑中提出問題。因此,在作出判斷定下決心之前,要提倡懷疑。不過,如果懷疑過了頭,疑而成狐,以致影響作出判斷和定下決心,那就會誤大事。貴在疑而有度,這就是《兵經百篇》所說的“疑”。
四、治軍和組織指揮
“肅”者,肅然嚴整。一支訓練有素、治理有方、令行禁止的軍隊,蘊藏著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威懾力量,才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否則,治理混亂無所約束,必然不堪一擊。如果說,軍威和將令來自嚴明的軍紀和嚴格施行的賞罰制度,那么士兵的忘我精神,則靠指揮員的模范行動和關心愛護部下的將德來煥發。這便是“威”字條和“忘”字論述問題的不同與聯系。“忘”字條強調指揮員與士卒同衣、同食、同住、同行,“憂士卒之憂,傷士卒之傷”,部隊就會忘卻風霜饑渴、攻關征戰之苦。正如“勵”和“銳”字條所說,振奮和激發士兵拚死殺敵的精神,培養出虎威雄風的精銳之師,便可無敵于天下。而要調動部下的積極性,必須做到對部隊愛與嚴的結合。“勒”和“馭”兩字條,分別講了對部隊和將領都要嚴加約束與控制。進行軍事斗爭,發揮的是整體力量,團結才能步調一致。團結才有力量。“結”和“輯”字條從團結部下,講到君臣將相和國家的團結、睦鄰的友好。
治軍練兵,旨在提高部隊的戰斗力。“練”字條講,三軍經過反復訓練,彼此互相協調,前后互相依恃,動則步調一致,止則整齊化一。除了嚴格的訓練,還要進行科學的戰斗編組。揭暄認為,在古代戰爭中,軍隊的戰斗編組到作戰方式,表現出單一化、模式化,缺乏應有的活力。因此,他在“鋒”字條中設想“更立九軍”,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建立九支特種部隊。“九軍”和陣列中各戰斗部分協調一致。發揮整體功能,達到“隅則各御,合則兼出,可伸可縮”。值得一提的是,《兵經百篇》專門列有“女”字條,從男女的秉性之差,論述婦女的特殊作用,提出“男不足,女乃行”,把吸引婦女寫進兵法,在“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的封建社會中產生的兵法上是很少見的。古代戰爭的作戰方式,十分注重陣法。“陣”字條對古代的陣法進行研究后,設計出神奇的“人”陣”:從正面看是人字,反面看也是人字;前進時是人字,后退時還是人字;全陣集中在一起是一個人,散開又是各個單獨的人;一個人為一陣,千萬人又組成一個陣,千萬個陣合成一個陣,千萬人行動起來又象一個人一樣協調一致。總之,“人”陣的真實含義,在于把較為固定的陣法模式,變為靈活機動的用兵之道。“陣”字講陣法,而“戰”、“搏”兩字條講戰法。“戰”字條共列185個字,分為“諧于法”、“協于正”、“因于時”、“宜于地”、“展謀”、“握奇”、“施勇”、“經危”八類。“搏”字條特別指出了軍事斗爭的特點,認為制勝之法不可“先著”,只能隨機應變,臨機處置。研究戰法,不在于學會多少具體的打法,而在于不斷提高隨機應變的能力。因此,“轉”字條說,善于用兵的人,能扭轉敵主我客的被動局面,改變敵我兵力的對比,變換敵逸我勞的情況,改變敵我利害的態勢,力挽危難的局面,克服驕傲暴躁的情緒。由是,“更”字條強調兵不可濫用,要利用時機輪換休整部隊,以便反勞為逸。“分”字條要求指揮員學會在集中兵力的前提下,分散配置部隊的本領,提出了“兵重則滯而不神,兵輕則便而多利”的思想。
治軍與組織指揮的關鍵,在于指揮員的素質和思想修養。“鎮”字條揭示了將帥的思想修養與用兵取勝的關系,“造”字條描述了軍事將領的形象,“將”字條則就指揮員的性格特征、能量氣度進行了專門論述,從知識結構的角度,將高級指揮員分為儒將、勇將、心將、巧將、藝將等類型,并且進一步認為,一個指揮員如果能同時具備以上各種類型將領的素質,就會用兵如神,戰無不勝。“任”、“材”、“能”、“恤”等字條;都是講的用才任將、用賢任能、愛惜人才、愛護部隊的原則和藝術。作為將領,除了需要有獨立自主的指揮權,但同時又不能離開人才群體的集體智慧,要做到重視人才,大膽合理地使用人才。權力只有與智慧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才能真正運用好權力,智慧才能得到充分有效地發揮。
五、用間與瓦解敵軍
這方面字條的數量雖說不多,但其中有些字條的篇幅,卻要算是比較長的。例如,“借”字條長達250個字,它全面地講述了“借敵”之法,即借敵之力、刃、財、物、將、謀等諸多方面,歸納為一點,就是制造敵方的矛盾,利用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敵的各種矛盾。“知”字條把竊取敵人的軍事情報,獲得戰場信息,察明敵人的實際情況,做到知彼的方法概括為四個方面,一是利用與敵方有交往的人員,從敵軍內部人員的情報中,了解敵人的計謀;二是派遣間諜,從諜報材料中了解敵人的虛實情況;三是組織偵察,了解敵人的有關行動;四是利用當地的向導,了解作戰區域內的地形狀況。接著,“間”字條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十六種用間的方法,即生、死、書、文、言、淫、歌、賂、物、爵、敵、鄉、友、女、恩、威,巧妙地使用間諜,除掉敵人的心腹,殺掉敵人的愛將,打亂敵人的作戰計劃。“勾”字條中提出的“勝天下者用天下”的思想,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種可以利用的條件,盡可能地爭取和團結一切可以爭取和團結的力量,建立廣泛的軍事與政治同盟,目的在于孤立敵人,或者是為了打擊主要的敵人,防止樹敵過多,避免腹背受敵。并且,為了應付詭詐機變的情況發生,既要有“勾”之術,又要有防變之策,堅持“結”與“制”兩手并用的方針,明則以恩結交,暗中用力量控制,才能保證萬無一失。
總之,《兵經百篇》大大豐富和發展了前人的軍事思想,并且有不少獨創的見解,至今仍不失其存在和借鑒的價值。但是,它畢竟是封建時代的兵法,難免滲雜著一些糟粕性的內容,少數字條中的某些觀點還前后矛盾,在此略舉幾例。譬如,“數”、“辟”兩字條,都是反對戰爭觀上的天命論,認為卜卦算命是迷信的方法,不要去研究,這無疑是值得肯定的。可是,“材”字條卻又將道術之士,列為大將股肱羽翼的“九士”之一;“言”、“妄”兩字條中提出假托鬼神、吐狂言、說夢話,“鬼神時假,夢占時托”;“勵”字條中還提出“詭之以術”,運用封建迷信的方式來激勵士氣。此外,“能”字條拋開人才成長的實踐條件,把人的勇智說成是由于“氣散四肢”和“氣聚中虛”造成的,這當然是毫無科學根據的唯心主義觀點。有些字條又將某些相對正確的東西絕對化、片面化,自然難免失之偏頗。例如,“先”字條的“能用先者,能運全經矣”;“趨”字條將“師貴徐行”推向極端等等,都是不足取的。盡管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我們不應當苛求于古人,但是對于其中的封建糟粕也不可良莠不分,囫圇吞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