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蘇軾·超然臺記》散文名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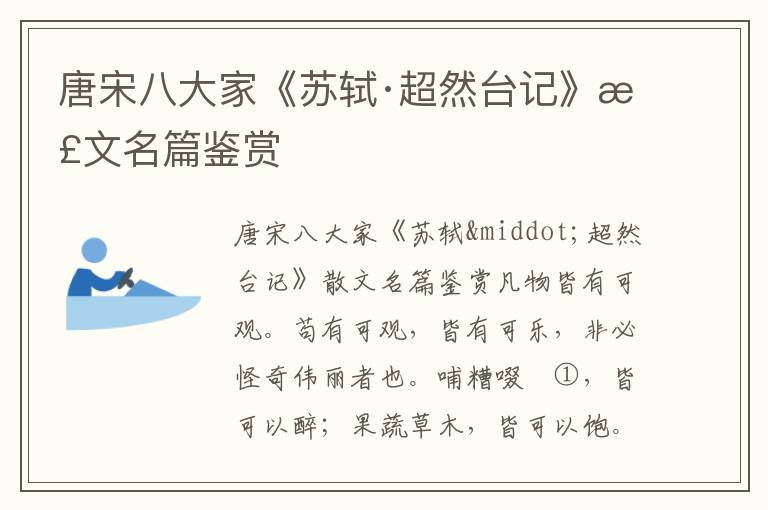
唐宋八大家《蘇軾·超然臺記》散文名篇鑒賞
凡物皆有可觀。茍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zhèn)愓咭病2冈汔ㄡr①,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
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zhàn)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②之矣。彼游于物之內(nèi),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nèi)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復(fù),如隙中之觀斗,又焉知?jiǎng)儇?fù)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錢塘移守膠西③,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蔽采椽④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⑤,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發(fā)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fēng)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
于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bǔ)破敗,為茍完之計(jì)。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shí)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⑥,出沒隱見,若近若遠(yuǎn),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⑦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吊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fēng)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疏,取池魚,釀秫酒⑧,瀹脫粟而食之⑨。曰:樂哉游乎!
方是時(shí),余弟子由適在濟(jì)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于物之外也。
【注】
①哺(bù不)糟啜醨(lí離):吃美食,喝美酒。哺,吃。糟,酒糟。醨,薄酒。②蓋:蒙蔽。③膠西:漢置膠西郡,宋為密州。今山東高密。④采椽:從山中采來椽木。比喻不加修飾,粗糙樸實(shí)。⑤歲比不登:連年收成都不好。⑥馬耳、常山:都是山名,在密州以南。⑦盧敖:秦博士,傳說隱于盧山,修道成仙。⑧秫(shū熟)酒:高粱酒。⑨瀹(yuè月):煮。脫粟:指糙米。
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蘇軾因?yàn)榉磳ν醢彩兎ǎ瑸樾曼h所不容,由杭州通判改任密州太守。熙寧八年(1075),密州政局初定,他便開始治園圃,潔庭宇,把園圃北面的一個(gè)舊臺修葺一新。他的弟弟蘇轍給這個(gè)臺取名叫“超然”。故此,蘇軾寫了這篇《超然臺記》。
本文意在說明,超然物外,就可以無往而不樂,即把一切事物都置之度外,無所希冀,無所追求,與世無爭,隨遇而安,就不會有什么煩惱,能成為一個(gè)知足常樂的人。這是用莊子“萬物齊一”的觀點(diǎn)來自我麻醉,以曠達(dá)超然的思想來自我安慰。管它什么禍福,什么美丑,什么善惡,什么得失,通通都一樣。自己屢遭貶謫,每況愈下,也就不足掛齒,可以逆來順受,無往而不樂了。
第一段,從正面論述超然物外的快樂。“凡物皆有可觀。茍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一切物品都有可以滿足人們欲望的作用,假如有這種作用,都可以使人得到快樂,不一定非要是怪奇、偉麗的東西。實(shí)際上并非如此,物有美丑、善惡之分,愛憎自有不同,人各有所求,其選擇也不能一樣,所以很難“皆有可樂”。蘇軾是以“游于物外”的超然思想看待事物,所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落筆便暗寫“超然”,直接提出“樂”字為主線,然后舉例加以證明。“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是說物各有用,都可以滿足欲求,給人快樂。推而廣之,人便可以隨遇而安,無處不快樂了。四個(gè)“皆”字使文意緊密相連,語勢暢達(dá),渾然一體。
第二段是從反面論述不超然物外必會悲哀的道理。求福辭禍?zhǔn)侨酥G椋驗(yàn)楦?梢允谷烁吲d,禍會令人悲傷。但是,如果人不能超然物外,任隨欲望發(fā)展,必然陷入“游于物內(nèi)”的泥潭。物有盡時(shí),很難滿足無止境的欲求。而且事物往往被某些現(xiàn)象掩蓋著本來的面目,美丑不一,善惡難分,禍福難辨,取舍難定。事物的假象常常令人頭昏目眩,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超然物外,就會盲目亂撞,結(jié)果必然招來災(zāi)禍,造成滅頂?shù)谋А?/p>
最后一段敘述移守膠西,生活初安,治園修臺,游而得樂的情景。先是描寫移守膠西,其中用了三個(gè)對偶句,組成排比句組,語調(diào)抑揚(yáng)起伏,氣勢充沛,使杭、密兩地形成鮮明對比,說明了蘇軾舍安就勞、去美就簡的遭遇。這既是紀(jì)實(shí),也是以憂托喜的伏筆。其次是“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是寫初到膠西后年成不好,政局動亂,生活艱苦。再次寫憂,以見喜之可貴,樂之無窮。“處之期年,而貌加豐,發(fā)之白者,日以反黑”,意外的變化帶來無限喜悅。“余既樂其風(fēng)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自己愛上了膠西,百姓也愛戴太守。官民相愛,必然官民同樂。由苦變樂,真是無往而不樂。最后是修臺游樂。先交代臺的位置、舊觀和修繕情況,利舊成新,不勞民傷財(cái),含有與民同樂之意。后寫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流露出無比喜愛的感情。再寫登臺四望,觸目感懷,見景生情,浮想聯(lián)翩,所表現(xiàn)的感情十分復(fù)雜。時(shí)而懷念超然物外的隱君子,時(shí)而仰慕功臣建樹的業(yè)績,時(shí)而為不得善終的良將鳴不平。這正表現(xiàn)了作者想超然物外,而實(shí)際上又很難完全超然處之的矛盾心情:有懷念,有仰慕,有不平。
本文的最大特點(diǎn)是用“樂”字貫串全文,先寫超然物外,就無往而不樂,不超然物外,則必悲哀,正面寫樂,反面寫悲,悲是樂的反面,終不離樂字。再寫初到膠西之憂,初安之樂,治園修臺,登覽游樂。以游去襯托樂,愈顯出更加可喜可樂。以樂開頭,以樂結(jié)尾,全文處處現(xiàn)樂。
后人評論
賴山陽《纂評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七:“鋪敘宏麗,有韻有調(diào),讀之萬遍不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