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宗泰《游鐘山記》原文,注釋,譯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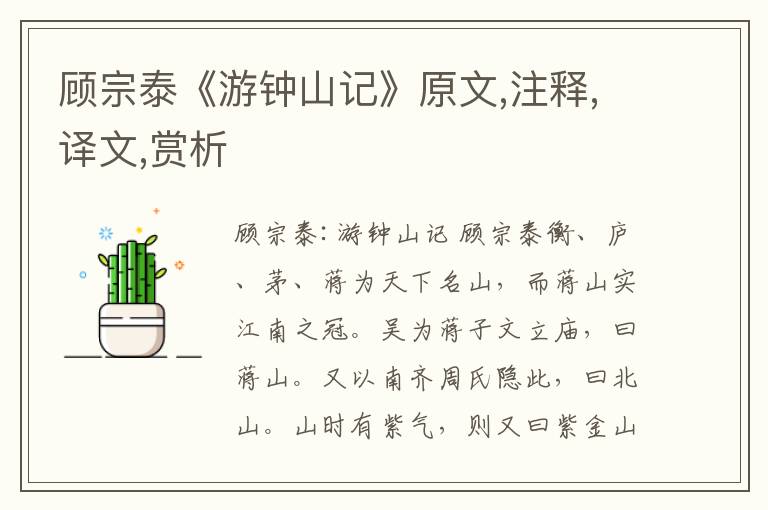
顧宗泰:游鐘山記
顧宗泰
衡、廬、茅、蔣為天下名山,而蔣山實江南之冠。吳為蔣子文立廟,曰蔣山。又以南齊周氏隱此,曰北山。山時有紫氣,則又曰紫金山。統而名之為鐘山。
余于是山向一至焉,未盡其勝。今鼓興而往,未至山六七里,峰崿蔽虧,藏云障日,水泉激澗,凈細可愛。至山,松陰夾路,寒濤吼空,風自絕壁而下,掩鱗動翠,其音颯然。自晉以來,刺史罷還,栽松百株,山故多松也。沿山五里,遂抵靈谷寺,寺故在獨龍阜,梁武帝為寶誌禪師建塔,宋改太平興國寺,明初徙山之東偏,名靈谷。龕鏤壁繪,不及往時,惟無量殿、寶公塔獨存。因偕寺僧觀景陽鐘,規小而音短,不能必為景陽樓中物也。至寶公塔,禮焉。問三絕碑,已毀沒矣。南為琵琶街,履之若有聲。塔循山,而左為安石讀書所,其說法臺舊址旁為八功德水,藤葛糾紛,求所謂清泠者不可得。由是為太子巖,此山之最高者。余乃升高而望,豁然四空,西瞰覆舟、雞鳴諸山,黛螺繚繞,后湖隱見,其六朝之佳麗乎?而其南則俯眺城中,萬家煙火,綺紛繡錯,曠無人處,夕陽故宮也。北凌大江,蒼然極浦,紫蓋黃旗之氣,猶有可想見者。而虎踞龍蟠,江山如故,獨慨然于齊梁遞遷之主,而嘆其銷沉于是。歷巖而下,日已薄暮。朝陽洞、商飆館、周氏草堂、羲之墨池諸境最僻,俱不得訪,別僧而歸。
歸則松風送人,明月滿衣,流連清景,恍若有失,不知路之幽且杳也。
歷來關于鐘山的游記很多,明代宋濂作有《游鐘山記》,詳細地描寫了鐘山上的名勝古跡和自然景色,并記敘了作者一行在鐘山上兩天的活動,寫景、記事、抒情相結合,跌蕩開合,詳實而凝練。四百多年后,鐘山依舊,顧宗泰亦作游記,雖然內容不免與宋氏記有相似之處,但語言清麗,簡潔,筆觸似行云流水,別具一格。
據宋濂《游鐘山記》引地理志云:衡、廬、茅、蔣四山同為江南名山。本文開頭幾旬即援引這一公論,并進一步認為“蔣山實江南之冠”。接著,介紹了由“蔣山”易名“鐘山”的由來,點出漢末秣稜尉蔣子文、南齊隱士周颙與鐘山山名的關系。作者未游山,先贊山。正因山之著名,所以過去雖曾游歷過,如今還要乘興而往,以盡覽其勝境。
“未至山六七里,峰崿蔽虧,藏云障日,水泉激澗,凈細可愛。”這是遠望鐘山所見到的景象:峰巒高聳,藏云障日,也遮蔽了山中的溝溝壑壑;山澗激流,就象一條潔凈細長的帶子,延伸在山間。因是遠望,所見不過是景物的輪廓。待入山中,則是很具體的景象了:松林夾道,每當風從絕壁吹來時,翠綠的松濤象魚鱗一樣,一浪接著一浪,翻滾不息,濤聲颯颯,響徹天空。接下來,作者較為詳細地描寫了從靈谷寺到太子巖一路上所見到的名勝古跡:靈谷寺為梁武帝天監十四年(515)高僧寶志禪師所建,在獨龍阜(鐘山南的玩珠峰)。其中寶公塔,乃永定公主為寶志禪師造,與無量殿同為靈谷寺的主要建筑,景陽鐘則是齊武帝永明中置于景陽樓的。至于三絕碑,因碑有梁張僧繇畫、唐李白贊和顏真卿書,世號三絕。還有八功德水,相傳梁天監中,胡僧曇隱來居鐘山,山中缺水。有一濃眉老人說:“我是山龍,得知你沒水喝。要喝也不難。”一會兒就涌水成池。后一西僧來到這里,說他們那兒八個水池,失去一個,大概到了這里。其泉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凈、七不饐、八蠲疴,所以稱八功德水。太子巖是鐘山的最高峰。作者登高望遠,四周豁然開朗。西面的覆舟、雞鳴諸山,象黛螺環繞著城郭,玄武湖或隱或現,景色秀麗如畫。向南俯眺城中,千家萬戶,炊煙裊裊;大街小巷,縱橫交錯,一派繽紛繁華的景象;遠處的夕陽下,明故宮空曠無人。北面俯瞰長江,江邊一片蒼茫。這里寫太子巖遠眺,和前面未至山時的遠望不同。前者是仰望,所見只有山的一面,這里寫的是從山上俯瞰山下,所以境界開闊,周圍景色,盡收眼底。作者把自己對六朝歷史的追想,今昔遞遷的慨嘆,寄寓在“虎踞龍蟠,江山如故”的描寫中,悠遠之思,壯麗之景,交融在一起,構成了一幅鮮明生動、內蘊深厚的鐘山遠眺圖。
“歸則松風送人,明月滿衣,流連清景,恍若有失,不知路之幽且杳也。”這里寫歸途情景,如詩如畫。“松風送人,明月滿衣”,清風,明月俱有情。這本是作者流連清景,但卻通過擬人化的表現手法,寫成風、月依人,表現了作者對鐘山的戀戀不舍之情,所以竟有“恍若有失”之感。這種失落的惆帳,不僅僅是因為要告別這清幽寧靜的美景,或許也有過去失去這清景的遺憾呢。
本文不同于其他游記,它并沒有借助所描寫的山水來發抒議論,而是把自己對清景的依戀以及對歷史遺跡的慨嘆同對景物的描寫緊密結合起來,寓情于景。筆調自然流暢,語言清麗簡潔,生動凝練。如寫覆舟、雞鳴山似“黛螺繚繞”,松濤翻滾如“掩鱗動翠”,歸途是“松風送人,明月滿衣”,形象清麗逼真生動。寫太子巖遠望,分別用西瞰、南眺、北凌,簡潔凝練,別具匠心。這種形象化的語言,不但增強了文章的藝術美感,也給文中所描寫的鐘山風光增添了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