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馨《靜靜的地壇(外一篇)》散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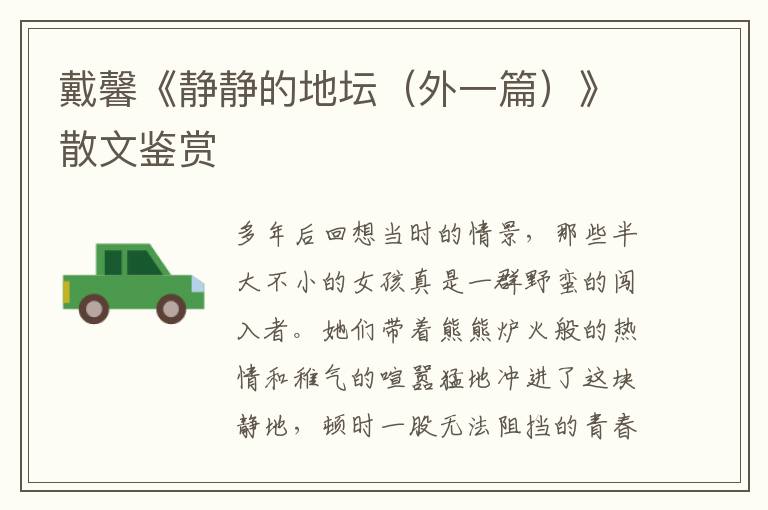
多年后回想當時的情景,那些半大不小的女孩真是一群野蠻的闖入者。她們帶著熊熊爐火般的熱情和稚氣的喧囂猛地沖進了這塊靜地,頓時一股無法阻擋的青春氣息便在空氣中散發開來。記不清是什么季節了,滿園的樹木依舊蒼翠,陽光淡淡地映照,樹木、建筑肅立。連鳥雀也是間歇地叫著,懶懶的聲音,偶爾撲棱棱地從隱蔽的樹梢騰起,劃過林間,好像在一個空曠的山谷里發出的一陣低沉的回響。比起人流如織的天壇,這兒顯得是太安靜了。而她們,那群天真的女孩,也是在領略了這個城市的繁華之后,才無意中來到這兒的。
且不說那古殿的玉砌雕欄、琉璃朱紅,在此時的氛圍中方可顯現它們莊重的美,光是走在叢蔭遮日的小徑、曲折回旋的長廊上,那份靜謐就足以令人心醉了。她們沒想到,在紛紛擾擾的都市中還會有這樣一片靜美的天地,更沒想到,慣于嬉笑打鬧的自己會滿足于這一刻安寧的心境。這兒,仿佛沉睡著一個遙遠的夢想。
她們的聲音不知不覺間小下來了,待到看見那一片片沁人的草坪時,索性不約而同地撲到了它的懷里,確實像撲進了母親溫暖的懷抱。那嵌在靜穆的大地上的色塊,不是翠綠、草綠,而是油綠,深沉而熱烈,浸透著飽滿、鮮活、生動,還有諸如此類說不清的意蘊。是它,使得這片土地一下子熠熠生輝,閃亮在眼前。
那是一生中最恣肆和彷徨的歲月。外表的強硬,性情的乖僻,也無法掩飾獨處時從心底生出的凄惶和冷寂。常常沉湎于一個人的遐想,不知自己身處何方,陷進了時間的黑洞和空間的虛無之中。不知該怎樣來安撫時時游走奔突的思維,偶爾暗涌上來的怪異的想象可能在一瞬間逼得自己透不過氣。
在這些意象的深處總會有一個模糊的背影,那是我很少對人提起的母親。我對于她的更多的記憶是寫在信頁上的一個個文字,我們的生活很難有交點。小時候她在外地,而她回來,我又求學在外,每次短暫的相聚暗示著即將的離別。我們都似在秋風中搖蕩的草葉,帶著風與塵土的氣息。酷似的面孔,相同的血液,強烈的個性,讓我們的心靈不能彼此交融。她矜持而冷靜的面容,在一個個暗夜里折磨著我尚不成熟的心,令我時時感受人生的不可捉摸和虛幻。
狂亂跳動的心最終忍不住揭開它最后的面紗。在這里,我看到的不是淋漓的鮮血,卻是母親晶瑩的淚花。我驚訝,震驚,羞愧。以致后來的幾年,我一直逃避,不敢正視她那雙沉靜的眼。
而現在,每次和她相見,透過她那張慈祥的始終含笑的溫和臉龐,我似乎看到了當年離開地壇時,一抹斜斜停留在祭壇上的陽光。原來,陽光一直在身后,我看見的只是那一片陰暗,只需轉過身,迎接它。
人與一個地方是否有種宿緣,讓你在適當的時候走近它?離開地壇后,我有幸看到了史鐵生的《我與地壇》。我才知道,早在我之前,已經有一顆孤獨而不屈的心在這里經歷了生與死的糾纏與考驗。
“上帝在交給我們這件事實的時候,已經順便保證了它的結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差別永遠是要有的,看來就只好接受苦難。”
在溫暖的陽光下,在這片柔軟又豐厚的草地上,似乎有著一種神奇的力量,在人的心靈大廈即將傾倒之際力挽狂瀾,在你即將走入迷宮之時為你找到一個通道,雖然前途仍是不可知,但讓你陡然萌生出一線希望。
生活中,有些人,有些事,如浮光掠影般地過了,也有些沉淀下來,成為一生的回憶,譬如那個靜靜的地壇。或是經歷了,影響始終追隨你,但你始終不能準確地把握它,也譬如那個靜靜的地壇。
桂湖聽雨
冬日的跫音已近,天地間,綿綿雨絲便是它不變的點綴。不免盼望來上一場酣暢的大雨,將漫繞眼前的霧濕之氣澆個無影無蹤。于是憶起一場多年前遭遇的大雨。
那是一片寧靜的荷塘,在成都新都縣的桂湖。桂湖是明朝文化名人楊慎和女詩人黃娥的私家園林,因夏秋荷桂飄香而得名。雖叫桂湖,園中一大半卻是荷塘。去時正值盛夏,桂花未放,荷花開得正好,有淡淡的粉色,也有如玉般的白色,在亭亭如蓋的綠葉中,顯得愈加高潔。沿湖周漫步,靜靜賞玩,聞得一陣陣沁人的荷香。立于高高的古城墻上,俯視古老的園林,只見荷塘掩映在碧樹間,深深淺淺,層次錯落;亭臺樓榭,姿態不一,真是幽雅盡致,美不勝收。流連往復,舍不得離去,便坐在一座八角亭里,靜靜地對著那片荷塘遐想。
桂湖是楊慎的老家所在,也是他少年時讀書的地方。他24歲中狀元,30歲與女詩人黃娥新婚后,在桂湖度過了兩年幸福恩愛的時光,不久卻獲罪謫守偏遠的云南,直至72歲病死在滇南的雨季。他為云南的文化發展貢獻了畢生的精力,著作頗豐。除了短暫的幾次偷偷跑回桂湖外,在異鄉度過了漫長的35年,而黃娥也在人世的凄風苦雨中整整等待了幾十年。從一首她寫給楊慎的詩中不難看出一片思君的深情:
雁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煙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
一場蓄積已久的大雨就在此時傾瀉而下。初入耳如鼓聲重擂,奏響了這場盛夏音樂會的前奏。再聽如急湍的瀑布,密集如撒在玉盤上的亂珠。漸漸才聽得打在荷葉上的啪啪脆響,如間歇中升騰的琴音。天色不覺暗淡下來,恍然只見天地間掛滿寬大的珠簾。雨敲打在厚實的荷葉上,眾多妙手共同配合,演奏起一首完美的協奏曲。風聲漸近,雨聲亦迅即由遠及近,嘩然,輕輕重重又復輕,各種敲擊音與滑音密織成網。風不經意在某個角落吹起,風勢席卷而去,遠遠近近,又奏成一曲婉轉的小夜曲。
閉上眼,荷塘上晶潤的水珠仍不停耀動,讀書樓中頁頁書稿的幻影沖破歷史空間,綻放出古久的墨意芳華。在這曲意境更為悠遠的樂章里,自有另一種親切和柔婉,它舒展著身上的每一根神經,諧和著人的心靈節拍,一波一波地漾開去。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楊慎《臨江仙》)仿佛這雨從千古一直奏到如今,奏響的是浮浮沉沉歷史的滄桑,聚聚散散塵世的悲歡。
這不休不止的人間的絕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