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新階《土豆田中的母親》散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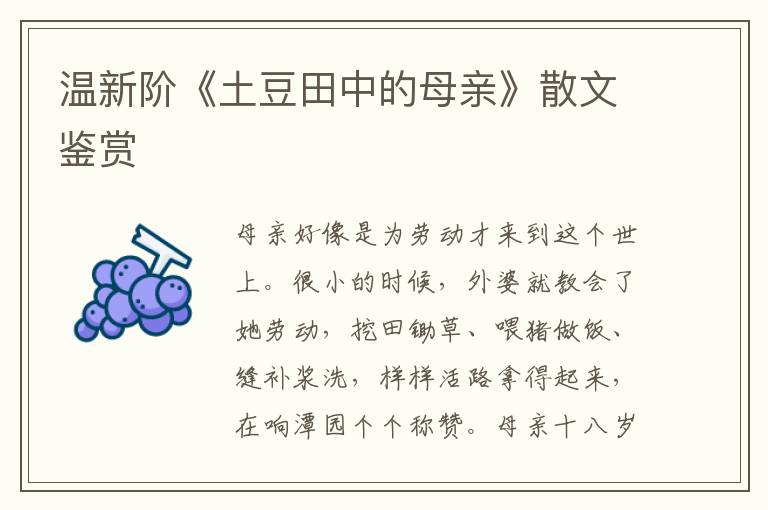
母親好像是為勞動才來到這個世上。
很小的時候,外婆就教會了她勞動,挖田鋤草、喂豬做飯、縫補漿洗,樣樣活路拿得起來,在響潭園個個稱贊。
母親十八歲嫁到楊家沖溫家,祖父解放前抽鴉片賣掉許多田產,四九年得以劃成貧農,但拖著一副抽過鴉片的病體,勞作自然被人瞧不上眼,祖母纏著小腳,一天到晚在堂屋和灶屋間走來走去,絮絮叨叨的數落祖父,幾十年都是如此,卻于事無補。父親在村委會做主任,那時的干部特別熱愛自己的崗位,一天到晚為村上的事奔波,家里主要靠母親。上隊里掙工分,侍弄自留地,喂豬、養羊、還有一群雞,母親幾乎沒有歇息的時間,碰上個雨天,也不能閑著,要搓納鞋底的麻繩。正頭臘月,家里別的人都閑下來了,母親似乎比平時更忙,打豆腐、做米酒、熬糖、炸果子,幾乎每天都是半宿。正月初一匆忙回響潭園給外公外婆拜個年,就要回家來做飯。因為父親做主任的緣故,來我們家拜年的就很多,父親負責給客人敬煙倒茶,給客人斟酒,做飯的事都是母親操辦,有時一天來七八撥客人,灶膛里的火就沒有熄過。
1962年,我們在白楊樹淌造新屋,母親正懷著弟弟新楷,為了少請人,每天和父親天不亮就開始出屋場。黃土一擔一擔挑出去以后,露出幾個大石頭,那時炸藥緊張,吃過晚飯,母親就在石頭上碼上干柴,點起熊熊大火,把石頭燒紅以后,用冷水澆,聽著石頭炸裂的聲音,母親一邊擦汗,一邊還哼起了姊妹歌:
高粱葉葉翠
姊妹來相會
房子造好時,母親的月份已經很重了,立屋那天,她和父親手里托著大盤,跪在地上接木匠師傅拋梁撒下的花生、板栗、核桃、包子和硬幣,我看見她差點要倒在地上,小姨連忙扶住了她。
搬進新屋不久,新楷就出生了,后來又有了小妹新翠,這時祖母早已過世,祖父年紀大了,更不能做事了,一家七口人,就只有父親母親勞動,每年都是缺糧戶。為了盡量多掙一點工分,母親總是揀工分多但是比較累的事做。比如鋤草,生產隊長和會計一塊田一塊田估完工分,每塊田多少工分寫在一塊篾片上,把篾片插在田里,鋤完草驗收質量后憑篾片到會計那記工分。隊長和會計插完篾片。母親就一塊一塊去看,哪一塊工分最高,她就把那一塊的篾片拿回來,當然工分高的必定是難度最大的,母親愿意去做這個難的,不然,你上哪去找工分?隊長會計知道母親的心思,后來插完篾片,就會告訴她哪幾塊工分高,母親就感激不盡。
那個年月,盡管父親母親拼命勞作,依然沒有擺脫缺糧戶的命運,每年年終分紅時,別人家分到余糧錢,可以去買年貨打燒酒愉愉快快的過個年,我們家依然只能拿回一個欠款的單子。母親倒不氣餒,能做的自己做,絕不比買到的年貨差,到了臘月二十九,母親就會回響潭園找舅舅借一兩塊錢,把一斤酒的酒票用出去,給父親買一斤酒過年。
直到分田到戶,我們家的日子才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父親母親能吃苦,又特別會種田,糧食多了,豬也喂的大,錢也不愁了,母親經常會哼起山歌,她唱得最多的是《探妹歌》:
正月探妹是新春
樹上的鴉鵲子唱高聲
奴的姊妹喲……
母親一邊唱一邊納著鞋底,父親就說,有沒有新鮮的,母親不理不答,唱的聲音更大了。
這樣的好日子持續了二十多年,父親因為庸醫亂用青霉素去世了。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使母親仿佛一下子蒼老了十歲,她不能接受這個現實,但是又必須接受這個現實。
母親打發傷心而寂寞的日子的方法就是拼命地勞動,她一個人種了十幾畝地,而且是我們村種得最好的。不但田里看不到一根雜草,連田邊地頭的荒草也割得干干凈凈。她收的菜籽存到榨坊里,去打一次油就在賬本上減一次。去年我回老家,碰到榨坊的師傅說,你媽存在我這里的菜油還可以打二十年,她只愿勞動不愿吃不愿喝,一個怪人。
母親就是這樣,每年喂幾頭豬,賣一頭,至少殺一頭,但是她卻不怎么弄肉吃,火塘的樓板上密密麻麻掛的都是臘肉,不愿吃,也不愿賣。她走進走出看著那些肉,是她的成就,看一看就足夠了。去年,母親已經八十歲了,喂了一頭豬,把幾個殺豬佬累得夠嗆,硬是弄不到殺豬凳上去。后來一過秤,四百多斤,母親喃喃地說,要是我愿意喂飼料這豬還可以喂大些的……
今年,我們堅決不讓母親喂豬了,我們承諾年底給她買一頭豬,田也只讓她種點小菜。前幾天,弟弟來電話說,豬倒是沒喂,但是田還是都種上了。我打電話回去問她怎么又種了那么多田,她在電話里說,我這個人,勞動慣了,我不勞動,渾身就不舒服,再說,我看不得田荒了,看著心里就發毛。她接著又說,我的洋芋長勢才好,只是到時候沒有豬來吃可惜了,我是不是還是買一個豬坯,不然糧食都浪費了。
第二天,弟弟發來一張照片,母親正在土豆田里施肥,陽光照在她臉上,一臉的喜悅和甜蜜。母親就是這樣,只要勞動著,她就快樂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