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莊子·山木(節選)》原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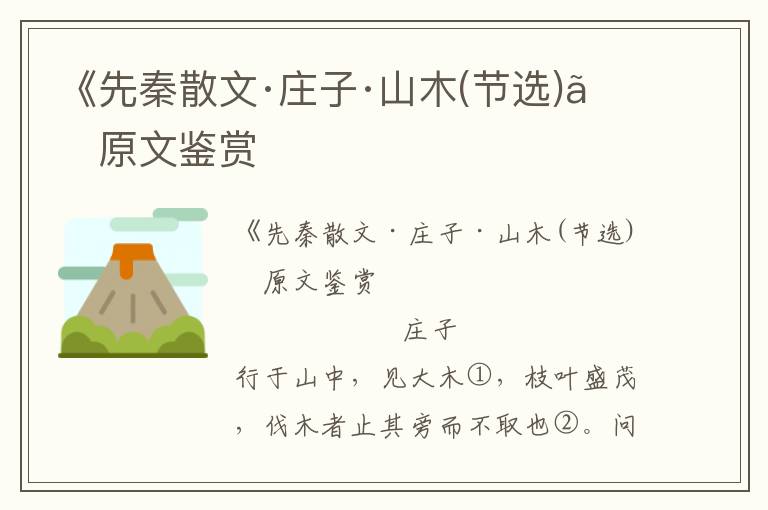
《先秦散文·莊子·山木(節選)》原文鑒賞
莊子行于山中,見大木①,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②。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③。”夫子出于山④,舍于故人之家⑤,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⑥。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⑦?”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于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⑧,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⑨。無譽無訾⑩。一龍一蛇,與時俱化(11),而無肯專為(12);一上一下,以和為量(13),浮游乎萬物之祖(14);物物而不物于物(15),則胡可得而累邪(16)!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17)。若夫萬物之情(18),人倫之傳(19),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20),尊則議(21);有為則虧(22),賢則謀(23),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24),其唯道德之鄉乎(25)。”
【注釋】 ①大木:大樹。 ②止;停下。 ③不材:不成材;終其天年,享盡自然賦予的壽命。 ④夫子:指莊子。 ⑤舍:寄宿;故人,老朋友。 ⑥豎子:童仆;雁,鵝;烹,讀為享,與饗通,指殺雁款待莊子。 ⑦奚殺:殺哪一個。 ⑧不材:指鵝之不能鳴。⑨乘道德:意謂順應自然;乘,駕取;浮游,指活動于世。 ⑩譽:稱頌;訾,讒毀。 (11)俱化:一同變化。 (12)無肯,不愿;專為,固執一端。 (13)和:和順,指順應自然;量,標準.原則。 (14)萬物之祖:指道。 (15)物物:指把物看作為物;不物于物,不為物所役使,即超于物外之意。 (16)胡:何。 (17)法則:指處世的方法、態度。 (18)情:指萬物的情理。 (19)人倫之傳:人類的習俗;倫,類;傳,指習慣,習俗。 (20)廉:品行廉正;挫,挫辱。 (21)議:非議。 (22)虧:指損害。 (23)謀:被謀算。 (24)志:記。 (25)道德之鄉:指天道無為的精神境界。
【今譯】 莊子在山中行走,看見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有伐木的人就在樹旁歇著卻并不砍伐它。莊子問這是什么緣故。伐木的人說:“沒什么用處。”莊子說:“這棵樹因為它沒用處所以能夠活到它應有的歲數。”莊子從山中出來,借宿在一位老朋友的家中。老朋友見到莊子十分高興,就叫他的童仆去殺鵝招待莊子。童仆問主人說:“兩只鵝,一只會叫,一只不會叫,請問殺那一只。”主人回答說:“殺不會叫的。”第二天,弟子問莊子說:“昨日山中大樹,因為不成材,所以能盡享它的天年,現在主人的鵝,卻因為不成材而被殺,老師您將怎樣安處呢?”莊子說:“我將處于材與不材之間。但材與不材之間,好象接近道,實際不合于道;所以還不能避免為憂患所累。假若能順乎自然之道而處世,就不會有拖累。無所謂稱頌,也無所謂毀議,此時可為龍,彼時可為蛇,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不愿偏滯于任何一端;可時高時低,以順應自然為原則,游心于道的境地。超然于萬物之外,決不被萬物所役使,還怎么會受到萬物的牽累呢?這就是神農黃帝所遵循的法則啊。假若是萬物的情理,人類的習俗,就不是這樣。有合則有離,有成功則有損毀;品行廉正,則要遭受凌辱,位至尊貴,則要受到非議,有所作為就要受到損害,賢能就要被謀算,不肖就要受到欺侮,怎么可以偏執一端呢?可悲啊,弟子們記住,唯有‘道德之鄉’方能避禍。”
【集評】 明·孫礦《南華真經》:“不材得終天年,莊子常,此卻添出以不材見殺一節,用以相形,甚新奇有味。”
清·林云銘《莊子因》:“兩‘若夫’提清,一段正一段反。結二句曲終奏雅,極繚繞低徊之致。”(據劉風苞《南華雪心編》補)
清·吳世尚《莊子解》:“人知材之為累,而不知不材之亦為累也。歸本道德,方不是鄉原學問.比《人間世》說話,又推進一層。”
【總案】 大木因不材而終其天年,鵝卻因不材而死,作者以這兩個比喻,說明處于混亂的社會現實中,材與不材,都會帶來災患,而處于材與不材之間.也不可能真正保身全命,唯一可取的處世方法是“乘道德而浮游”,順乎自然,一切無為。
市南宜僚見魯侯①,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②,然不免于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③,棲于山林,伏于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④;雖饑渴隱約⑤,猶且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⑥,定也⑦;然且不免于網羅機辟之患⑧。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愿君刳形去皮⑨,灑心去欲⑩,而游于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11),名為建德之國(12),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13),與而不求其報(14);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15);猖狂妄行(16),乃蹈乎大方(17);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愿君去國損俗(18),與道相輔而行(19)。”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20),我無舟車(21),奈何?⒋”市南子曰:“君無形倨(22),無留居(23),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24),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見其虛(25),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26),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27),見有于人者憂(28)。故堯非有人,非見有于人也。吾愿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游于大莫之國(29)。方舟而濟于河(30),有虛船來觸舟(31),雖有惼心之人不怒(32)。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33);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于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34)。向也不怒而今也怒(35),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游于世(36),其孰能害之!”
【注釋】 ①市南宜僚:作者虛構的人物,一說姓熊,名宜僚,居于市南,楚人。 ②居:指所處的境地。 ③豐狐:大狐;豐,指狐貍的皮毛豐美,文豹,身上有漂亮花紋的豹。 ④戒:警惕。 ⑤隱約:窮困。 ⑥胥疏:遠離。 ⑦定:指謹慎。 ⑧網羅機辟:捕鳥獸的工具。 ⑨刳形去皮:剖空形體,舍棄毛皮;刳(ku音枯),割棄;刳形,指忘身;去皮,指忘國。 ⑩灑心:洗凈內心;灑:通洗。 (11)南越:喻遙遠之地。 (12)建德之國:作者的理想世界。 (13)作:勞作;藏,私下藏匿東西。 (14)與;給與別人;報,報答。 (15)將:行。(16)猖狂:指不用理智,隨心所欲;妄行,指沒有任何束縛地任意而行。 (17)蹈乎大方:指合于道;蹈,行;方,道。 (18)捐俗:棄俗。 (19)相輔:相助,指人與道同行。 (20)江山:喻通往建德之國路上的重重險阻。 (21)舟車:喻抵達建德之國的方法。 (22)無:通毋,不要;形倨,指自恃位高而傲慢;倨,傲慢。 (23)留居:滯于所居,指不肯舍棄君王的高位;留,滯守。 (24)費:費用。 (25)崖:際。 (26)反:同返。 (27)有人者:意為擁有臣民的人。 (28)見:被。 (29)大莫之國:指道的境地,猶《逍遙游》中的“廣漠之野”;大莫,猶廣漠,指寥闊無人的曠野。 (30)方舟:兩舟相并;濟,渡。 (31)虛船:無人駕駛的空船。 (32)惼(bian音貶):心地狹隘。 (33)呼:叫喊;張,撐開;歙(xi音細),收攏,靠攏。 (34)惡聲:辱罵之聲。 (35)向,過去,剛才。
【今譯】 市南宜僚去見魯侯,魯侯面帶憂色。市南宜僚問道:“君王面有憂色,為什么呢?”魯侯說:“我學習先王之道,繼承先君的事業,敬鬼神、尊賢人,躬身力行,一刻也不曾偏離;但仍然不免于憂患,我因此而憂慮。”市南宜僚說:“您解除憂患的方法太淺陋了!那皮毛豐美的大狐貍和毛色斑爛的豹子,棲息于山林之中,藏身于巖洞里,這是在靜靜地等待;夜里出來行走,白天靜居不動,這是有所警賜;雖然為饑渴所困逼,但還是要遠離江湖去覓食,以免遭禍,這是它的謹慎之處;然而還是免不了要遭受網羅機辟的禍患。它們有什么過錯呢?這是因為它們的皮毛給自己帶來了災禍。現在魯國不就是您的皮毛嗎?我希望您剖空形體,舍棄皮毛,拋卻一切心機、欲望,遨游在沒有人煙的曠野。在遙遠的南越有一個地方,名叫建德之國,那兒的人民愚昧而純樸,很少有私心和欲望,他們只知耕作而不知私下藏匿東西,只知給予別人而不求有報償;不知怎樣做才合乎義,也不知怎樣行才是禮;事事隨心所欲,任意而為,人人自蹈其方且都合于大道。他們活著,自得其樂;死后安然入葬。我希望您能離開君王之位,拋棄俗事,與大道相輔而行。”魯侯說:“到那兒去的路途遙遠而又艱險,我沒有車船,怎么辦呢?”市南宜僚說:“您不要自恃位高而傲慢,不要不肯舍棄君王的高位,您就可以以它作為車船。”魯侯說:“那兒的道路幽遠而且沒有人,我與誰為鄰呢?我沒有糧食,沒有吃的,怎么才能到達呢?”市南宜僚說:“您減少費用,清心寡欲,雖然沒有糧也能得以滿足。您渡過江河遨游于海上,放眼望去無限廣袤,愈往遠處愈不知它的盡頭。送您的人都從岸邊返回了,您從此就更遠了!因此役使別人的人,則受其累患;被役使的人就會有憂患。所以,堯不是擁有百姓,也不是為百姓所有。我希望您能去掉拖累,除去憂患,而獨與大道游于寥闊無人的曠野。兩船并行渡河,有空船來撞,雖然是心胸狹隘的人也不會發怒;如果有一個人在船上,船上的人一定會呼喊對方把船撐開,或者靠攏;一次呼喊不聽,二次呼喊仍不聽,于是第三次呼喊時,那就一定伴隨著辱罵之聲了。剛才不發怒而現在發怒,是因為剛才船上沒人而現在有人。人若能象無人的小船一樣無心于世,那么,有誰能加害于他呢?”
【集評】 宋·劉辰翁《評點莊子》:“念哉!夫子乃并于物外無塵之境,盡其所見,歷歷指迷而言,又結駟裹糧而送之,以為幻則幻,以為仙則仙。讀至‘自崖而反’,飄飄有棄吾故屣之意。此論道德之鄉文章之妙,一至乎此。”
清·林云銘《莊子因》:“此地(指南越有邑)方稱樂土,武陵源不足言也。王績《醉鄉記》人以為絕唱,不知從此脫化出來。”
又:“莊叟善體物情,於《徐無鬼》篇撰出去國景況,於《則陽》篇撰出回鄉景況,於此撰出送行景況,淋漓曲盡,筆有化工。”
又:“末二句方是正意,文氣悠長,人情曲盡。”
清·宣穎《南華經解》:“行文清機飄渺,恍如伯牙入海,成連徑去,一段神境,使人塵心頓盡。”
清·陸樹芝《莊子雪》:“妙喻切理厭心。”
清·劉鳳苞《南華雪心編》:“此段只‘虛己游世’一句,括盡通篇奧義。……前面豐狐文豹,以喻土地人民;……中間作兩層波折,動宕生姿。無行地之勞,則險遠艱難不足慮,有深造之詣,則孤寂清苦何所憂。去其人之累,而我與天下相忘,更何有于一國,除其見有于人之憂,而天下與我相忘,又何重乎一國。語語透入清虛,真不食人間煙火者。‘虛舟’一喻,更為超脫,實則胸中有物,相觸而不能相忘;虛則胸中無物,逆來亦可順受。游于無物之地,物安得而傷之。建德之國,不見其崖,不知所窮,縱心孤往焉可矣。”
【總案】 本節以詩一般的語言,描繪了作者對理想之世——建德之國的熱烈向往。所謂建德之國,是作者為擺脫宗法制社會對人的壓抑,擺脫人為的對偶像的崇拜,而創造的遠遠超越于現實之上,并與現實針鋒相對的理想世界。這里的人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存在欺詐和虛偽。當然,作者也深知在現實社會中是找不到通往建德之國的道路的,因而他只可能在精神的領地,指出“刳形去皮,灑心去欲”的修養方法,這反映了作者理想的虛妄。但是,作者又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充滿渴望,充滿感情。文中描繪的“道德之鄉”的情景,是那么凄迷而感人肺腑。這說明作者在哲學上對道的追求,已發展為一種情感的抒發,心境的吐露,因而產生出巨大的藝術魅力。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①,正緳系履而過魏王②。魏王曰:“何先生之憊也③?”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④,憊也;衣弊履穿⑤,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⑥。王獨不見夫騰猿乎⑦?其得楠、梓、豫章也⑧,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⑨ ,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⑩。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11),危行側視(12),振動悼栗(13);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14),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15)。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16),征也夫(17)!”
【注釋】 ①大布:粗布;補之,衣服上打了補丁。 ②正:整理; 緳(xie音協),麻繩;系履,因鞋破舊,需用麻繩把鞋綁好;過,過訪;魏王,魏惠王。 ③憊:疲困的樣子。 ④行:施行。 ⑤衣弊:衣服破舊;履穿,鞋子破爛;穿,磨出了洞。 ⑥非遭時:猶生不逢時。⑦騰猿:善跳躍的猿猴。 ⑧楠(nan音南):楠樹;豫章,樟樹;楠、樟,都是端直的大樹。 ⑨攬:把捉;蔓,攀引;王長,自由自在的樣子。 ⑩羿:傳說中的神射手;蓬蒙,羿的弟子,亦以善射著名。 (11)柘棘枳枸:四者皆為有刺的灌木;柘(zhe音紙),黃桑;棘,酸棗;多刺;枳(zhi音紙)枸桔,有粗刺;枸(ju音舉),香櫞,在硬刺。 (12)危行:很憂懼地行走;側視,因膽怯而不敢正視。 (13)悼栗:恐懼,戰栗。(14)加急:加緊,指身體發僵;不柔,指行動不靈活。 (15)逞:施展。(16)比干:商紂王之臣,因忠諫而被剖心致死。 (17)征:證據。
【今譯】 莊子穿著打了補丁的粗布衣裳,用麻繩拴好破了的鞋子,過訪魏惠王。魏惠王說:“為什么先生如此疲困呢?”莊子說:“這是貧窮而不是疲困。讀書人有道德卻不能施行,這是疲困;衣服破舊,鞋子破爛,這是貧窮,不是疲困;這就是所謂生不逢時了。您難道沒有見過善于跳躍的猿猴嗎?它處于楠、梓、豫章這些高大端直的樹木之間,抓住樹枝攀援跳躍,十分自由自在,雖然是羿、逢蒙這樣的神射手也對它們奈何不得。但是等到它們來到柘、棘、枳、枸這些多刺矮小的灌木叢中,行走時十分憂懼,左顧右盼,非常緊張。這并不是它的筋骨發僵不靈便,而是它所處的形勢不利,不能充分施展它們的才能罷了。現在處于君主昏庸、朝臣作亂的時候,要想不憊,怎么可能呢!那比干被剖心而死,不就是例證嗎?
【集評】 清·劉鳳苞《南華雪心編》:“騰猿一喻,托出正意,絕妙機鋒。莊子蓋不愿為世用,世亦無能用莊子者。曳尾泥涂,不欲留骨于廟堂之上;憤世嫉俗,殆亦有慨乎其言之邪。即非廬山面目,亦與尋常蹊徑不同,熱中者讀之,可抵一服清涼散。”
【總案】 本段以莊子生活的窘迫,說明在“昏上亂相”統治下,士就是有道德也無可施行。從而把批判鋒芒直指最高統治者,揭示了造成社會黑暗的根源。在寫作上,作者緊緊抓住“貧”、“憊”二字展開論說,前后呼應,特別插入“騰猿”一喻,將滿腹心事,和盤托出,有言已盡而意無窮之妙。
莊周游于雕陵之樊①,睹一異鵲自南方來者②,翼廣七尺,目大運寸③,感周之顙而集于栗林④。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⑤,目大不睹?”蹇裳躩步⑥,執彈而留之⑦。睹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⑧;螳螂執翳而搏之⑨,見得而忘其形⑩;異鵲從而利之(11),見利而忘其真(12)。莊周怵然曰(13):“噫”物固相累(14),二類相召也(15)!”捐彈而反走(16),虞人逐而誶之(17)。莊周反入,三月不庭(18)。藺且從而問之(19):“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20)?”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于濁水而迷于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 ‘入其俗,從其令’,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游于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21),吾所以不庭也”。
【注釋】 ①雕陵:栗園名;樊;通藩,藩籬。 ②異鵲:奇異之鵲。 ③運寸:直徑一寸。 ④感:觸,碰;顙(song音嗓),額;集,止。 ⑤殷:大;逝,往,指遠飛。 ⑥蹇(jian音儉)裳:即褰裳,提起衣裳;躩(jue音厥)步,形容小心疾行的樣子。 ⑦留:伺機彈擊。 ⑧忘其身:指蟬躲在美蔭下忘了自己面臨的危險。 ⑨執翳:指舉著草葉作掩護;翳,隱蔽;搏之,指捉蟬。 ⑩得:指將要得其蟬;忘其形,指螳螂見到捕物而忘記了自己的安危。 (11)從:跟著;利之,以此謀利。 (12)真:真性,本性。 (13)怵然:驚覺的樣子。 (14)累:牽累,有相互殘殺之意。 (15)相召:相互聯系、吸引、依存。 (16)捐:扔掉;反走,回身走。 (17)虞人:管栗園的小官吏;誶(sui音碎),責罵。 (18)不庭:不出門庭。 (119)藺且(li n ju音吝居):莊周弟子。 (20)頃:這里意為長、久。 (21)戮:責罵,辱罵。
【今譯】 莊周在雕陵的栗園游賞,看見一只奇異之鵲從南方飛來。這只異鵲翅膀寬有七尺,眼睛的直徑有一寸大;它擦著莊周的額頭飛過來,落在栗林里。莊周說:“這是什么鳥呀?翅膀很大,卻不遠飛;眼睛很大,卻目光遲鈍?”莊周撩起衣裳,小心地快步跟了過去,拿起彈弓,等待著彈射的機會。這時,莊周看見一只蟬正陶醉在濃密的樹蔭下,全然忘了自己的處境,而螳螂正在草葉的遮蔽下準備捕蟬,螳螂為自己就要得到美味也忘記了自身的安全。異鵲跟在螳螂后面,又把螳螂當作自己的可圖之利,為自己就要吃到螳螂而忘記了本性。莊周見到這一幕,驚覺地說:“唉,物與物之間本來就是互相牽累、互相殘殺的,這是由于物與物相互吸引、相互依存導致的災禍呀。”說完,莊周扔下彈弓回頭便走。看管栗園的小官吏追在莊周身后直罵他。莊周回到家中,一連三個月沒有出門。莊周的學生藺且問道:“先生為何這么長時間不出門呢?”莊周說:“我守住形體(指異鵲),而忘了自身的安危;觀看濁水,反而對清水迷惑了。而且我從先生那里聽說:‘到一個地方去,就要隨從那里的習俗。’現在我在雕陵的栗園里游玩,卻忘記了自身;異鵲擦著我的額頭飛過,到栗林里去而忘了自己的本性,管栗園的人又來辱罵我,因而我很久不出門。”
【集評】 宋·蘇軾:“此與《戰國策》同,不及者又彈黃雀故也。作文如畫畫者,當留不盡之意,如‘執彈而留’是也,此間妙意,在‘捐彈而走’。”(見《百大家評莊》)
明·孫礦《南華真經》:“寫得意狀涌躍,大有妙境。”
清·宣穎《南華經解》:“接連寫出數層妙境,使人有目不及眨之趣。蟬一層,螳螂一層,異鵲又一層,已數累之上矣,又轉出虞人逐誶一層,收入當身。如窮幽涉險之后,又轉出一勝,真文家樂事也。”
清·吳世尚《莊子解》:“利令智昏,寫來如畫。”
又:“彈而得之,鵲不能去,故目‘留’。‘留’字鮮。”
清·胡文英《莊子獨見》:“死利之徒,有翼不逝,有目不睹,漆園之慨深矣。”
又:“‘觀’字極輕,‘迷’字’極重;較鮑魚芝藺之喻更為危切。”
清·劉鳳苞《南華雪心編》:“驀爽不覺,感顙不知,所謂觀濁水而迷清淵也。答還問者,現身說法。”
又:“此段極寫世途之危險,見得而忘其形,見利而忘其真,說透病根,是一篇扼要之語。蟬得美蔭,而螳螂已乘其后;螳螂執翳,而異鵲又乘其后,禍機之展轉相生,皆物類之自相為感召也。現前指點,便使人驚心動魄。‘執彈而留’、‘捐彈而走’,前后均從異鵲生波,而以螳螂執翳一層,夾在中間,與《國策》文引黃雀螳螂,另是一種機杼,極錯綜離合之奇,尤妙在虞人誶逐,又轉出一層,文心矯變不測,正如驚濤駭浪之中,忽逢峭石,疊蟑層巒之外,突起奇峰,真非尋常意境。通體筋節靈動,脫化無痕,亦有石棧天梯,架危凌虛之勝。”
【總案】 本段主旨在于宣揚清凈無為、超然利害之外的處世思想,指出逐利忘真,則必有喪身之患。同時,也真實反映了階級社會中人類自相殘殺的現實。在這一節中,作者巧設伏筆,環環相銜,先寫莊周伺機彈射異鵲,然而寫蟬得美蔭而忘其身,寫螳螂伺機捕蟬,再寫異鵲伺機捕螳螂,最后寫虞人逐罵莊周,把物與物之間相互為累的情形,刻畫的驚心動魄而又活靈活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