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中偉《十年征戍憶遼陽》散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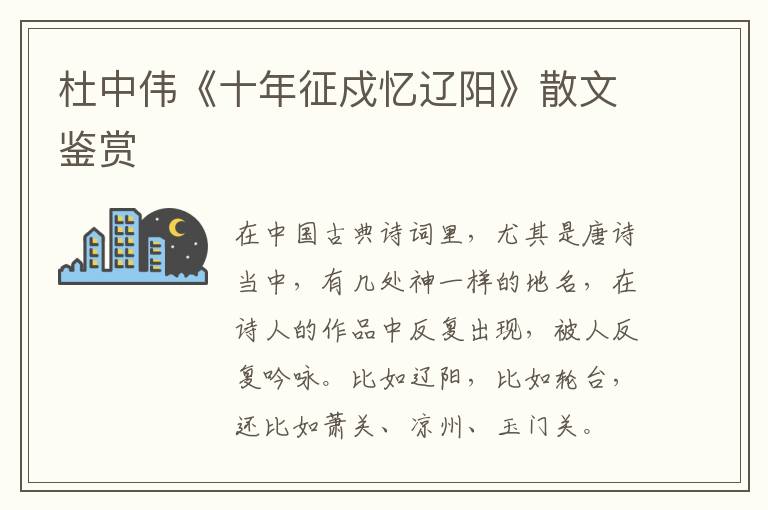
在中國古典詩詞里,尤其是唐詩當中,有幾處神一樣的地名,在詩人的作品中反復出現,被人反復吟詠。比如遼陽,比如輪臺,還比如蕭關、涼州、玉門關。
這些地方大多是邊地。邊地是什么?是“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是“五原春色舊來遲,二月垂楊未掛絲”;是“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也是“刁斗鳴不息,羽書日夜傳”。它們訴說著豪邁,也訴說著柔軟;訴說著遙遠,也訴說著思念。它們是浩瀚之風、氣吞山河,也是春風難度、寤寐思服,但無論蒼涼高遠還是敏思哀婉,總會讓人觸摸到滾燙、鮮活的靈魂。這靈魂里有家有國有蕩氣回腸,有念有怨有兒女情長。所以,在唐代,邊塞詩和閨怨詩是詩歌朋友圈里的一道別樣風景。
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講,邊防征地一輩子也許都不會到過一次,但對于戍邊將士來說,這幾乎是自己的第二故鄉,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收集感情的文化高地,把征人、深閨、文人、將士的情感一股腦兒地收集到自己懷內,然后被釋放在那些千古流傳的文學作品當中。
而遼陽, 是以怎樣的面目呈現于今人面前呢?
盧家少婦郁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
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
誰為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唐沈佺期(約656-約715)的這首《獨不見》,被認為“曲折圓轉,如彈丸脫手,遠包齊梁,高振唐音”。
初讀這首詩,就使得“遼陽”這個地方一下子從文中躍進了自己的腦海里,就和讀完“春風不度玉門關”“但使龍城飛將在”“西出陽關無故人”后,“玉門關”“龍城”“陽關”一樣。有時候,一個地名就僅僅是因為一首詩,而名揚天下。
那是一個什么樣的地方,能夠讓人如此愁腸百結,秋水望斷?
其實,詩詞中和歷史上的遼陽,并不是如今的遼陽市,而是一個更加廣泛的地區,有人說是遼河以北地區,而按胡可先注《唐詩三百首》,解釋為遼河以東地區。從地圖上看,遼河主體在遼寧省,溯流向上的話,分為兩支,一支進入吉林,為東遼河,一支進入內蒙,為西遼河,這兩條分支都是東西走向。因此,河東、河北的說法大致都沒有問題,無論河東也罷,河北也罷,無非都是指廣大遼東地區。而現今的遼陽,《奉天通志·沿革志》則“考唐以前稱今遼陽或曰遼東城,或曰襄平城,或曰遼東郡故城,無稱遼陽者”。
據此,遼陽,就是今天遼河周邊一帶,這總歸是沒有錯的。
而這正是唐時安東都護府的駐地所在。
由于李唐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統局面,統治區域東至遼東,甚至朝鮮半島,西達西域,其威懾力和影響力空前提高,使得周邊的異族兄弟,比如突厥、回紇、靺鞨、鐵勒、室韋、契丹等,大多表示臣服。但他們從來都不是規規矩矩地聽從中央政府,時不時地奓奓毛,所以,為了有效地對他們進行管理和震懾,唐設立了安西、安北、安東、安南、單于、北庭六大都護府。而安東都護府就是負責管理東北事務的最高軍政機構。據史料記載,唐高宗總章元年(668年),唐滅高句麗,在平壤設置安東都護府以統轄其地。其所轄范圍包括遼東半島全部、朝鮮半島北部、吉林西北地區和朝鮮半島西南部的百濟故地,包含今烏蘇里江以東和黑龍江下游西岸及庫頁島直至大海。但后來,由于吐蕃和新羅擾邊,上元三年(676年),安東都護府治所由平壤遷往遼東故城,也就是今天的遼陽。儀鳳二年(677年),再遷治新城,也就是今天的撫順高爾山。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696年),遼西契丹族反唐,唐與安東都護府的陸路交通一度中斷。唐玄宗開元二年(714年),安東都護府治所內遷治平州(今河北盧龍)。天寶二年(742年),遷治遼西故郡城(今遼寧義縣)。受安史之亂影響,唐肅宗上元二年(761年),設立了近百年的安東都護府宣布廢止。
故,“十年征戍”的盧家少婦之夫,便應該是鎮守安東都護府的將士了。
遼陽,雖然尚算不得苦寒,但畢竟比內地要寒冷許多。所以,當長安秋高、天氣轉涼、家家戶戶開始著手準備寒衣時,征夫在外的少婦不免愁緒涌動,觸景生情。甚至,都后悔自己沒跟著夫婿出征遠方了。
遼陽在何處,妾欲隨君去。
義合齊死生,本不夸機杼。
誰能守空閨,虛問遼陽路。
(于濆《遼陽行》)
而等到金昌緒寫《春怨》時,則一定是天寶二年之后的事了。彼時,安東都護府已經遷至遼西,所以生怕夢不到遼西,而不再是遼東了。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
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但那份牽掛究竟還是十分一致的。
多年征邊,不知生死,這不是“悔教夫婿覓封侯”的嗔怪與相思,而是未知生死的刻骨深念。
哀怨,孤獨,深情款款。哪位征人能讀之而不潸然淚下?哪位讀者能讀之而不怦然心動?
說來有些奇怪,同是寫邊地,不知是因為古人給我們留下的名篇太少,還是因為詩人們被那些閨怨詩所感染,在寫遼陽的詩里我們很少能看到更恢宏的場景,體味更寬廣的心境。即使有類似邊塞風格的詩作,但終究不如西北風來得那么痛快、豁達和剛烈。
征人歌且行,北上遼陽城。
二月戎馬息,悠悠邊草生。
青山出塞斷,代地入云平。
昔者匈奴戰,多聞殺漢兵。
平生報國憤,日夜角弓鳴。
勉君萬里去,勿使虜塵驚。
(李益《送遼陽使還軍》)
勉強算是邊塞詩吧,但照樣有點不溫不火,不急不緩,婉約里似乎流露出點豪放,但終究還是沒有豪放開,猶如把弓拉開,卻又輕輕放下,不過癮。
也許是時代使然,也許與地域文化有關。在這方面,不免會讓我們想起輪臺,一個邊塞意味豐厚、英雄氣概爆棚的地方。
這里有岑參的詩,也有陸游的詩。
這些詩,寬廣、豪邁、雄渾、健壯,少了那些兒女情長、憂愁郁結,多了許多壯志豪情、劍膽琴心。
……
瀚海闌干百丈冰,愁云慘淡萬里凝。
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
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
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
……
(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
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
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
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
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
虜騎聞之應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西門佇獻捷。
(岑參《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
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陸游《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
這些耳熟能詳的詩句讀之向來會讓人豪情平起,恨不得立即躍馬揚鞭。
若拋開陸游,單從唐詩的角度看,這兩種詩風恰恰反映了對戰爭截然不同的態度。
邊塞詩的詩風映射的是大唐帝國威武雄壯的氣象,而閨怨詩則映射的是厭戰情緒蔓延和兵役之苦。
往往如此,且必須如此。即一個國家的康寧富庶,必須有一批人在犧牲,犧牲與家人的團聚,犧牲卿卿我我,犧牲奉孝雙親。一方面是守家衛國的榮光,我們稱之為民族長城,一方面是父母妻兒的目光,把你當作家庭的梁柱。于是,總是在壯烈中深藏著嘆息、思念、孤單和悲涼。無論是抵御侵略,還是開疆拓土,無論是守望和平,還是兵荒馬亂,遙遠的邊城,是最讓人揪心之地,尤其是在音信難通的古代,怎能叫人不想他?
但那個時候,整個帝國都是春風得意,氣勢磅礴,文采郁郁,武備昌隆。“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不用說那些軍人,連文人士大夫都有強烈的建功立業的愿望。
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楊炯《從軍行》)
愿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
(李白《塞下曲》)
然,對于一般戰士和家人而言,“十年征戍”,更有著道不盡的酸甜苦辣。而這一切,也與唐初至中期兵役制度的變革有關。
在唐朝初期,兵役制度實行的是府兵制。簡單講,府兵制是一種兵農合一的軍事制度,府兵21歲入軍,61歲出軍,平時散居務農,府兵征發時自備兵器資糧,定期宿衛京師,戍守邊境。政府對府兵有一系列的優待辦法。比如,規定戍邊和出征實行三年一輪換制,無須長期戍邊。同時,當府兵可以免除徭役,可以因勛功受田,增強當兵人的榮譽感。假如府兵外出作戰陣亡,軍隊立刻會把名冊呈報中央,中央政府也馬上會轉給地方,地方政府會立刻派人到死難士兵家里去慰問,送勛爵,給賞恤。陣亡軍人的棺木還沒運回時,政府一應撫恤褒獎工作都已辦妥了。這種體制對于提升軍人的榮譽感和軍隊的戰斗精神,都有很大的幫助。更為重要的是,府兵出征或守邊的統帥不是固定人選,因此不會造成軍隊私人化,這對于朝廷來說,非常安全。
但歷史卻經常發展得出乎人的意料。大體到了高宗年間,隨著土地兼并問題越來越嚴重,國家對軍人的優待辦法越來越少,直至取消。府兵的社會地位也日益下降,甚至成了那些官員的奴隸,并且服役年限日益延長,新兵難招,老兵大批逃亡。府兵們開始怕到邊疆,能逃則逃,逃不掉的,大都家破田荒,后繼無人。
所以,“十年征戍憶遼陽”,不僅僅是一名閨中少婦的嘆息,更有歷史老人深深的、沉重的嘆息。杜甫也記下了這種變化: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于是兵源日益枯竭。那怎么辦?買。
政府是不缺錢的。故,自玄宗開元十年(722年)起,“召募壯士充宿衛”。于是,唐朝的兵役制度便從府兵制逐步過渡為募兵制,開始招募雇傭軍,邊疆上守邊的戰士慢慢地都變成外族士兵。因勢而起的,是安祿山、史思明這些外族將領,他們野心勃勃地走上歷史舞臺,逐漸控制了朝廷的邊防,也控制了治下軍隊的歸屬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后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幾個人便生出了驚天大亂,這也是玄宗皇帝始料不及的吧。
而彼時,戍守輪臺的岑參們,并沒有看到這種兵役制度下隱藏的不安和騷動,他們滿眼仍然是唐軍的威武,熱血沸騰的戰士。北風吹得戰旗嘩嘩作響,人馬卷起的塵土蔽日遮天,他們目光如炬,豪氣干云,心中沒有去國懷鄉的失意,沒有戍邊寒瑟的苦衷,相反,他們心中充滿的是報效朝廷的忠誠和統兵殺敵的快意。
天寶十三年(754年),岑參剛剛被委派為安西北庭節度使封常清的判官,正沉浸在橫掃千軍的理想和對戍邊將士的謳歌中。他肯定也不會想到,僅僅一年后便發生了導致李唐王朝由極盛至極衰的驚天變局。又半年后的六月十三日,唐玄宗攜楊貴妃及部分心腹大臣離京西逃,幾天后,在馬嵬坡前,喜愛荔枝的楊貴妃香消玉殞,猶如那顆晶瑩的荔枝,瞬間色香味全無,整個大唐也處在了風雨飄搖之中。其時,大唐經濟與國力已不堪戰爭重負。隨著戰爭的深入,堂堂大唐帝國的邊地也不斷地向內地收縮,直到收縮到洛陽附近。
“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這是杜甫《新婚別》中的句子,參軍的壯士守邊居然守到了自己的家門口,不得不說整個王朝對戰爭估計不足。
再英雄的歷史,或者說橫空出世的英雄再多,也抵不過朝廷的腐敗。即使皇恩浩蕩,又有多少英雄終是抱恨終生?而戰爭,無論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都是在拿人的生命作賭注,人的生命總是那么不值一提。
還是玄宗時期的一場戰爭,這場戰爭,或許不應該發生(其實好多戰爭都不該發生,然而歷史沒有假設),但還是發生了,并且以“唐師三征失敗,喪師二十萬”(《至簡中國史》)的代價而結束。這就是南詔之戰。
南詔之戰具體的前因后果不再詳敘,明萬歷年間云南副總兵鄧子龍所寫的一首詩還是讓我們能感受到其中凄涼。詩云:
唐將南征以捷聞,誰憐枯骨臥黃昏?
唯有蒼山公道雪,年年披白吊忠魂。
“一將功成萬骨枯”,然而,功未成,骨亦枯。
從遼陽到輪臺,從輪臺到南詔,從閨怨到英雄,從英雄到亡魂,就像一枚硬幣的三面:正面、反面和側面。從不同的一面,會解讀出許多不同的意義。
而這,絕不僅僅是詩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