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州快哉亭記原文,注釋,譯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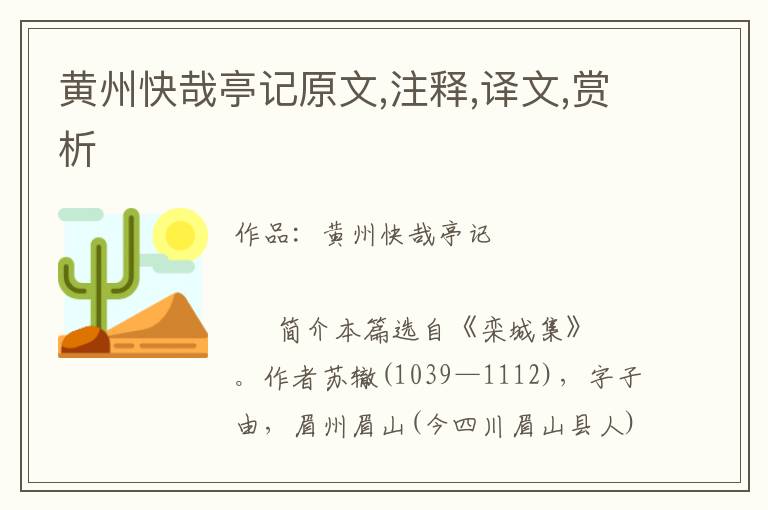
作品:黃州快哉亭記
簡介
本篇選自《欒城集》。作者蘇轍(1039—1112),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縣人),與父蘇洵、兄蘇軾并稱“三蘇”,是北宋散文家,都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蘇氏先世為趙州欒城人,故名其集,五十卷,又《欒城后集》二十四卷,《欒城三集》十卷,《欒城應詔集》十二卷,此四集均蘇轍自編。本篇作于元豐六年(1803),時作者謫居筠州(治今江西高安)。文章揭示了快樂與否的關鍵在于人的精神修養,贊揚了張夢得不以遷謫為患,怡情山水,逍遙自得的曠達胸襟。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漢沔①,其勢益張,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云開闔②;晝則舟楫出沒于其前,夜則魚龍悲嘯于其下;變化倏忽③,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幾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于長州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④,周瑜、陸遜之所騁騖⑤,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⑥于蘭臺之宮,有風颯然⑦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余功⑧,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⑨,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⑩,揖西山之白云,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為快也哉!
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
注釋
①漢沔(miǎn):即漢水。 ②闔(hé):閉合。 ③倏(shū)忽:迅速、非常快的樣子。 ④睥睨(pìní):側目窺察。 ⑤騁騖(chěnɡwù):馳騁、奔走。 ⑥景差(cuō):差,一作瑳,戰國時楚國辭賦家。 ⑦颯(sà)然:風聲。 ⑧竊:偷閑,利用。 ⑨蓬戶甕牖(yǒu):蓬草編成的門,用破甕作的窗戶。 ⑩濯(zhuó):洗滌。 揖:通“挹”,本指以器取水,此處有觀覽、享受的意思。
譯文
長江出了西陵峽后,開始進入平地,于是它的水流才奔放浩大。在南面匯合了湘江和沅江,在北面匯合了沔水、漢水后,水勢愈加壯闊,至赤壁之下,水流匯聚浸灌于其附近,簡直就像大海。清河張夢得君因被貶謫住在齊安,在他住宅的西南方修建了一座亭子,用來觀賞江水奔流的優美景色。我的兄長子瞻給這座亭子命名為“快哉”。
在亭子里可看到:南北約一百里,東西三十里左右。下面波濤洶涌,上面風云或開或合;白天則船只出沒于其間,黑夜則魚龍水族在水下悲傷地鳴叫;一時之間變化多端,令人觸目驚心,簡直令人不敢多看一會兒。如今卻可以把這驚心動魄的風光賞玩于幾席之間,一抬眼就能看個夠。向西遙望武昌附近的群山,只見平岡峻陵起伏,草木排列成行,當煙云消散太陽露出時,遠處漁人、樵夫的房舍,甚至都可以用手指清清楚楚地點數出來,這就是稱它為“快哉”的緣故吧!至于在那沙洲的岸邊,故城的廢墟,曾是曹孟德、孫仲謀當年虎視眈眈的區域,周瑜、陸遜當年率兵馳騁的戰地,那些遺留下來的傳說和痕跡,也足以聽世間傳說而為之快意了。
從前楚襄王讓宋玉、景差跟隨著游蘭臺宮,一陣清風吹來,颯颯作響,楚襄王敞開衣襟沖著風說道:“這風多么使人快樂啊!這該是寡人和百姓們共有的吧。”宋玉說:“這只是大王的雄風,百姓怎么能和您共享呢?”宋玉這話大概含有諷刺的意味。這風并沒有什么“雌雄”的區別,但是人卻有逢時不逢時的不同。楚襄王之所以感到快樂,而百姓之所以感到憂愁,這正是人為地造成的變化嘛,與那風又有什么關系呢?
士人生活在世上,假使他心中不得意,去到哪里沒有憂愁?假使他的心胸坦蕩,不因外物而損傷性情,那么,去到什么地方沒有快樂呢?如今張君不認為被貶謫是憂患,當清理完文書簿籍等公務后,自己縱情于高山流水之間,大概是他的胸懷有超過一般人之處了。即使住在茅屋瓦窗之中,也沒有什么不快樂,更何況是在清澈的長江中洗濯,觀賞著西山的白云,盡量地親身賞玩這優美的風光來自我享受呢?如果不是這樣,那么這群山連綿、丘壑壁立,遼闊的森林和參天的古樹,清風震撼,明月高照,這都是多愁善感的文人為之不勝悲傷憔悴的景色,怎能會看到它而“快樂”呢?
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