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游《游小孤山記》原文,注釋,譯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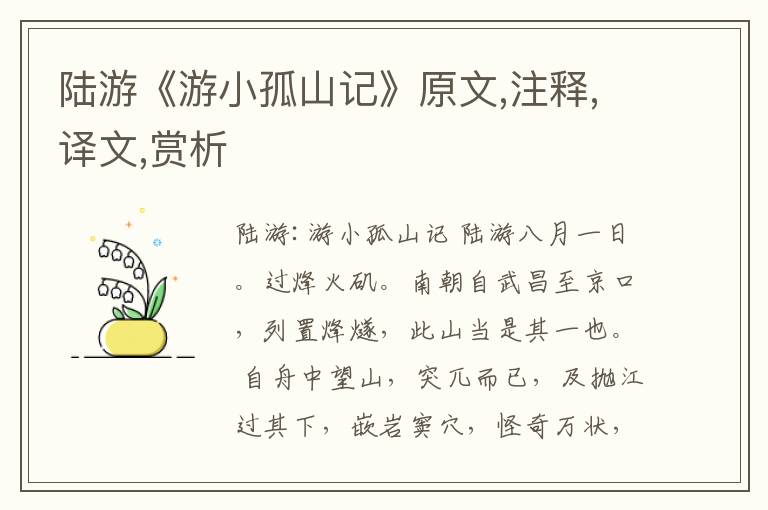
陸游:游小孤山記
陸游
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山當是其一也。 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拋江過其下,嵌巖竇穴,怪奇萬狀,色澤瑩潤,亦與它石迥異。又有一石,不附山,桀然特起,高百余尺,丹藤翠蔓,羅絡其上,如寶裝屏風。是日風靜,舟行頗遲,又秋深潦縮、故得盡見老杜所謂“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也。過澎浪磯、小孤山,二山東西相望,小孤屬舒州宿松縣,有戍兵。凡江中獨山,如金山、焦山、落星之類,皆名天下,然峭拔秀麗,皆不可與小孤比。自數十里外望之,碧峰巉然孤起,上干云霄,已非它山可擬,愈近愈秀,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極于荒殘,若稍飾以樓觀亭榭,與江山相發揮,自當高出金山之上矣。廟在山之西麓,額曰惠濟、神曰安濟夫人。紹興初,張魏公自湖湘還,嘗加營葺,有碑載其事。又有別祠在澎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涌,蓋以此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孤廟有彭郎像,澎浪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晚泊沙夾,距小孤一里。微雨,復以小艇游廟中,南望彭澤、都昌諸山,煙雨空濛,鷗鷺滅沒,極登臨之勝,徙倚久之而歸。方立廟門,有俊鶻搏水禽,掠江東南去,甚可壯也。廟祝云:山有棲鶻甚多。
《游小孤山記》也是《入蜀記》中的一則。小孤山在今安徽宿松縣東南大江中,隔水與南岸的江西彭澤縣相望。因狀如女子發髻,所以俗名髻山。小孤山,又因音近而訛轉為小姑山,并由此產生小姑嫁彭郎的傳說。歐陽修《歸田錄》卷二:“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為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為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婿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敕額為圣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在訛傳中衍化為神幻故事,所以蘇軾有“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的詩句。
陸游的這篇游小孤山記,看起來是按航程順次記敘,但仔細揣摩之后,方知作者深得用筆比襯之妙。未寫小孤山前,先以烽火磯相襯:“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山當是其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拋江過其下,嵌巖竇穴,怪奇萬狀,色澤瑩潤,亦與它石迥異。”在寫過澎浪磯、小孤山時,還是先不具體寫小孤山,而是概述長江中獨峙的著名山峰:“凡江中獨山,如金山、焦山、落星之類,皆名天下。”從更廣闊的背景上為小孤山作遠比和補襯。最后又以澎浪磯對比:“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層層烘襯,以賓拱主。
作者描寫小孤山之美,選用各個角度進行透視刻畫,既有總體的印象:“峭拔秀麗”;也有較遠距離的遠眺:“自數十里外望之,碧峰巉然孤起,上干云霄。”峰巖的顏色,突起的形貌,高峻接云的氣勢,在短短十字之中,勾畫無余;有近看:“愈近愈秀”;還有不同時間、不同氣候下的景觀變化:“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綠裝素裹,晴峰雨髻,姿顏色貌,秀麗動人,當然,更美的是小孤山傍晚的景色:“微雨”天氣,“南望彭澤、都昌詣山,煙雨空濛,鷗鷺滅沒”,江水浩茫,南岸遠峰隱約連綿,煙雨迷濛,在一片渺闊的銀灰色的背景上,偶爾有雪白的鷗鷺飛起隱沒,使這一寥寂的境界引起輕微的動蕩,顯得別有韻味,而最后的“有俊鶻搏水禽,掠江東南去”的景象,令人難以忘懷,猛健的鶻鳥撲擊水禽,并迅疾地掠過江面飛向東南天空,作者的心緒也隨之引向空渺的境界“陸游所創造的這一意象,空寞冷雋而又矯舉不凡,尤其是“掠江東南去”,更寓含難以明言的深意。
陸游在感嘆小孤山上祠宇荒殘時提出:“若稍飾以樓觀亭榭,與江山相發揮,自當高出金山之上矣。”這一看法極為精到。自然美景有其獨立的美,但如能在自然美的基礎上,建置樓臺亭閣,便可以人工美豐富和擴大自然美。明人計成《園冶》中曾說:“軒楹高爽,窗戶鄰虛,納千頃之汪洋,收四時之爛漫”,人工建筑所創造的空間,可以與自然山水所本有的空間,相互諧和地組合,“與江山相發揮”,表現出“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或藏或露,或淺或深”(沉復《浮生六記》),江山的自然美可以得到進一步發展、集中、變化、延伸和豐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