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石渠記》文章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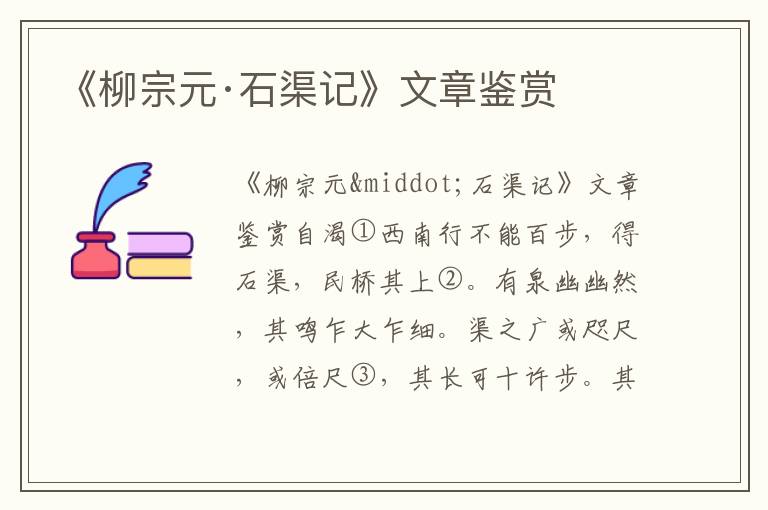
《柳宗元·石渠記》文章鑒賞
自渴①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②。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xì)。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③,其長(zhǎng)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④,昌蒲被之,青鮮環(huán)周⑤。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倏魚。又北曲行紆馀⑥,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cè)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⑦。風(fēng)搖其巔,韻動(dòng)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yuǎn)。
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⑧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⑨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⑩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窮也。
【注】
①渴:指袁家渴,一條溪水的名字。②民橋其上:百姓在上面建橋。橋,架橋。③咫尺:古代稱八寸為咫。咫尺,比喻很近的距離。倍尺:二尺。④泓(hóng弘):凹石積水而成的水潭。⑤被:覆蓋。鮮:苔蘚。⑥紆馀:曲折伸延。紆,彎曲。⑦箭:小竹。庥:同“休”,休息。⑧釃(shī詩):分流,疏導(dǎo)(水道)。⑨累記:接連記述。⑩蠲(juān涓)渠:清潔石渠。蠲,通“涓”,使清潔。
柳宗元的“永州八記”取材范圍已經(jīng)十分有限,地理跨度小得不能再小,依然篇篇精致,韻味悠長(zhǎng),這《石渠記》就是一例。這是柳宗元在永州寫的八篇山水游記的第六篇,文章記述了作者沿渠探幽,追求美景的事。表達(dá)了作者探奇制勝,拓寬胸懷,追求勝景借以抒發(fā)胸中積郁之氣的感情。
石渠之景比之永州山野中別處風(fēng)物也沒有什么特別之處,無非是水、木、石、風(fēng)等類。但柳宗元卻為讀者繪制了一幅“石渠風(fēng)光圖。”無論恬靜的民橋,幽然的渠水,昌蒲覆蓋的石潭,上下飄浮的白鰷魚,或是搖曳的樹木、花卉,韻動(dòng)崖谷的微風(fēng)以及紆曲緩行的流水,都能緊扣石渠的特色落筆。從石渠的被發(fā)現(xiàn)到石渠誘人的景觀,從對(duì)石渠的清理打扮到為之寫記的留傳后人的交代,都寫得清晰明麗,妙趣無窮。文章語言流暢,令人百讀而不厭。
文章構(gòu)思新穎,寫了石渠、石泓和小潭,這三個(gè)方面的景物雖然同在一個(gè)畫面里,但是它們的特點(diǎn)卻又各不相同。尤其是以似小曲的微觀展示“風(fēng)韻其心”的魅力,寫泉上的石頭樹木花草和竹子,特別是側(cè)重于風(fēng)聲的描繪上。風(fēng)搖動(dòng)著竹樹的梢頭,產(chǎn)生震撼崖谷經(jīng)久不息的回響,由視覺轉(zhuǎn)入聽覺,給那些畫圖似的景物,再加上一種詩韻般的音樂美,令人有深幽穆靜及如在目側(cè)的身臨其境之感。
此外,柳宗元以渠自喻,融情于景,愛渠及己,推己愛渠,從石渠天然之景,到整治石渠煥發(fā)其美,賦予石渠以人格化,不時(shí)給讀者以心靈的感應(yīng)和無窮的藝術(shù)享受,在“八記”中堪稱別具一格。
后人評(píng)論
林紓《韓柳文研究法》:“文有詩境,是柳州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