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桭臣《寧古塔紀略(節(jié)選)》原文,注釋,譯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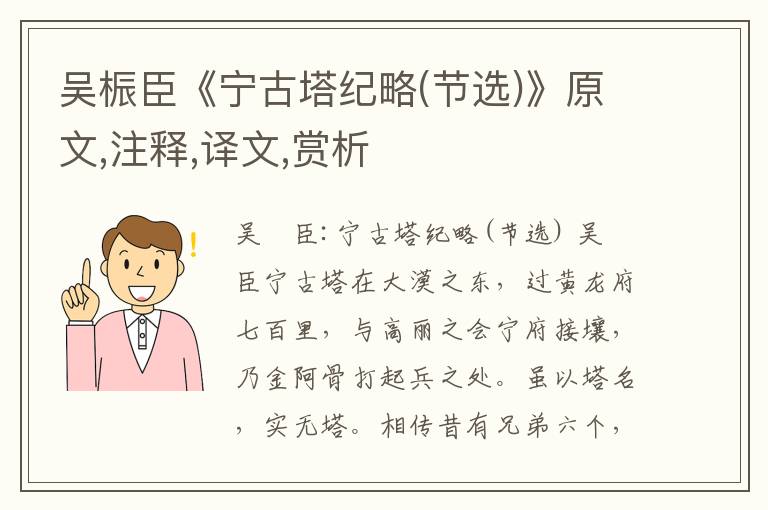
吳桭臣:寧古塔紀略(節(jié)選)
吳桭臣
寧古塔在大漠之東,過黃龍府七百里,與高麗之會寧府接壤,乃金阿骨打起兵之處。雖以塔名,實無塔。相傳昔有兄弟六個,各占一方。滿洲稱六為“寧古”,個為“塔”。其言“寧古塔”,猶華言“六個”也。……
當我父初到時,其地寒苦。自春初至三月,終日夜大風。如雷鳴電激,塵埃蔽天,咫尺皆迷。七月中有白鵝飛下,便不能復起。不數(shù)日即有濃霜,八月中即下大雪,九月中河盡凍,十月地裂盈尺。雪才到地,即成堅冰。雖向日照灼不消。初至者必三襲裘,久居即重裘可御寒矣。至三月終,凍始解,草木尚未萌芽。近來漢官到后,日向和暖,大異曩時。滿洲人云:“此暖是蠻子帶來”,可見天意垂憫流人,回此陽和也。
南門臨鴨綠江,江發(fā)源自長白山。西門外三里許,有石壁臨江,長十五里,高數(shù)千仞,名雞林哈答。古木蒼松,橫生倒插。白梨紅杏,參差掩映。端午左右,石崖下芍藥遍開。至秋深,楓葉萬樹,紅映滿江。江中有魚,極鮮肥而多,有形似縮項鳊,滿名發(fā)祿,滿洲人喜食之,夏間最多。余少時喜釣,每于晡夕,持竿垂釣。頃刻便得數(shù)尾而歸。……
春秋二季,將軍令兵丁于各門城上,晨夕兩時吹笳,聲聞數(shù)里。冬至令兵丁各山野燒,名曰放荒。如此則來年草木更盛。又每歲端午后,派八旗撥什庫一人,率兵丁幾名,將合寧古塔之馬,盡放于幾百里外有水草處。馬尾上系木牌,刻某人名,至七月終方歸。此時馬已極肥,俱到衙門內(nèi),各認木牌牽回。四季常出獵打圍。有朝出暮歸者,有兩三日而歸者,謂之打小圍。秋間打野雞圍,仲冬打大圍,按八旗排陣而行。成圍時,無令不得擅射。二十余日乃歸。所得者虎、豹、豬、熊、獐、狐、鹿、兔、野雞、雕羽等物。獵犬最猛,有能捉虎豹者。虎豹畏人,惟熊極猛,力能拔樹擲人。野雞最肥,油厚寸許。遼東野雞頗有名,然迥不及矣。……
至山海關。山海關,即秦之長城第一關也。城高而厚。南入海四十里,北面大山多,極其高峻。城則隨山上下而筑,關門向東。大路有一嶺,出關者稱為凄惶嶺,入關者稱為歡喜嶺。嶺下有孟姜女廟。是夕宿于嶺下。兩大人各述當時出關景況,今得到此,真為歡喜。明日進關,氣象迥別。又七日,至京師,與親友相聚,執(zhí)手痛哭,真如再生也。
《寧古塔紀略》是一篇回憶錄,也是一篇描寫東北風光的出色游記。作者吳桭臣出生于滿洲貴族發(fā)祥地——寧古塔,直至十八歲時才隨父吳兆騫返故鄉(xiāng)江蘇吳江。因而對這里的“風土人情,山川名勝,悉皆諳習,頗能記憶”。這篇“紀略”,便是他四十年后“誠恐久而遺忘,子孫不復知乃祖父之閱歷艱危”而寫的回憶。在這篇回憶錄中,作者以真切感人的筆觸,生動形象的敘述,藝術地再現(xiàn)了寧古塔的歷史、民情和山川風物,不僅在民俗學上有著珍貴的價值,而且也豐富了清代游記文學的寶庫。
《寧古塔紀略》原文近萬字,本文只節(jié)選了部分章節(jié)。從這些節(jié)選文字中,我們同樣會賞析到作者才華橫溢的文筆和寧古塔的奇異風光。
首先,作者開門見山,緊扣題面,準確而詳明地介紹了寧古塔的名稱和地理方位。這種開筆看似平淡,但卻十分必要。因為就字面而言,“寧古塔”很容易引起人們的誤解。因此當點出“雖以塔名,實無塔……猶華言六個也”之后,不僅使人渙然冰釋,而且還給讀者以異域風情的新奇感,從而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
接下去,追述其父初到寧古塔時的氣候。作者筆下隨即出現(xiàn)了一個苦寒冰冷的世界:自春初至三月的大風、七月的濃霜、八月的大雪、九月的河凍,十月的地裂……真是風雪彌漫的北國邊城!這段描寫,顯示了作者非凡的觀察力和表現(xiàn)力。正由于作者極善于觀察和捕捉寧古塔一年四季中典型月份的典型景物,所以只用幾個排比句,就把其父初到時的嚴寒氣候和悲苦心境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出來。隨后,作者借用滿洲人“此暖是蠻子帶來”的話,巧妙地把氣候變暖和漢官的流放連結一起,既撫慰著流人內(nèi)在的精神創(chuàng)傷,也反映了當?shù)厝说馁|樸與憨厚情態(tài)。
接下來,便是本文中最精彩的段落。作者以生花妙筆,把鴨綠江風光寫得錦繡迷人,妙趣橫生。碧水澄澈的鴨綠江畔,石壁臨江高聳,古木蒼松橫生倒插,白梨紅杏嫵媚多姿,石崖下的芍藥散發(fā)著醉人的馨香,萬樹楓葉染紅江面,水中魚兒成群結隊……萬千景象信手拈來,匯成一幅生機盎然的畫圖。這里,既有季節(jié)的更迭,又有場景的轉換;既有植物,又有動物:既有靜態(tài)的描寫,又有動態(tài)的刻畫。甚至還有顏色的組合,如鴨綠江暗含一個“綠”字,古木蒼松暗含一個“青”字,芍藥則赤、白相雜,再加上白梨紅杏和丹楓的參差掩映,顯得更加色彩繽紛,風光滿眼。尤其那關于魚的描寫,更充滿著生活情趣。且不說那鮮美可食的鴨綠江特產(chǎn)哈什馬和發(fā)祿魚,就是那黃昏“持竿垂釣,頃刻便得數(shù)尾而歸”的場景也足以令人心馳神往。
如果說前邊的描寫還只是以自然氣候的苦寒和自然景物的秀麗牽動人的情思,那么下一段則是以風土人情動人心魄。諳悉北國風情的吳桭臣,一開筆就象電影放映師那樣推出了一組畫面:聲聞數(shù)里的笳聲、各山野燒的放荒、草原水邊上的牧馬。隨后,便把特寫鏡頭對準了“四季出獵打圍”的風習。滿洲人向以騎射、打獵著稱于世,打圍更成了寧古塔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仲冬的“大圍”更為壯觀。對此,作者采取了虛實相生的手法,有意把一些場景隱去或虛寫,讓讀者從筆下的實景中去聯(lián)想、體會和補充。比如作者雖只寫了豐盛的獵物虎、豹、豬、熊、獐、狐、鹿、兔、野雞,雕羽等,但卻會使人由此想到狩獵場面的宏大壯闊;雖只寫了鷹犬之猛,卻令人仿佛看到其主人剽悍勇武的英姿;雖只寫了虎豹畏人和熊拔樹擲人,卻讓人想象到圍場緊張激烈的拚搏撕殺……這樣寫,既節(jié)省了大量筆墨,又適當?shù)丶哟罅俗髌返奈炊ㄐ院涂瞻锥龋ぐl(fā)了讀者的理解和想象。
節(jié)選的最后一段,是寫作者隨赦歸的父親入關至京師的情景。此段最為突出的特點是移情于景,情景交融,感情濃烈而深沉。他的父親作為一個被流放異鄉(xiāng)二十余年的逐臣,一旦踏進山海關門,該有多少話語要傾吐啊!然而作者卻沒有空發(fā)議論,眼前的景物對他來說都是初次相識,但隨父生還,步入關門的喜悅之情卻是很強烈的。山海關門前的一條嶺,本是無情之物,但由于人的不同境遇和情感卻充當了悲、喜不同的兩種角色:“出關者稱為凄惶嶺,入關者稱為歡喜嶺”。因此作者及時地捕捉到了父親此次入關見到當年凄惶嶺時悲喜交集的復雜情態(tài)。一方面“兩大人各述當時出關景況”,一方面兩位老人又止不住熱淚橫流,發(fā)出:“今日到此,真為歡喜”的肺腑之語。至此,作者將他父母郁積心底二十余年的感情大潮才找到了渲泄口。讀后,令人感慨殊深,回腸蕩氣。
這篇文章內(nèi)容異常豐富,但寫法上基本以寫景、抒情見長,而不以議論、說理取勝。文中寫景物、記古跡,敘風俗、抒感慨,筆法靈活自如,很能代表這類回憶錄式的游記文學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