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萬里《景延樓記》原文,注釋,譯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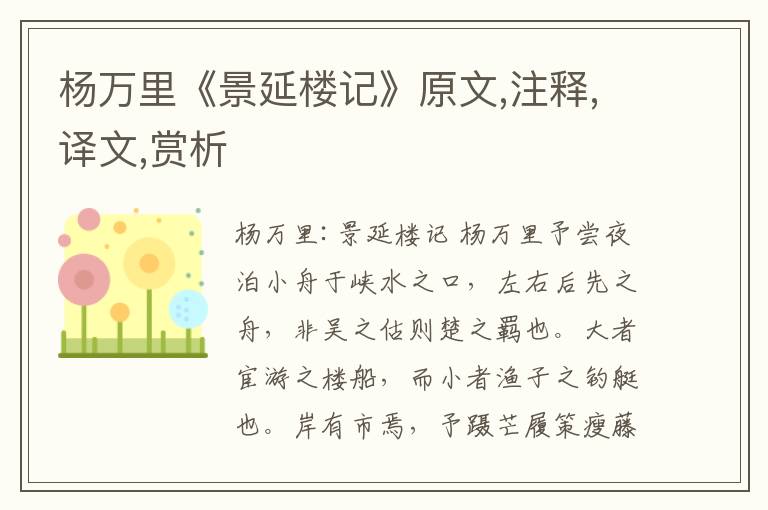
楊萬里:景延樓記
楊萬里
予嘗夜泊小舟于峽水之口,左右后先之舟,非吳之估則楚之羈也。大者宦游之樓船,而小者漁子之釣艇也。岸有市焉,予躡芒履策瘦藤以上,望而樂之。蓋水自吉水之同川入峽,峽之兩巖,對立如削,山一重一掩,而水亦一縱一橫。石與舟相仇,而舟與水相諜,舟人目與手不相計則殆矣。下視皆深潭激瀨,黝而幽幽,白而濺濺,過者如經(jīng)滟滪焉。峽之名豈以其似耶!至是,則江之深者淺,石之悍者夷,山之隘者廓,而地之絕者一顧數(shù)百里不隔矣。時秋雨初霽,月出江之極東,沿而望,則古巴丘之邑墟也;面而覿,則玉笥之諸峰也;泝而顧,則予所經(jīng)之峽也。市之下,有棟宇相鮮,若臺若亭者。時夜氣寒甚,予不暇問,因誦山谷先生《休亭賦》登舟。至今坐而想之,猶往來目中也。
隆興甲申二月二十七日,予故人月堂僧祖光來謁予,曰:“清江有譚氏者,既富而愿學(xué),作樓于峽水之濱,以納江山之勝,以待四方之江行而陸憩者。樓成,乞名于故參政董公,公取鮑明遠(yuǎn)《凌煙銘》之辭而揭以‘景延’,公之意欲屬子記之而未及也,愿畢公之志以假譚氏光。”予曰:“斯樓非予疇昔之所見而未暇問者耶?”曰:“然。”予曰:“山水之樂,易得而不易得,不易得而易得者也;樂者不得,得者不樂;貪者不與,廉者不奪也;故人與山水兩相求而不相遭。庾元規(guī)、謝太傅、李太白輩非一丘一岳之人耶?然獨得竟其樂哉。山居水宅者,厭高寒而病寂寞,欲脫去而不得也。彼貪而此之廉也,彼與而此之奪也,宜也,宜而否何也?今譚氏之得山水,山水之遭乎,抑譚氏之遭乎?為我問焉!”祖光曰:“是足以記矣。”乃書以遺之。
譚氏兄弟二人,長曰匯,字彥濟;次日發(fā),字彥祥。有母老矣,其家睦。祖光云,楊某記。
《景延樓記》寫于宋孝宗隆興二年(1164)二月。按記文所述,景延樓當(dāng)在此前不久建成,其位置則在江西峽江縣西南的峽水(贛江)之濱,與縣東南的玉笥山遙遙相望。
按照一般寫法,總是分別描述景延樓內(nèi)外的景觀,而這篇記文卻以不同凡俗的構(gòu)思,用自己泊舟峽水之口的一段親身經(jīng)歷,取代了慣用的正面描寫。在隨意記敘的夜登峽岸所見景色中,實際上也就是景延樓中所應(yīng)觀賞到的吞納江山之勝的氣象。初看起來,開篇就寫個人夜泊峽水之口的經(jīng)過,似乎與文題不相切合,可是這一大段文字又顯然是整篇文章中的重頭筆墨,更奇特的是整段文字絲毫沒有提到景延樓,使人感到這只是一則偶爾登臨的山水小記。看到后文,方知這一段不是一般的記游,而是與寫景延樓密切相關(guān)的妙文。作者在前段文字寫夜登峽岸觀覽江山后,自然而又暗含深意地寫到夜色“市之下”,隱約有“若臺若亭”的棟宇,“時夜氣寒甚,予不暇問”,這棟宇當(dāng)然就是景延樓,說因夜氣寒冷來不及細(xì)問,可能是事實,也可能是遁辭。就文章而言,不問最好,問明了,點出了景延樓,也就顯不出前后兩段文字的藏露之趣,構(gòu)思至妙。前段文字的最后兩句:“至今坐而想之,猶往來目中也”!這是對夜中峽水景色的贊美之辭。同時也是對景延樓景的評贊。
從寫景角度看,前一段也是一篇難得的山水游記文字。整個游覽的過程敘述得井然有序,從“夜泊小舟于峽水之口”開始,然后寫登上峽岸小市觀望諸景,最后再寫回歸舟中,觀望的角度變換多樣,但又脈絡(luò)清楚,先寫峽水之險,繼寫峽口平曠景貌,再接寫月下遠(yuǎn)望中的邑墟、山巒,最后寫市下隱約的棟宇,層次極為分明。特別值得稱道的是景色的描繪。他先大筆勾貌:“蓋水自吉水之同川入峽,峽之兩巖,對立如削,山一重一掩,而水亦一縱一橫。”從吉水縣同川到峽口的一段贛江,兩岸巖石壁立如削,而且山峰轉(zhuǎn)折連綿,江水也自然隨之回環(huán)奔流,峰巒陡峭,水流受阻后更加湍急。接著進一步具體畫形比較:“石與舟相仇,而舟與水相諜,舟人目與手不相計則殆矣。”嶙峋突出的巖石,沖激漩洄的波濤,象仇敵一樣伺機將舟船撞碎擊沉。駕舟人的眼睛和掌舵、扯帆、搖櫓等動作協(xié)調(diào)配合上,只要出現(xiàn)小小差誤,就會舟毀人亡,極力寫出峽水行舟的艱險。作者在勾貌畫形的基礎(chǔ)上,再精心著色渲染水的情狀:“下視皆深潭激瀨,黝而幽幽,白而濺濺,過者如經(jīng)滟滪焉。”俯望峽水,不是水色黝黑幽暗的深潭,就是浪花飛濺如雪的礁瀨,黑色隱含著深不可測,白色描畫出水急石險的景狀,使人目眩心驚。山轉(zhuǎn)水奔、巖浪相激,在作者勾貌、畫形、染色的層層描繪下,逼現(xiàn)出峽水的險壯之美。更妙的是,峽口的另一面則是:“江之深者淺,石之悍者夷,山之隘者廓,而地之絕者一顧數(shù)百里不隔矣。”水變淺了,石變平了,山峰蔽塞變闊了,原來險仄之地變?yōu)橐煌綍绲脑埃瑑烧咝纬蓮娏业膶Ρ龋郊语@現(xiàn)出景延樓一帶景色的多姿多采。在秋雨初停之后,明月東升之際,天地澄明,遠(yuǎn)處巴丘古鎮(zhèn)的燈火,玉笥群峰的秀影,斗折蛇行的峽水,都映現(xiàn)在清冷的月光之下,顯得分外清晰、優(yōu)美,江山寥寂,身處此境,很容易產(chǎn)生如畫似夢之感。
后面的一大段文字,寫故人祖光和尚為清江譚氏求寫景延樓記事。通過祖光之口,交代了景延樓的建置本意和取名景延的由來。譚氏“富而愿學(xué),作樓于峽水之濱,以納江山之勝,以待四方之江行而陸憩者。”表明建樓取景,意在待客。為樓取名“景延”的故參政董公,指曾在紹興二十五年(1155)除參知政事的董德元,他從鮑照《凌煙銘》的“望景延除”句中摘選“景延”二字,含延景入樓之意。作者沒有在“景延”的名稱上多費筆墨,而是伸延開去,就山水與人之間的相求相遭關(guān)系發(fā)表議論:“山水之樂,易得而不易得,不易得而易得;樂者不得,得者不樂;貪者不與,廉者不奪也;故人與山水兩相求而不相遭。”山水作為自然物,無處不在,人人可得可見。然而,真正領(lǐng)略山水之樂趣者并非人人可得。不能賞覽山水之樂趣者,對隨處可見的山水視若無物,而能深知山水之趣者,則隨處俯仰可得。 當(dāng)然,有時候樂于山水者未必得見山水,而可得常見山水者又未必獲得此中之樂。山水作為獨立存在的自然物,貪占者不見得能賞玩,而廉潔者無掠奪之意卻可能獲得山水之樂。山水與人之間存在著互相追求、而又常常未必能如愿相遇的關(guān)系,山水求知音,愛山水者求樂趣,兩者都能巧相諧和者不多。因為人對山水有著截然相反的態(tài)度。歐陽修曾說過:“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于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之樂也”,“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浮槎山水記》)。作者所以在夜觀峽水之景后,“誦山谷先生《休亭賦》登舟”,是因黃庭堅《休亭賦》中寫友人肖濟父“齋心服形,”絕意仕進,“筑亭高原,以望玉笥諸山”,真正獲得了山林之樂,成為山水的知音,因而借誦其賦以抒情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