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任《雁蕩山記(節(jié)選)》原文,注釋,譯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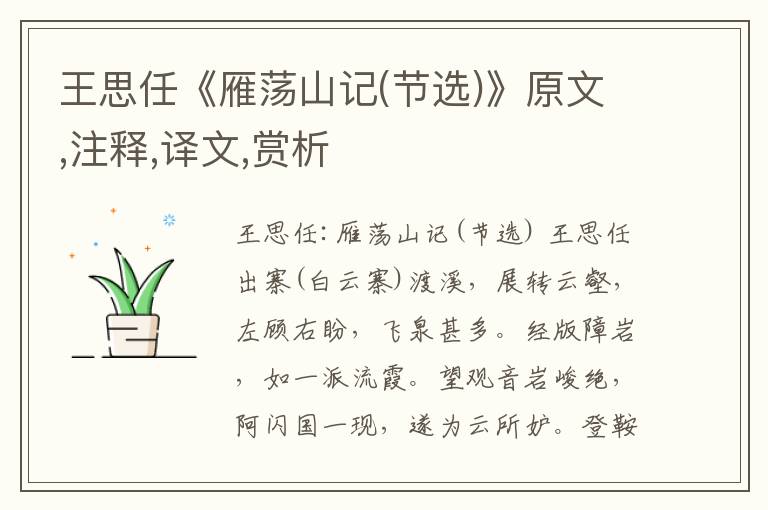
王思任:雁蕩山記(節(jié)選)
王思任
出寨(白云寨)渡溪,展轉(zhuǎn)云壑,左顧右盼,飛泉甚多。經(jīng)版障巖,如一派流霞。望觀音巖峻絕,阿閃國一現(xiàn),遂為云所妒。登鞍嶺以待之,云且呼黨錮我,于是走石門寺廢基,上羅漢洞看石羅漢。或云自閩飛來,惡知非應(yīng)真之化體耶?望常云峰,峰似云耳。過道松洞,洞以羽客得字。經(jīng)瑞鹿寺遺跡,一峰呦呦岳岳,安得浪指為馬。沿澗有大峰,人立而怒。對壁為連云障,障上開二小鉗。元李孝光謂是蟹足。稍入澗有剪刀峰,分開千仞,欲剪青天者。張肅之易其名為巨螯而未決。予以為山波似海,既有彭越,那得無蝤蛑?對壁有兩穴,名閻王鼻,然大約似虎頭虎眼。入益幽畏,耳根但聞雷走。
過一庵折徑而上,數(shù)千仞凹壁懸空,掛下一團白柱,又不知是龍是水也。上諾詎那觀瀑臺,勢既雄惡,而潭洄兇暗,令人百端交集。稍狎之,怖心略定。諸家摹仿,各得其一體,而予靜圖之:初來似霧里傾灰倒鹽;中段攪擾不落,似風纏雪舞;落頭則是白煙素火裹墜一大筒百子流星,九龍戲珠也。……
大龍湫絕頂五里,尚有碧潭。正德中五臺二僧廬焉此龍藪,二僧寂后仍龍據(jù)。去碧潭上約三十里,則為蕩湖,是即宋人見雁之頂,亦有鳥路可通。而雨深草塞,予不能好事矣。還從錦溪出壑,身如霞瀑水洗濯珊瑚骨。一行七里,過古塔寺,僅有華陽洞,不及登。所謂梅雨巖,星飄珠濺,頗為龍湫所掩。卓刀峰僅當徐夫人一匕首。而含珠峰弄丸于夾谷之中,似從大湫盜睡驪者,終當風雨取去。逾數(shù)溪,至能仁寺,雁山萬木奔呼。至寺后,忽亭靜如凝靛。從左嶺繞下,一溪頭瀉入八尺水屏,聲聲月珮。由行春橋入寺,望火焰峰,不可向邇。戴辰峰則手可以摘星矣。燕尾泉裂玉飛潭,時生空霧。看大鑊二只,可飯千僧。云是宋官家物。意當年梵宮鼎麗,游屐必多。而今不能無銅駝野棘之感也。
于是從筋竹澗,上丹芳嶺。舊傳筋竹澗,康樂開山止此。山水有緣,顯晦有候,豈畚鍤之所得取者。嶺峻絕,四十九盤,一盤一勝。回望一百奇峰,如郭子儀軍偃旗息鼓,而戟槊稜稜,俱有欲起之意。……
是役也,山谷之外所見者,紫茶方行、金線鳳尾草、香魚、白鷴、山樂官、雪髯猿一。而雁蕩之觀,亦仿佛得其皮毛矣。或曰:雁蕩應(yīng)秋游。予獨以五月來,宜受云物之吝,然吾不欲其一覽而盡,故且以云紆馀委曲之。吾觀靈峰之洞,白云之寨,即窮李思訓數(shù)月之思,恐不能貌其勝。然非云而胡以勝也。云壯為雨,雨壯為瀑,酌水知源,助龍湫大觀。他時無此洪沛力者,伊誰之臂哉?至于秋清氣肅,上蕩頂,走山根,呼天剔地,則予尚有葛陂之龍,在秋所同也,而云所獨也,吾復何憾也!
王思任的《雁蕩山記》寫得很長,這里節(jié)錄了最后兩部分加以鑒賞,即出白云寨到諾詎那觀瀑臺觀大龍湫瀑布,再登丹芳嶺看雁蕩全景的游程。
文章的線索純粹是按照游蹤安排的,并沒有什么突兀奇特之處。沿途的一峰、一溪、一橋、一寺都作了記載,但讀來并不覺得瑣碎,關(guān)鍵在于作者沒有花費大量筆墨作客觀具體的描繪,而是以充分的想象和比喻,傳神地寫了一處處景色。如從白云寨到觀瀑臺,一路上十處景物以數(shù)百字寫過,非常注意用比喻來勾畫山水特有的形象,如寫版障巖如霞,常云峰似云,觀音巖阿閃國一現(xiàn),剪刀峰欲剪青天,都顯得流動洗煉。
觀瀑一節(jié),寫出了龍湫奇觀對作者心靈的震憾以及作者的心靈與山水的融合境界。作者一登上諾詎那觀瀑臺,看到“勢既雄惡,而潭洄兇暗,令人百端交集”,而后“稍狎之,怖心略定。”開始,完全震懾于大自然的雄奇?zhèn)ゴ蟆5谡饝刂啵佬穆远ㄖH,很快進入了對自然的審美過程之中,而且以靜心觀動景,與自然融為一體。他作為一位善于寫生的畫家,卻不同于其他諸家畫瀑布的激蕩之勢,而是“靜圖之”,這“靜圖之”就是他對自然的審美,是他內(nèi)心的境界。龍湫觀瀑臺是晉代高僧諾詎那觀瀑之處,后人的贊語中有“雁蕩經(jīng)行云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王思任在此時也想到了諾詎那當時的心境,又聯(lián)想到孔子在川上說“逝者如斯夫”時的情景,這是在動蕩流逝的大自然景物之前發(fā)出的對宇宙本體的頓悟與感嘆,也是王思任“靜圖之”的意趣所在。此外,這一節(jié)中寫龍湫瀑水自上而下的勢態(tài)非常精采,由于瀑布非常高遠,瀑源瀉出處霧氣蒸騰,“似霧里傾灰倒鹽”,使人感到水勢瀰滿宇空。中段水勢洪浩不絕,“攪擾不落,似風纏雪舞。”到了下面則散作珠雨,作者傳神地寫成“白煙素火裹墜一大筒百子流星,九龍戲珠也。”云霧煙水,混濛攪擾,構(gòu)成奇壯的圖景。
離開龍湫去丹芳嶺一路,有兩處寫得尤為精采。一是“含珠峰弄丸于夾谷之中,似從大湫盜睡驪者,終當風雨取去。”這里作者看到了含珠峰上裂隙之間,有石如珠,因而巧妙聯(lián)想,把石珠比作驪龍頷下的驪珠,而含珠峰則成了探驪者。只是這驪珠和莊子所說的不同,是從大龍湫沉睡的驪龍那里偷盜來的,必將為乘風雨而來的驪龍取去。這樣的想像不僅是非常奇特的,而且將古代傳說,隨手點化,移花接木,更富于神話色彩。二是寫能仁寺的“雁山萬木奔呼,至寺后忽亭靜如凝靛。”寥寥幾筆便寫盡了樹林的動靜勢態(tài)。
丹芳嶺是作者最后的游程,也是作者對雁蕩山全景的頓悟與洞徹。開始上嶺時,由于未能俯瞰雁蕩,所以盡管能回顧千百奇峰,但峰峰皆有上聳之勢,“如郭子儀軍偃旗息鼓,而㦸槊稜稜,俱有欲起之意。”真是妙筆生花,將群峰聳起之勢寫得栩栩如生。而到了峰頂更加豁然開朗,看盡雁蕩山內(nèi)外的奧妙,“胡桃果隔,別中妙有囊實”等一系列比喻,是作者感悟的心靈歷程。最后作者為在不適宜之時游雁蕩卻看到云水勝境而自許。
總觀全文,可以發(fā)現(xiàn):作者很注意寫山水景物的動靜之勢,也注意寫自我心靈的激蕩與平靜,還善寫云寫水。這大概與作者是位畫家有關(guān)。我們知道王思任的畫風是米家山水與云林畫意,空濛遠靜是這兩家的特色,這樣的畫風也影響了這篇游記的風格,使之成為融畫意于文思的清美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