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學·艾略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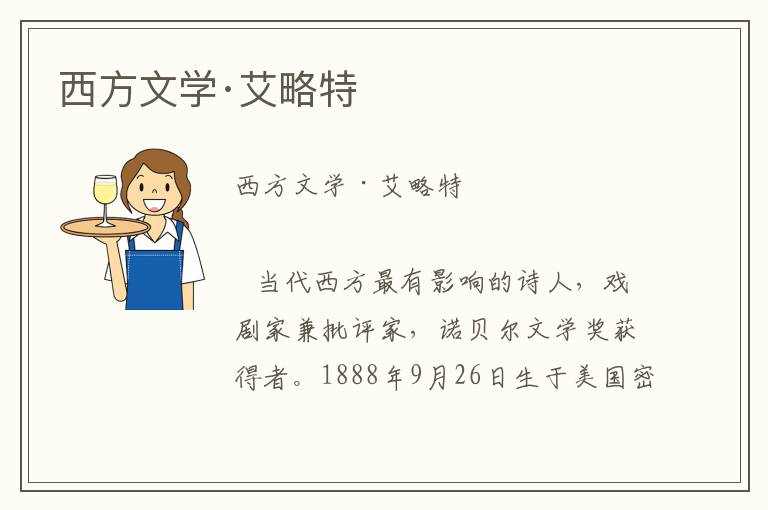
西方文學·艾略特
當代西方最有影響的詩人,戲劇家兼批評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1888年9月26日生于美國密蘇里州,祖父是華盛頓大學的創建人,父親是一位殷實商人,母親來自新英格蘭名門,艾略特的才賦,勤勉,對詩歌的愛好都深受母親的影響。他在這樣一個富有文化修養的家庭里度過了童年時代。他曾就讀于哈佛大學、巴黎大學、牛津大學,專攻哲學,他興趣極廣,除哲學外,還修習了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臘文、中世紀史、比較文學、東方哲學和宗教等,他潛心研究布萊德里,博士論文為《經驗和知識的目的: 布萊德里哲學》,布萊德里的哲學思想對艾略特詩歌創作起了深遠的影響。1914年艾略特結識了已成名的龐德,在他的影響和幫助下,開始專心致力于詩歌創作。艾略特作過中學教師,銀行職員,1925年進入費邊和哥威爾出版社(后來成為費邊和費邊出版社)。1927年加入英國國籍,入英國國教會,194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1965年1月4日在倫敦逝世。艾略特曾自稱他在宗教上是英國國教徒,政治上是保皇派,文學上是古典主義者。在詩歌創作上,他深受玄學詩人,法國象征主義詩人和雅各賓時代劇作家影響。艾略特詩歌作品在數量上并不大,但在現代文學界,詩歌界卻無可爭辯地成為一座里程碑,開創了一代詩風。他的詩作“具有嚴格的責任感和作風的自我約束力,摒棄了所有抒情的老調,完全著墨于實質性的事物上,嚴峻,硬朗,質樸,但又不時地為來自奇跡與啟示的永恒空間的光芒照耀。”
從1915年《普魯弗洛克的情歌》發表,到1922年《荒原》發表前這段時間,是他創作的第一階段。艾略特看到的西方世界危機四伏,腐化墮落,而西方社會中生活著的人們只是有體無魂的行尸走肉。《普魯弗洛克情歌》、《小老頭》等作品也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知識分子的情況,他們痛感西方世界已日薄西山,現代文明枯竭無力,但卻不愿陷入骯臟罪惡之中,苦于無能為力,只有冷眼觀望。早期作品《普魯弗洛克的情歌》、《一位夫人的畫像》、《—個哭泣的年輕姑娘》、《海倫姑娘》等收入《普魯弗洛克及其它》。
1922年到1925年《空心人》發表,是艾略特創作的第二個階段。《荒原》是20世紀最杰出的詩篇,它反映了戰后西方世界整整一代人的幻滅和絕望,昔日文明和傳統價值衰落。它的成就正在于捕捉了處于一片混亂和衰退中現代社會荒原般的“時代精神”。詩人大量運用典故和神話傳說,時而現實時而神化,各種意象交織在一起,構成一幅富有象征意義的神秘的完整畫面。《空心人》描寫一切都已毫無意義,荒原中的人們成了空心人,這首詩代表了詩人精神歷程中死氣沉沉的中心。
從《灰星期三》 (1930) 到《四個四重奏》 (1942),是詩人創作的第三階段。《灰星期三》描述宗教皈依道路上的艱辛和思想斗爭,其它宗教題裁作品有《三圣人之旅》 (1927),《西蒙之歌》 (1928)。《四個四重奏》是詩人一生創作的高峰,全詩分為四部分,都是對時間、歷史、皈依等主題的沉思默想,分析深刻,同時充分體現了詩人對作品音樂美的興趣。詩人皈依宗教的另一結果是幾部詩劇的創作:《磐石》 (1934)、《大教堂里的謀殺》 (1935)、《合家團聚》(1939)、《雞尾酒會》 (1950)、《機要秘書》 (1954)、《政界元老》(1959),其中主要主題為在自然和超自然組成的世界中對精神寧靜的追求,詩人認為宗教能使分崩離析的西方社會復興,人們能在神秘的世界里找到精神寄托。
艾略特是一位著名的文學批評家。1922年至1939年,他在《自我主義者》、《泰晤士文學刊》、《標準》等雜志任編輯,成為類似于19世紀馬修·阿諾德那樣的評論權威。他學識淵博,比較分析客觀深刻,擅于旁征博引,這些使他的判斷評價更加有力。他的主要論文集有《圣林》(1920)、《論文選集》 (1932)、《詩的功能和批評的功能》(1933) 、《論詩與詩人》(1957) 等。艾略特是一位有意識進行實踐的詩人,他有自己的文學理論,而他的詩正是他詩歌理論的具體體現。他善于運用內心獨白,把意識和潛意識中的思想寫進詩中。把抽象的思想感情化,用鮮明的意象使思想形象化。用典故是他詩作又一大特點,典故既含蓄地暗示出古今對比,發人深思,同時也增大了作品的容量。艾略特作品十分難懂,有時甚至是晦澀的。關于這點,詩人曾作過說明,揭示我們的文明是復雜多樣的,詩人必須隱晦地、間接地去表達他的意思。而當詩人晦澀而純熟的文字形式被人理解后,它們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