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學·后期象征主義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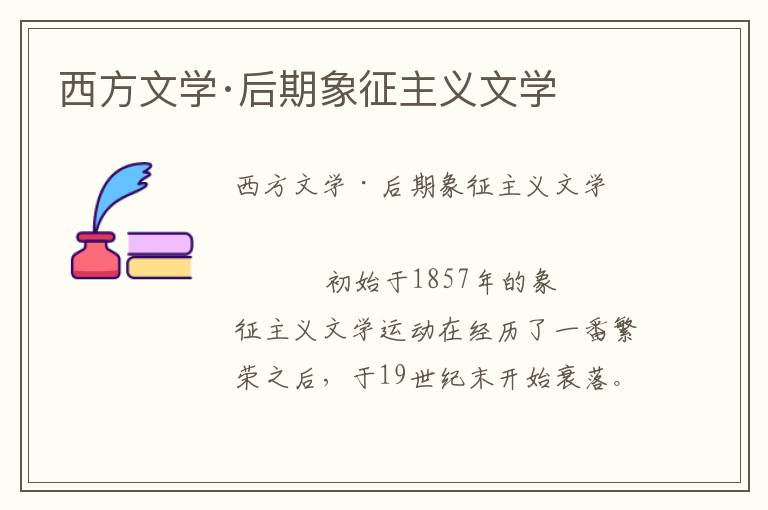
西方文學·后期象征主義文學
初始于1857年的象征主義文學運動在經歷了一番繁榮之后,于19世紀末開始衰落。到了20世紀20至40年代,這股潮流又開始在歐美文壇上復活盛行,人們把這時的象征主義文學稱為后期象征主義文學。后期象征主義文學在創作方法上依然沿襲了前期象征主義的傳統并加以發展; 在創作領域方面突破了詩歌的界限,進入了戲劇等藝術門類。后期象征主義文學比之前期,不論是聲勢還是規模都更為宏大,它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文學傳統相結合,呈現出多姿多彩的面貌,同時,在具體的作品中象征也顯得更復雜,更多層次。
具體地說來,在美學追求上詩人們仍然認為外界的事物與人的內心世界互相感應契合,息息相通,可以運用有聲有色的物象來暗示內心的微妙世界。美并不存在于現實世界之中,而只存在于這之外的另一個更真實的世界里,詩的目的就在于暗示這另一更真實的世界的神秘。如葉芝就說過:“全部聲音,全部顏色,全部形式,或者是因為它們的固有的力量,或者是由于源遠流長的聯想,會喚起一些難以用語言說明,然而卻又是很精確的感情。”這和早期象征主義詩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相比較而言,后期象征主義的詩人們又帶有更多的理智的成分。他們要求“除了感情的象征外,還有理智的象征”,讓理智滲進詩里,使讀者知道該在什么地方對一系列象征進行深思。也正是讓理智進入詩作之中,使得后期象征主義的不少作品一方面很有想象力和激情,另一方面又不流于縱情無度。后期象征主義文學還深受當時流行在詩壇上的“意象派”詩歌影響。意象派深感于后期浪漫主義感情泛濫、言之無物、意象模糊等弊端,強調詩歌意象的重要性,這一點為著名詩人和文藝理論家艾略特所吸收,如艾略特就提出了“客觀對應物”的概念。艾略特的理論認為詩歌不是放縱感情,而是逃避感情; 詩歌不是表現個性,而是逃避個性。一個作家發展的過程就是“不斷地犧牲自己,不斷地消滅自己的個性”的過程。他所提倡的尋找“客觀對應物”的創作方法就是指詩人為了表現具有普遍意義的情感,必須找到與這些情感密切相關的形象、情境、情節等等適當的媒介。他認為詩人一旦找到了這種適當的媒介,把它寫在詩里,就能夠使讀者立即感受到詩人要表現的情緒。“客觀對應物”賦予情感以形式。詩人愈能把各種情感密集地表現在某種形象或文字里,詩就愈有價值。艾略特自己的詩作就典型地體現了他的這種理論主張,如他的著名長詩《荒原》就是借漁王尋找圣杯的情節來表現西方現代人心靈的饑渴的。詩中還有很多現實生活細節的形象描繪,借此來向人們顯示現代人的寂寞和空虛,讀者可以從詩人不動聲色的客觀描述中體驗到那種掩藏在形象背后的強大感情力量。后期象征主義文學由于過多地強調對不同于現實生活的另一個神秘的境界的追尋,帶有很強的玄想成分,造成許多作品非常晦澀難解。里爾克后期的一些作品一方面交織著個人的懺悔、怨訴和對宇宙萬物的變化以及生與死的關系的探索,顯得深沉,但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晦澀神秘這一特點。葉芝的詩作中就更明顯了。后期象征主義文學還非常重視詩歌的形式美,不少詩人在自已的創作中都力爭使詩作具有音樂美、雕塑美等特點,這使得后期象征主義文學在作品的形式發展上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后期象征主義文學運動同政治斗爭聯系非常密切,這也是它的一個顯著特點。它的許多詩人都表達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不少人投入到了政治斗爭的洪流中去,創作了帶有很強傾向性的作品。如俄國詩人亞歷山大·勃洛克在革命浪潮的影響下創作了長詩《十二個》,歌頌了赤衛軍戰士的英勇品格。葉芝也因為參加了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而使詩風變得明朗。艾略特更是直言不諱地宣稱自己是“文學上的古典主義者,政治上的保皇主義者,宗教上的盎格魯天主教徒”。
后期象征主義的代表詩人和作品,除了上面提到的外,還有俄國的葉賽寧; 法國的保爾·瓦雷里,他的代表作是長詩《海濱墓園》; 意大利的埃·蒙塔萊; 西班牙的費·加·洛爾伽; 比利時的愛彌兒·維爾哈倫等。還有戲劇方面的代表人物比利時的莫·梅特林克,代表作 《青鳥》; 德國的蓋·霍普特曼,代表作 《沉鐘》; 英國的約翰·沁,代表作《騎馬下海的人》。








